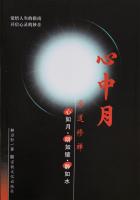袜宏在云栖寺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在此期间,他一边手不释卷地著述,一边为四方信众开讲净土法门,倡导念佛往生。中国佛教经过隋唐兴盛之后,自宋以后便渐趋衰微,而南北戒坛,更是久无人迹。袜宏在云栖寺开坛传戒,接引徒众,从此四方前来求法的人多不胜数,一时人称“云栖大师”。
袜宏的继室汤氏在其丈夫决定出家时曾说过一句话:君请先行,妾随后就去。株宏出家不久,汤氏即削发为尼,为孝义庵主。袜宏人寂前一年,汤氏即先而逝。
袜宏中年出家,弘宗演教四十余年,对净土、华严、禅、律都有极深的研究,一生著述顿丰,主要著作有《竹窗随笔》、《禅关策进》、《阿弥陀佛经疏钞》四卷、《楞严摸象记》十二卷等。在所有诸宗中,对净土念佛更为热衷,被后世人尊为净土宗八祖。对于自东晋慧远以来所倡导的念佛法门,他更总结为四种念佛,即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像念佛、实相念佛。他认为,惟有横截生死,都摄六根的净土修持,才是末法众生了脱生死,往生净土的方便法门。
§§§第六节明末四大高僧(二)
——冤死狱中的紫柏真可
夜幕徐徐降临,苏州虎丘山被一股沉沉的雾蔼笼罩着。十七岁的昊达观信步踏上虎丘山.想一睹古城苏州的夜色。
从不远处的云岩寺传来一阵僧人的诵经声,正是僧人们进行每日例行的晓课时间。吴达观被那苍苍的音韵吸引着,不觉走到那大殿的门口。
大殿里油灯高悬,昏黄的灯光下,几十个僧人正跪在地上诵念着佛号。吴达观细细地听了一下,那是在诵《八十八佛》。他过去曾去过一些寺庙,他也知道僧人们每晚的功课是单日《阿弥陀经》,双日《八十八佛》。但是,今天听这《八十八佛》,竟是以往任何时候也没有的感受。随着那沉沉佛号的诵念,吴达观渐渐地感到自己就像一片缥缈的云丝在夜空中轻荡着,渐渐也就虚无而空旷起来。僧人们终于结束了晚间的功课,依次向佛顶礼,一边脱着海青一边走出了大殿,而吴达观却依然站在那大殿门外,对着那三尊大佛泪流满面。
僧人们不知这青年受着什么刺激,人家也不管他,径自从他的身边走过。大殿前就只剩下吴达观一个了。他从一种虚无的境界中醒来,终于意识到,连日来的奔波,实在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吴达观自一个月前离开家乡吴江(属今江苏)后,就一直在外飘泊着。
自少年时代即开始萦绕于心的梦想,吴达观一直想做一个镇守边关的军将。也正是这梦想使得他再也不肯静心读书,于是,他辞别父母,开始云游。然而此刻,在这沉沉的佛号声中,他忽然觉得,一切的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限烟云,惟有这青灯古佛,只有这沉沉如梦幻般的佛号,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这天晚上,吴达观宿在云岩寺里。第二天黎明,当寺里早课的板子刚一敲响,吴达观即翻身起床,当僧人们在佛前齐齐排定,等待那一声引罄敲响之时,吴达观也悄悄地挤进了大殿,选一个角落站定。功课结束,吴达观问明住持的所在。径直寻去,举手敲响了住持的房门。住持正与一个僧人说话,见他进来,便问他有何公干。吴达现在住持面前跪了下来,说:
“不为什么,只为出家。”
住持看了看这服饰华贵一脸稚气的青年,说:“请把话说规矩点,佛前不可有戏言。”
吴达观说:“一言九鼎,决无戏言。”达观说着,解下身上所有的盘缠,尽数放到住持的佛龛前。
住持说:“你要出家做什么?”
达观说:“代佛弘化,不染一尘。”
住持认真地打量了他一下说:“既然要不染一尘,就请把你身上这件华服脱下来吧。”于是,吴达观果然就将那件华贵的袍服脱了下来。里面则是一件丝棉夹袄。
住持又说:“还有一层(尘)。”于是,吴达观又将那层夹袄脱下,待要再行脱去里面的俗衣,住持阻住了他,说:“那就还留一层(尘)吧,要知道,要做到不留一尘是很难的。”
就这样,住持选了一个吉日,替吴达现在云岩寺举行了剃度.为他取法名真可。
师父看出迭青年将来是个于佛前行大气候的人,一心要好好地度他,就让他在寺里闭门读经。一直到他二十岁后,才送他去受具足大戒。受过戒后,师父又打发他去匡庐、北京等地参闻佛法。几年的参学,让真可大开了眼界,学业也突飞猛进。就在这段参学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深深地打动了真可,从而使他由此决定了自己行持方向。在一个乡间小庙,真可无意间发现一个老僧整天伏在那里抄写经书。有人告诉他说,老僧一辈子都在抄经,抄完一部又一部,老僧发愿要抄完所有的大藏经,直到色身寂灭的一天。真可去看老僧时,老僧头也不抬地依旧抄经。山风吹拂着老僧古铜色的睑宠,一根银白的胡须落到老僧抄写的经文上,老僧轻轻吹去,继续写着他的一个个蝇头小楷。
在老僧的寮房,真可看到一本本装订成册的经书。直到天将黑尽,老僧收去了笔墨,才和真可说起话来。老僧告诉他说,他之所以发愿抄经,是有感于大藏经梵夹浩繁,讲读起来非常不便。而单篇成册,则无论讲经还是阅读,都方便多了。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真可的心中像大树一样地生根了:刊刻方册藏,以利于更多的修学者。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真可慕名前往山东即墨海印寺,拜会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二人一见如故,促膝畅谈达四十昼夜。
说到方册藏的事,憨山德清说,此项工程浩繁,费工费时难以想象,非几代人不能完成.法师对此事需有足够耐心。真可于是说到那一次在乡间小庙见到老僧抄经的事,真可说,以愚公之志,必能撼群山于倾刻间。憨山德清对真可欲刊刻方册藏的决心大加赞赏,于是。二人一同来到北京房山云居寺,想一睹房山刻经,以资借鉴。没想到却在无意间发现了隋时高僧静琬藏于雷音洞内的三颗佛舍利。
这一发现,令二人喜不自禁,在真可的请求下,憨山德清书写了《复涿州石径山琬公塔院记》的文章刻碑干云居寺旁。这件事惊动了朝廷,神宗生母李太后一向笃信佛教,听说发现佛舍利的事,当即请回宫内供养三日。三日之后,李太后将怫舍利归还云居寺,真可、德清重新供回于房山石洞内。
万历十七年,方册藏工程得到一些朝廷大臣的捐助,于五台山正式开工。由于五台山天寒地冻,刊刻者四肢垒被冻裂。几年后,方册藏不得不移于浙江杭州继续刊刻。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情,从而使正在进行的方册藏工程半途停工。一是真可的法侣憨山德清因“黄冠之难”被捕下狱,另一件事是南康太守吴宝秀因抵制朝廷矿税也被捕下狱。二人都是真可的好友,二人冤案都因宦官陷害而致。为了救助两位好友,真可北上进京,住进西山潭柘寺。在京期间,真可一边四处游说,一边上书皇帝.力陈事件真相。真可在游说中说到自己晚年“三大负事”:“老憨(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
由此而见真可的耿直和天真。而所述第三大负,则是指与憨山德清(亦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另外一位高僧是智旭)共同发起刊刻方册藏和续写《景德传灯录》一事。
由于神宗与母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混乱的朝廷内一时谣言四起,由于宦官从中作梗,真可不久即被捕下狱,其罪名是制作“妖书”,惑乱朝纲。
狱中的真可遭受到刑具和役卒的喝斥,最后被转至刑部,定下“坐左道罪”。得此消息,真可说:“世法如此,久住何为?”于是写下遗书交与侍者,随后跏趺而坐,安然示寂。时年六十一岁。
§§§第七节六世班禅巴丹益喜进京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北京紫禁城里一片忙乱。大小太监们奔前跑后,扯着他们尖细的喉咙指挥着那些工匠们把一批批从各地运来的礼品运到库里。离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还有一年的时间,各地派人送来的祝寿礼品就在皇宫里堆成了山,太监们正急着没地方存放呢。
有道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此刻,六十九岁的乾隆正坐在他的龙廷上批阅着成堆的奏折。忽然,一份奏折引起了皇上的注意,那是章嘉活佛写来的奏折.奏折上写明,为庆贺圣上七十大寿.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将干近日启程来京。章嘉活佛在奏折中特别提到六世班禅对维护中华统一所作的贡献。乾隆四十年(公元177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哈斯汀利用英国东印公司与不丹发生战争之机,派员擅自闯到札什伦布寺会见六世班禅,提出英国与西藏建立单方面联系、英方与西藏自由通商、要求到拉萨设驻藏代表等要求。六世班禅威武凛然,强调说,西藏属中国领土,英国与西藏的一切行为,均必须按照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
其实,即使章嘉活佛不提这些,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的一切早就了如指掌。
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六世班禅出生于襄地扎西则(今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则)地方。父唐拉,咒师出身t母尼达昂茂,系贵族宗室之女。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经札什伦布寺喇嘛寻访考察.七世达赖派代表会同噶厦政府官员共同确认巴丹益喜为前世班禅转世灵童。经乾隆皇帝恩准.次年,巴丹益喜于札什伦布寺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乾隆帝派中央特使与七世达赖的代表一起专程前往札什伦布寺祝贺坐床典礼。自此以后,六世班禅与中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章嘉活佛受中央委派,到札什伦布寺看望六世班禅,并一同商议西藏政教事务。乾隆三十年(公元1766年),乾隆帝遣使到札什伦布寺册封六世班禅,并颁给金册金印。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9年),六世班禅三十一岁时,乾隆帝又赐给了一颗用230两黄金铸成的有藏、满、蒙三种文字的班禅额尔德尼金印。
对于六世班禅即将来京,乾隆皇帝十分重视,颁旨要求必须做好隆重迎接六世班禅来京的一切准备。为了让六世班禅在京的生活不致有任何不适,乾隆下令必须按照札什伦布寺的格局于承德建造须弥福寺一座。“务将须弥福寿之庙内厢房赶在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前修竣,以备存放班禅先遣两千驮包及其众喇嘛居住。
断不可误期。”乾隆先后发出六道谕旨,催促驻藏大臣刘保柱专程前往扎什伦布寺与六世班禅商议入觐事宜,并征询章嘉活佛意见,确定迎接等事项。乾隆皇帝甚至想到,班禅长途跋涉,鞍马劳顿,谕令为他准备轿辇。当接到六世班禅确定启程日期后,又派索琳赴扎什伦布寺赐谕奖赏,谕令在六世班禅启程后,后藏事务由八世达赖看管办理等。乾隆还学习唐古特语(藏语),欲与班禅额尔德尼见面时叙谈。与此同时,乾隆又命宫廷画师专程赶往札什伦布寺为六世班禅描画法相,准备挂在建好后的须弥福寺内。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他们率随行人员2000余人,从札什伦布寺启程,一年以后,六世班禅一行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承德。当六世班禅走进那座完全按照札什伦布寺的格局建造而成的须弥福寺时,迎面的一幅画像顿时让他感动万分。画像中的六世班禅身着黄色僧服,头戴黄色僧帽,左手执佛经,右手施说法印,形态体现为正在为众生宣讲佛经。
承德避暑山庄,一次历史性的会晤终于开始了,乾隆特许六世班禅可乘轿直至殿前。六世班禅向乾隆行跪拜大礼,乾隆问道,喇嘛身体好吗?
一路辛苦了吧?班禅答道,托皇上洪福,一路无恙。乾隆说,朕年已七十岁,以如此高龄,幸见喇嘛,甚慰朕怀。从此中土佛法弘扬可期,四海人民得歌舞升平。说着,乾隆命人将自己用的珍珠串、玉如意和一条哈达赠给六世班禅。六世班掸再次跪拜,谢帝龙恩。次日,乾隆又玉驾亲临须弥福寿庙看望班禅,乾隆说,昔日五世达赖来朝,我祖特建黄寺以馆之。朕今特建热河札什伦布寺,以备喇嘛驻锡。不知喇嘛是否适意。六世班禅说,谢皇帝龙恩,一切就像在札什伦布寺一样。六世班禅对乾隆居然能用藏语与其对话甚为吃惊,乾隆说,朕欲与喇嘛对话,一年来一直在学藏语,但只能讲些普通用语,而经文奥典,仍须由章嘉呼图克图译述。班禅听罢,大为感动。
同年夏,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六世班禅。乾隆当即为班禅颁赐玉册玉印。乾隆寿辰这日,六世班禅和章嘉国师率僧众至避暑山庄诵经,为乾隆祝七十大寿,班禅进献重300两的金佛像一尊、佛案和菩萨画像8l幅、全套《甘珠尔》、重30两的金制护身盒、琥珀串珠三挂等物品,作为寿礼,祝福乾隆帝万寿无疆。
乾隆寿辰结束,六世班禅来到北京,由皇六子和章嘉国师陪同游览圃明园、大钟寺、颐和园、香山等地,为殿堂、园林、寺院开光加持。不久,乾隆又与六世班禅在香山昭庙会见,并向班禅献金如意、羊脂五香炉、宝体等;班禅也向乾隆进献佛像及袈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