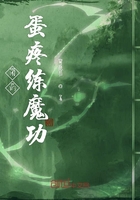阳光明媚,白云两朵。
沈七站在园门前的梨树前,面容肃静,和平时有几分不同。他身后是才领了去的玉蟾。
如画莫名地觉得有一丝尴尬不自在,却不知为何,赶紧两步,和沈七说话。
“这么快就把人送回来了?”玉蟾要是回来,她倒是完全有理由,不必留着老六了。
“不过是路过此地,特来打声招呼。”沈七说完抬起头,看着贝长青,“两人相谈甚欢,不知在谈些什么?”他行事向来无所顾忌,有什么话都是说出来。
他可以对不同的女子好,却不能让自己中意的女子和别的男子说话。
沈七却是忘了,柳如画虽是他在意的女子,却不是属于他的,按理应是沈恭言的。
吃味儿也轮不到他。
沈七往前走几步,偏要在如画和贝长青中间站定,似乎这样才能让他满意。
“要是没什么事,贝大夫就请回吧。”
贝长青后退半步微微颔首,“在下还没有完诊。”
沈七白他一眼,扯了扯如画的袖子:“嫂子,人心难测,你该有所防备。尤其是你这样貌美的女子……”
“哈哈!”她没有忍住,哈哈笑起来,“七弟,别闹!贝大夫是来给我看病的。”
“好,那尽快诊治!”说着,沈七便邀请如画与他一同进屋。
贝长青在厅内为如画诊脉,沈七则坐在一旁,认真瞧着,平日里看见丫鬟都要打趣几句的他,见到云芝和采秀都跟没看见一样。
“病情大好。”贝长青略一斟酌,“该换药了。”采秀立即取来纸笔,让他写单子。
在沈七虎视眈眈的目光下,贝长青苦笑一声,去了。
“七弟,为何对贝大夫如此不客气?我的病可是他治好的!可以算是我的半个恩人呢。”
沈七越发不快,喊道:“采秀,下次贝大夫再来,去我院里通传一声。”
“你要做什么?”如画皱眉。
“他来,我就来。”
合着是要当监工。
她连连摇头,“你可有这闲功夫?不参加科举了?”府上一直请着先生,指点沈七的学业,虽自学亦能成才,沈夫人却从没断过请先生的钱。
虽说学了这么多年,可沈七却从没有真枪实弹上过考场。他自己不愿意,每次玩赖便能说服沈夫人,再而由沈夫人去跟沈从德说情。
好歹是小儿子,管教上难免松懈。
这时,沈七竟然回头看了玉蟾一眼,略显无奈地说:“还未到火候。须得等人想通了才行。”
如画不解:“这话是怎么说的?”
“不说这个了。”沈七站起来,不知从哪里取出个盒子来,“我这里有个宝贝想给你。”
精致的暗紫色烤漆匣子,里面躺着一支笔毫,笔杆是象牙做成,上面镶了碎玉和,贴了金色纹路,笔端坠珠。只一眼便能看出价值不菲。
如画从未见过这么精致的画笔,忍不住想要伸手触摸,却在半空中停下来。
这支笔,如果能保存到现代,怕是无价之宝了。可惜,笔毫难寸,上面的毛大多无法保存。
似是知道她的犹疑,沈七笑着取出来,端立着献给她。
她接过在手背上点了两下,不自觉说道:“笔锋尖锐,万豪齐力,毫毛饱满,弹度适中。好笔!”
“我可是松了一口气。生怕这间礼物送得不好。”
“就为了一个玉蟾,便送这般贵重的礼物,怕是有些过了吧。”
沈七闷笑,却是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似是很享受这种状态,“我送你的礼物,难道还需要许多说法不成?”
她摇头,又把笔毫放了回去,“我不能收。”
“为什么不要?你不是喜欢画画?你有了它好比猛虎添翼,如此好事为何要拒绝呢!”沈七不快,瞬间抬起了手臂,“你不要,我便砸了它又如何?”
“你敢!”如画瞪起眼睛。
“你不要,我就砸了它。”沈七还是头一回送女子东西被拒绝,心里受不了。
她只能半哄半劝,“我也想要,可是我根本没有能与之匹配的东西,就算把我的衣裳收拾都卖了……”
“不说这些。你嫁进来,根本没有陪嫁,四哥也从未给你买过一件东西。哪里有什么首饰?”
难得,他知道这些。
如画感慨,“我怎么能白要你的东西?”她拿什么换?
“你只管接受了,便等于是还了。”沈七后退一步,像个孩子一样倔强。
很少说有嫡子给庶嫂送东西的,就算是两人相见,大多也是庶嫂微微诺诺,这回子倒让一旁的采秀和云芝吓了一跳。尤其是云芝,她可是知道自家的这个小霸王是什么人。蛮不讲理起来,连夫人也要为他哭。
都说一物降一物。却不知柳如画是不是能降住他的。
“你要是敢摔,再也别踏进我的院门。这玉蟾也早早给我送回来。”她面色一紧,真的来了火气也够吓人的。
沈七心里莫名一颤,把匣子往桌上一放,掀起衣袍一角,疾步离开。玉蟾略带深意地瞧了她一眼,也跟出去了。
柳如画却不管他们,小心翼翼地捧起匣子,喃喃自语:“这么好的东西,要真是摔了,我非得揍得他屁股开花。”
她是真宝贝这件东西。
听见屁股二字,云芝别过脸去,脸色微微发红。采秀则是轻咳一声,过去把门关了。
玉蟾一声不吭,跟在后面,突然撞了一下,这才发现沈七停下来了。
“我送她东西,她为何不愿收?难道还在等着四哥?就算送,怕四哥也只知道送她酒。她喝吗?”
玉蟾白了一眼,“四少奶奶并不是不想要,怕是不想白要。无功不受禄,便是这个缘故。”难得,玉蟾开口说话,还是替人说好话。
“她和我,有什么客气的?她想要什么,凡是我能给,我便不会自己留下!”
以前院子里的丫头们在他跟前说几句好话,他也是都应允的。可这种话还是头一回说。玉蟾并不以为意,沈七自己吓了一跳。
自己愣了一会儿,又笃定发誓似的说了一遍:“是了!凡是她要的,我能给的,我就给!”
若是有人听了,一定以为他的拗脾气又上来了,一般也不会太当个事。却不知余下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做着这一件事。或者是因为这个誓,或者是因为别的,反正这一次的拗劲没有如往常那般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