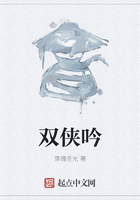林宗心中起了波澜,感情一事,不懂的人便是不懂,然而若有一段感情叫你刻骨铭心,那么你便轻易能看穿他人在他自己故事里的甘愿与苦痛。
妖怪重兄弟姐妹不重父母,但妖怪所重者,没有是非道德,不像人间以“为她好”之类的理由为名,习惯性地要求他人以自己的原则为标准。
对于林宗来说,若有人欺负唐夏,若唐夏厌恶某个人或者若有世物威胁到唐夏,那么他一定会将这些阻碍铲除干净。
然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唐夏不甘愿的基础上。
既然唐夏甘愿承受,那么他没有理由阻止。
妖怪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林宗怜爱抚摸唐夏柔顺长发,轻声道:“那么你就留下来陪他。”
“嗯。”
兄妹俩流离失所多年,如今重逢,各自有各自的轨迹,自然有多呆了一会,直到唐夏怕出来太久引起薛鸿铭猜疑,这才匆匆告别,走时不忘捎带那些沿途顺手猎杀到的“食材”。
林宗凝望着唐夏离去的背影,沉默不语,仍然伫立在月光山林中,直到唐夏没了踪影,他才扭身,然后似乎想起什么,扬手一张,林间有六七道寒芒急射而来,落在他手中。
赫然是一柄柄名剑。
林宗微微蹙眉,思索要随身带着这些名剑着实不便,于是手腕微抖,凌厉妖气硬生生将这些名剑全数震断,顺手往草丛一扔,扬长而去。
剑既然断,人自然死。
这些都是在执法组奉命来捉拿薛鸿铭唐夏的名剑师,倘若不是林宗,恐怕两人面对的压力会翻一番。
……
……
唐夏回来时,天色并不晚,时间恰恰到了吃饭时候。还未进屋,便惊喜发现薛鸿铭已经燃了一团盛大篝火,火势噼里啪啦作响,火星与他发梢在晚风中飞舞飘摇,如萤火,如细柳。
“呵,很自觉嘛?”唐夏愉悦笑着走来,琼鼻又嗅了嗅,讶然道:“这是……酒味?”
薛鸿铭笑道:“你看!”
他真的从背后掏出一壶酒来,酒味香醇,但混着一点奇怪味道,称不上好酒,但胜在存放的时间很长。
唐夏惊喜叫道:“你从哪里找来的?”
“你管我从哪里找来的?”薛鸿铭眨眨眼,揶揄笑道:“你只要知道,有肉无酒是个很悲凉的事。我们从此浪迹天涯,要终生被人追杀,已经够悲凉,经不起再多一点悲凉。”
唐夏掩嘴轻笑,坐在他身边,挽着他的臂弯,说道:“可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悲凉啊。”
“呵,你真乐观。”
火势已经足够大,薛鸿铭在佣兵团亦常常风餐露宿,效率极高,不一会便将一只山鸡烤得香味扑鼻,令唐夏在一旁垂涎欲滴。好不容易等到薛鸿铭撕下一块鸡腿,便迫不及待地撕咬一口,毫不怕它滚烫。
薛鸿铭看她吃相如此不雅反而觉得可爱,微笑递过酒壶,说:“来,大口喝酒。”
唐夏横了薛鸿铭一眼,一点不客气地抓过酒壶,仰起小脸,咕咚咕咚地果真大口喝酒!喝了一大口,玉手一抹嘴巴,却见薛鸿铭正眯着眼看她,不觉感到有些诧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薛鸿铭眼里闪过一抹古怪,别过脸去,说道:“没什么,只是觉得……”
唐夏双耳竖起,促狭道:“觉得什么?”
“……”
“说呀!”
“我也……不知道。”
唐夏恼怒地皱起了细长的眉,没好气地将酒壶塞到薛鸿铭怀里,嗔道:“你喝!”
薛鸿铭一言不发,仰首大口大口地喝,他喝的如此凶猛狂野,大股大股的酒从他唇边沿着下巴流下,沾湿了他的衣襟,勾勒出他壮硕结实的胸膛。
转眼之间,一壶酒竟已被喝掉大半,且薛鸿铭喉咙仍在滚动,不肯停歇。
唐夏暗吃了一惊,这才觉得薛鸿铭今夜有些不对劲,失声叫道:“鸿铭你……”
她娇腻的声音戛然而止,小脸剧变,睁圆杏目。身体内,血液似乎毫无预兆地沸腾,骨骼仿佛正在突破禁锢,正在一点点地生长。
这、这是……?!
唐夏心中大骇,这是她体内妖狐血脉不稳的迹象,并且眼看就要控制不住。然而她面上仍然保持从容镇定,浅浅一笑,对薛鸿铭说道:“你等我一下。”
然后她即刻起身,只想快些离开这里,不叫薛鸿铭见到她生出狐尾。不想刚站起身子,手腕便被有力抓住,诧异扭过头去,却见薛鸿铭仰头,眼眸凝定而似有灼灼热浪,又似极度冰寒。
薛鸿铭声音沉沉地问:“你去哪?”
唐夏心中咯噔一下,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平常,白了薛鸿铭一眼,故作羞涩道:“上厕所呀,怎么,你要……跟来吗?”
实则她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挣开薛鸿铭的手,因为体内妖狐血脉已然到了爆发边缘。
薛鸿铭默然片刻,颤声说道:“唐夏,酒里有血,我的血。”
说这话时,他仍然仰着脸望着唐夏,唐夏见他的眼眸凝实,幻觉那里最深处竟似一点刺人锐利的光亮,锋锐得像一把刀,且来势汹汹,凶狠异常。
她脸色终于保持不住从容,瞬间变得苍白如纸,从来镇静如她,竟然此时如遭雷击,只愣愣地看着薛鸿铭的目光。
每看一秒,心便痛一份,便恐惧一分。
偏偏她不知是何原因,本能地、偏执地与薛鸿铭对视,等待他一个答案。
薛鸿铭面容同样苍白,缓缓站起身,一手抓着唐夏皓腕,一手探进唐夏衣内,摸出一个小小物体,唐夏瞥眼看去,正是协会专用的小型窃听器,于是心中了然,感到极其苦涩。
那件窃听器,因为是不久前与薛鸿铭欢好时,薛鸿铭偷偷放进她衣内的,而她竟然没有察觉。
“我从来没想过是你,直到那时苏媚在日本叫你小狐狸时才感觉到奇怪。”薛鸿铭颤抖着唇,然而手起如电,霍然抓住了唐夏天鹅般修长的脖颈,眼中血丝密布如蛛网,满是魔影执念,住着狰狞凶戾的兽:“我于是开始留心观察你,我想这一次一定要是我错,可是我竟然没错。”
“唐夏,林宗……在哪里?”
唐夏绝美的脸容有不可掩藏的哀戚,她定定望着薛鸿铭,任用薛鸿铭卡着她的脖颈,良久之后,轻柔且认真地说道:“薛鸿铭,我爱你。”
“这世上人人都可以爱我,但惟独你不行。”薛鸿铭紧紧咬着牙,身体微微颤抖,似在呼啸冷风中瑟瑟发抖,他盯着唐夏,眼眸血红:“林宗杀我父母,但其实害了我全家的……是你。”
“你无父无母,因为你天生就是被遗弃人间的妖狐,收养你的就是孙不念,所以你一早就知道他是妖,之所以不告诉我,不仅仅因为怕我会像今日这般闯下弥天大祸,你还怕我知道你是妖狐,是林宗妹妹这样可怕的事。”
“孙不念在协会这么多年,除了那几个人,再没有名剑师知道他是个妖怪。所以他一定有某种秘法能够压制自己的妖气,所以在你身上也下了这种秘法。”
“那晚你就在我家附近,林宗感应到了你的气息,但因为秘法的原因,他感应的不是很准确,于是出了偏差。偏偏我母亲身负黑凤凰血脉,胎内未出生的妹妹亦有妖气,林宗便以为……我母亲怀的妹妹便是他投胎人间的妹妹。”
“所以他剖开母亲的肚子!才有了我们一家反抗之下惨遭毒手!才有了苏媚控制我吃下至亲血肉!而我从此只能在憎恨中安身!!”
“而你……收养了我,究竟为了什么?因为心怀怜悯仁慈,还是因为心中歉疚有罪?!”
“唐夏,我说得……对不对?”
他睁着血红的眼盯着唐夏倾城倾国的小小脸孔,眼中含泪,偏偏仍然倔强不让它流下,仍然杀气腾腾,满是恶煞!
唐夏以沉默回应。
沉默即是答案。
薛鸿铭觉得心碎,他的心曾经碎过,这十七年来,唐夏亲手一点一点地将它修补,好不容易勉强缝好,如今……唐夏亲手又将它摔碎!
他想,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将它缝补,他留着一颗心,其实已经尽成废墟,弃之不得,重建不能。
人生而于世,原来真的是在赎罪,承受苦难。所有欢愉,不过是为了让最后的苦难使得更痛苦。
他嘶哑着声音说道:“唐夏,我再问你一次,林宗……在哪?”
唐夏精致面孔扭在一起,明丽的眼与细长的眉颤动不休,她落下了泪,泪滴晶莹,每一个见到的人都会心如刀割。
但薛鸿铭的憎恨使他心如铁石。
唐夏说:“鸿铭,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你必须告诉我!!”
薛鸿铭忽然狂怒嘶吼,陡然沉寂的四周,红雾飘动,血滴自四面八方悬浮而上,每滴血都释放着幽蓝电流,彼此相连,仿佛一张巨大电网将这片山林吞没!所有电流,最后都涌入薛鸿铭掐着唐夏脖子的手,灼灼热度与煌煌明光,映照唐夏的脸孔哀戚悲怜中又有惊骇恐惧!
御气决……宁碎。
“鸿铭,你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