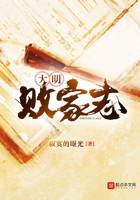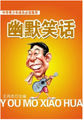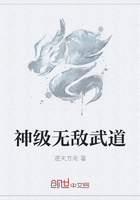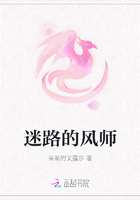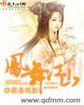旁边的乘客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把另一只鞋也丢掉,老人说:“这只鞋子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如果一个人正好从铁路旁经过,他就可以得到一双鞋,而不是一只鞋。”
感思寄语:
与人为善,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和关爱别人,对你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却往往能让别人过得开心一点,给别人带来幸运。有能力令别人快乐,才有能力使自己快乐。
琳达最后画的一幅画:琳达·柏提希完全献出了她自己。琳达是个杰出的教师,但她感觉,如果她有时间的话,她宁愿去创造伟大的艺术和诗篇。在她28岁那年,她开始有严重的头痛现象。她的医生发现, 她有个巨大的脑瘤。他们告诉她,手术后存活的机会只有2%。所以,他们没有立刻帮她开刀,先等6个月再说。
她知道她相当有艺术天赋。所以在这6个月中她狂热地画、狂热地写。除了某一篇以外,她所有的诗篇都在杂志上刊出来。她的画作也都被放在一流的艺廊中展售,除了某一幅以外。
在6个月结束时,她动了手术。手术前一夜,她决定完全捐献自己。她签了“我愿意”的声明,如果死了,她就捐出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给比她更需要它们的人。
不幸的是,琳达的手术夺走了她的生命。结果,她的眼睛被送到马里兰州贝瑟丝达的眼角膜银行给南加州的一个领受者。一个年轻人,28岁,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这个年轻人深深地感恩,写信给眼角膜银行致谢。虽然已经捐出了3万个眼角膜,这是这个眼角膜银行所接到的第二个“谢谢你”!
进一步地,他说他要感谢捐献者的父母。孩子愿意捐出眼睛,他们也定是好人。有人把柏提希的家的住址告诉他,他于是决定飞到史代登岛去看他们。他来时并没有预先通知,按了门铃,自我介绍以后,柏提希太太过来拥抱他。她说:“年轻人,如果你没什么地方要去,我丈夫和我会很高兴与你共度周末。”
他留了下来,当他环视琳达的房间时,他看见她读过了《柏拉图》;他曾用盲人点字法读过《柏拉图》。她读了《黑格尔》;他也用盲人点字法读过《黑格尔》。
第二天早上,柏提希太太看着他说:“你知道吗?我很确定我曾在哪儿看过你,但不知道是在哪里。”忽然间她记起来了。她跑上楼,拿出琳达最后画的那幅画,它是她的理想男人画像。
画中人和接受琳达眼睛的男人十分相似。
然后,她的母亲念了琳达在她临终的床上写的最后一首诗。它写道:
两颗心在黑暗中行过
坠入爱中
永远无法获得彼此的目光眷顾。
感思寄语:
爱能够创造奇迹。爱使彼此的心灵达到最大的默契,爱能激发一个人生活中的勇气和灵感,爱使真挚的情感永存人间。
善良母亲的“身教”:“我越来越醒悟了,觉得这世界就是一个竞争残酷的角斗场,不狠又不善斗的人肯定吃亏! 但我这辈子亏就亏了,便指望儿子托马斯和加菲尔德千万别和我一样,要做就做个硬汉铁人,特别是加菲尔德。于是我从小灌输给他们‘恨’和‘斗’的哲学。在我的精心培训下,加菲尔德6岁时,我的‘教育’就初见成效,比如,他不太会哭了,在有人夸他乖巧时,他会像受辱似的反驳,‘我不乖,要乖你乖去吧!’他会跟人以牙还牙了……”这些成果使这位 母亲很骄傲!但这位母亲邻居家的儿子阿尔包利显然也接受这种“教育”,但他比加菲尔德要“杰出”得多,这使得加菲尔德的母亲很有点妒忌。
阿尔包利比加菲尔德大1岁,他继承了他父亲粗壮的体魄和他妈火暴的性子,他是这里的孩子王,很有点儿无法无天、生死不怕的劲头,打架时即使被别人压在底下了,还要反问上面的人:“说,下次敢不敢了?”至于像扯小姑娘的辫子,掐小男孩的雀雀,踩死人家的鸭子,淹死人家的兔子等这类恶作剧,更是数也数不清了。还敢犯上作乱,跟大人对骂,吐大人口水。附近的人对他真是又愤恨又叹气,但毫无办法。
加菲尔德在妈妈的教育下,虽然知道跟阿尔包利针锋相对,但总恨自己体能不如人,几乎每仗必输。有两次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次被推下楼梯,额上还被划过一刀,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加菲尔德的母亲唯一欣慰的是——“尽管如此,我儿子也没有哭,只是受伤时像狼似的叫过几声。”
“你儿子会不得好死!”每回加菲尔德的母亲和这里几乎所有的女人一样,在跟阿尔包利他妈骂街时都这样诅咒过,而后来的事实却不幸真的被大家言中了。那年初夏,阿尔包利第一个跑到深潭里去游泳,结果被淹死了。或许他根本就不会游泳。总之,尸体两天后才浮上来,情景惨不忍睹。
“哼,这下阿尔包利真的死定了!下一个孩子王就是我了!”6岁的加菲尔德终于胜利了似的宣告。这时,这位母亲心里猛然一惊!一下子,她便全盘否定了她一贯奉行的那种所谓硬汉教育:“我是在害孩子啊!一个没有品德的孩子将来又有什么用?孩子还小,我怎么也不懂事?”
这位母亲深深地责问自己后,她悄悄把儿子领到阿尔包利被淹死的那口深潭边。当时水天阴郁,凉风无声,芦苇萧萧,树木森然,归鸟黑影一样飞过,潭里像笼罩一层鬼气。儿子下意识地偎紧母亲。“阿尔包利就淹死在这儿。”她对儿子说,“你知道什么叫淹死吗?”
“不知道。”
“好,闭上嘴,捂住鼻子,不准透气,看能坚持多久,我记时。”
加菲尔德照做,但很快他就憋不住了,放手张嘴,劫后余生似的大口喘息。
“你获救了。”她说,“可阿尔包利没有,他就这样憋下去,水还直往他肚里灌。他往下沉,他蹬脚,喊救命,可没人听见。不,他根本就喊不出声。他不想死,他害怕,他求饶,可是不行……”
加菲尔德大睁着眼望着阴森的水潭。
然后,这位善良的母亲把儿子带到阿尔包利家门口。阿尔包利的妈妈嗓子早就哭哑了,可她还在哭。
“她是世界上最伤心的妈妈。”她说,“没人喊他妈妈了,她讨厌你们,可她爱阿尔包利,就爱阿尔包利。”
许多女人在屋里叹息着,还上前劝慰着那个绝望的阿尔包利的妈妈。“你看,”她对加菲尔德说,“这里所有的人都不恨他了,大家都很伤心,真的伤心。试想,要是你也死去……”
“我不会死……”小加菲尔德惶恐又茫然。
“可阿尔包利死了。”她说,“他回不来了。你会继续长大,可他不行了。”她抚摸着儿子额上那块疤,“他甚至不能再跟你打架,也来不及跟你好了,这是阿尔包利留给你唯一的纪念。”
母子俩走进阿尔包利的灵堂。微暗的烛光下,阿尔包利在骨灰盒上的相框里憨厚地笑望着他们。母亲神态严肃,很郑重地给阿尔包利鞠躬。这是这位年轻的母亲平生第一次给死者鞠躬 。
她要儿子照做,儿子也做了。
“想跟阿尔包利说几句话吗?”母亲悄声说,“他能听到的。”
“阿尔包利……”加菲尔德讷讷地说,“我不恼你了,我跟你好……当时我要是在潭边,一定会拉你上来,我不会水,我就喊人,大声喊……”他的泪珠滚落下来,在烛光下晶莹发亮 。回家的路上,加菲尔德不解地问:“妈妈,你今天怎么了?平时不是老教我对人要狠和敢斗吗?怎么突然很仁慈了?”
母亲一把拉住加菲尔德,非常愧疚地说:“孩子,妈妈错了,请你原谅。不但我错了,也让你跟着错了!阿尔包利的死告诉我,人的一生很短促,如果总是拼勇斗狠,一点道德都不讲,尽管他死后别人原谅了他,但他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
“难道一个有品德的人就不会死吗?”加菲尔德问。
“不,当然会死,但人们对他的悼念却和阿尔包利的不同,对他,别人只是因可怜她的母亲而原谅了他,可一个有道德的人虽然也会死去,但人们会永远地记住他的。”
“为什么要记住他?”加菲尔德问。
“他们从不和别人打架,他们虽然很有力气,很魁梧,但他们却只会帮助人,关爱人啊!”母亲动情地说。
“可……可我已经这样了,我还能改好吗?”加菲尔德问。
“当然能!这样吧,加菲尔德,妈妈也错了,就让我们一起改吧!咱们比赛,看谁改得快,改得彻底好吗?”母亲问。
“好啊!”加菲尔德高兴地说。
这位母亲说到做到,从此对人温文尔雅,讲究礼貌,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总是抢在最前头!
在这位善良母亲的“身教”之下,这个名叫加菲尔德的小男孩,更是不愿落在母亲的后面,他追随着母亲那迈向品德圣殿的脚步,一步步地成长为一个拥有高尚品德的人,成了人人皆知的楷模。
后来,他还凭着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良好的品德,当上了美国的第二十任总统,他就是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
感思寄语:
世界并不是一个竞争残酷的角斗场,凶狠善斗的人占不到任何便宜;只有温文尔雅、讲究礼貌、肯于帮助人、关爱人的人才能真正地征服别人,赢得别人的支持。
探险队中的幸存者:一次,一支探险队在考察溶洞时,5人被困洞中。他们尝试了各种逃生的方法,都失败了。洞外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但估计需十余日方能打通。而此时他们的干粮、水都已用尽,无法维持到救援成功的时刻。
饥饿、恐惧、绝望……就像这洞中的黑暗团团包围了他们。他们将身边能吃的东西,如皮带、皮鞋、衣料,甚至洞中的土等都弄来吃了。再也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他们只好偎依在一起,相互安慰着。死亡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
队长詹尼福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年轻、能干、活泼,大学毕业后来到探险队,被大伙推选为队长。
大伙奄奄一息,如果救援不及时,5人将面临死亡。面对这种无奈局面,詹尼福左思右想,终于做出了一个痛苦决定:与其大伙同归于尽,不如牺牲自己,维持他们的生命。此刻他想得最多的是帕娅,一位美丽的姑娘。他们相爱已多年,如果他死去,帕娅将悲痛欲绝。然而,他除了牺牲自己救队友已别无选择。
当詹尼福准备把这个决定说出来时,他忽然有一个想法,想考验一下4位队友,看谁能为了别人,甘愿牺牲自己。
于是他对队友们说:“我们必须牺牲一人用他的血肉来维持其他队友的生命。不然……你们……谁愿意牺牲自己,奉献出躯体?你们谁愿意……”
他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死一般寂静。他打亮了火机,看到的是队友们一张张恐惧的脸。
明天,詹尼福决定自杀,自己的血肉能供队友将生命维持到后天或更长时间,等救援队的到来。詹尼福为自己高尚的决定感到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