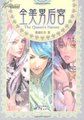我需要林北风给我一个解释,完完整整的,不掺任何虚假的解释。
他明知是我,却弹贝斯、举着字,和那些起哄的人站在一起,帮别的男生,向我表白。
过了好半天,突然醒悟过来的我翻身起来跳下床,抓起衣服飞快地往身上穿,舍友们看着我一脸吃惊,秦谦谦吃着零食笑我:“对嘛,总得去面对。你一下去,就有轰动性新闻了。”
懒得理她,我匆匆穿好衣服一口气跑下楼,人群中有人认出是我,纷纷兴奋地叫着:“来了,来了!”
穿着格子外套、一脸憨憨笑容的程家辉捧着鲜花惊喜不已,大叫着:“薄砂!”
我直奔过去,擦过他的肩头,原地转了一圈后,却不见林北风的人影。
不过一会儿工夫,他去了哪儿?
我站在原地,像个疯子一样大叫:“林北风,林北风!你给我出来!出来!”喊着喊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大伙儿都看着我,一脸看不懂的表情。程家辉小心翼翼地来拉我的袖口,被我一把挥开:“滚。”
简短的一个字,令那些写着字的牌子纷纷放下,几个男生看我骂他们老大有些不乐意,想对我比划被程家辉拦住,他的脸也如同手里因拿得太久而枯萎的玫瑰花一样,颓败着,却还挂着勉强的憨厚的微笑:“薄砂,你在找林北风吗?”
我猛地扭过脸拽住他的衣服,目光直逼向他:“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他,我是要找他。我等他七年了。”
那天的闹剧是这样结束的。女生宿舍楼下拥堵了太多的围观者,以致于惊动了宿舍管理科的阿姨们,她们穿着蓝色制服从办公室跑出来,有的手里还掂着扫把。胖胖的宿管科长双手叉腰一吆喝,那些围观的人应声而散。程家辉手中的玫瑰花被人群挤得纷纷零落,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也掉在地上被无数的脚踩过,唯独林北风举过的那个“爱”被我抢着捡起来,抱在怀里。
程家辉说,可以带我去找林北风,于是,我跟着他走了。
夕阳已渐渐收敛,最后一点苍白的光线也消失在远处密密麻麻的建筑群中。气温愈发低了,身上单薄的夹克并不足以抵御街上的寒风。
走了很远的路,我跟在程家辉的身后,至少走过三条街,转过四个路口,他不说话,我便也紧闭着嘴巴。
走到一条长满梧桐树的街道时,他突然转身,黑黑的眼珠望着我:“冷么?”
我摇摇头,却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他没说话,脱掉厚实的格子外套递给我,目光欲言又止:“其实,昨天我就该想到的。林北风认识你…不然,他也不会问那么多…”
我没接衣服,有些酸楚地抬头看他:“你们怎么认识的?”
原来,和当年约定的一样,林北风考的也是北京的大学,只不过和我、叶未央都不在一个学校。去年夏天,程家辉组建的乐队招人,别人便向他介绍了贝斯弹得不错的林北风。
程家辉指着掩藏在一大片苍灰色树林后的一座厂房,微笑着说:“我们乐队的训练场就在这儿,这个时候,林北风应该在。”
我拔脚便朝前面跑,只穿了件衬衣的程家辉拎着衣服站在原地,眼里有一点悲悯的凉意,他轻声说:“你从侧门进,慢点跑,小心摔倒。”
心里突然有小小的感动,我回过头去,男孩已经转身,沉默的背影消失在渐渐黯淡的暮色里。
像是一座废弃的工厂,青灰色的墙身,大概三四层的样子,房顶还伸着一只生锈的大烟囱。天,慢慢黑下来了。我在晚风中奔跑,可以听到自己气息的呼哧呼哧声。
从铁栅栏的侧门一进去,果然听到一阵琴声,不是聒噪的电贝司,象是钢琴。悠悠的流淌在有些荒凉的夜色里,那琴音也显得有几分凄怆。
一层的厂房大门紧闭着,我推了推,好像从里面锁上了。
“林北风!”我大喊,无人应声,钢琴还在缓缓流淌。
“你出来,我是薄砂!林北风!”琴声突然停了,四周顿时静默,惟听到风掠过树梢的沙沙声和远远的汽车声。
厂房是密闭的,唯有两米高的地方有几扇窗户,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的。
仍不见有人出来,我四处看看,见身后的树林里有一堆废弃的断砖,便弯腰拾起一块,用力朝高处的窗户砸去。
“砰!”玻璃窗应声而碎,碎渣四下溅开,一片蹦到我的脖子上,划破了皮肤,隐隐作痛。
我蹲下身子,有些无助,却哭不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门吱咛一声开了,一个瘦高、颀长的身影缓缓地挪出来,在已经暗淡的夜色里,借着远处路灯的隐隐灯光,我认出,那就是他。
“薄砂,你哭什么?”一截红色的火光闪在他指间,那个发出声音的人慢慢向我走来,身上带着凄清的薄薄烟草味道。
我突然浑身无力,想站起来却跌坐在了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我没哭,你是林北风吗?”我抽抽鼻子,轻声问。
一只手轻轻落在我的额头,掌心的温度缓缓地渗入心头,象是走过漫长艰辛的寒冬,忽然之间,一抹春风就融化了冷痛。
“七年不见了,薄砂,好想你啊。”他在我面前蹲下身子,一张出落得几近完美的年轻面庞极近地挨着我,长长的睫毛下,乌黑的瞳仁里是我看不清的神情。
“你还…你还记得我?”我小心翼翼地抬头望着他,他唇角微陷,象是安静地笑:“傻瓜。”
“起来吧,这里凉。”他抽走放在我额头的手,转身狠狠抽了一口手里的香烟,然后弹出去。火星倏忽而灭,我的心也跟着游走,毕竟是多年不见,他改变许多。当年的如荷少年,也是会抽烟弹琴沉默的内敛男子了。
他站在铁门下等待我进去,满肚子疑问尚来不及问,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传入耳中,他等我进门后,便去拿搁在钢琴旁边的一只黑色手机。
“你在哪里?”他沉声问,脸上的表情如门外暮色般阴沉。
“我只是问你现在在哪儿,和谁在一起!”音调突然提高,他像快遏制不住隐怒,左手紧紧握着一只烟盒。
电话那头不知在说什么,但我猜一定是个女的,能让林北风这么在乎和生气,难不成是…我的心瞬间低落下去,重逢的喜悦被打消了七八分,这些年的委屈也一股脑地涌上来。
等他一挂电话,我便走过去,定定望住他:“我需要你的解释,哪怕是编造的理由。”
“什么?”他把电话放到一边,有些意外地看着我:“解释什么?”略作思考,他哦了一声,眉头微微跳动:“你是怪我帮程哥追你吧。”
“怎么说呢。”他在那架黑色的钢琴前坐下,右手随意按住一串音符,脸上带着薄薄的笑容:“我从他那听说你的名字,但不敢确定就是你。”
“你可以先来看一看…好吧,你压根没想过找我。”我黯然地苦笑。
林北风侧过脸,五官的轮廓在幽暗的灯下显得朦胧,他垂下眼帘:“所以我才答应去你们学校,不过,没想到真的是你。”
他轻轻弹起一首曲子,说:“程哥那人其实挺不错的,你可以试试…”
“够了。”我霍地将手按在琴键上,心底的痛蔓延上来像一股火要烧到眼睛里:“谢谢你。老同学,谢谢你的关心。”
我没意识到自己的嘴唇在打哆嗦,可能整个身体也在哆嗦,我只是像一截木头般机械地迈动双脚,往门口走去。
而他静静坐在那里,琴声止了,一层薄光罩在他身上,气氛无比的压抑。
人是很会自欺欺人的动物,很多年后,我记起的都是和他在一起温暖美好时的场景,而那些伤害、冰冷、眼泪,只是彼时疼痛,一旦有所抚慰,必将悉数淡忘。
我便是这般毫无出息的女子。那晚从林北风那里出来时,我一人走在初春的街道上,没有月光,路旁高大青灰的梧桐树在路灯下投成一片片诡异恐怖的形状,我的心,像被凿穿了无数个孔,寒风吹进去,又出来,带走了周身的所有温度。
回到宿舍,将睡时,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薄砂,对不起。”
短短五个字,没有署名,我猜测是林北风,但也可能是程家辉。我没有回复,累了,我真的很累了。
周六一大清早,我就接到爸爸的电话,他说今天是叶淙灵的生日,要我回家一起吃饭。
“有这个必要么,只怕回去也没人做饭吧。”我坐在阳台上边晒太阳边修指甲。薄云天有些惭愧地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准备了一桌好吃的,就等你和未央过来。前段时间她确实忙,没照顾好你,以后就不会了,你还是多回来住吧。对了,爸爸准备了礼物,待会你给她,就说是你为叶阿姨特意准备的。”
我嗤地冷笑出声:“您可真够体贴入微的。”啪地挂断电话,望望远方,天很蓝,春天的风柔和地拂在脸上,我突然决定,如薄云天所愿,回家为叶淙灵“庆生”。
刚进胡同就闻到浓浓的香味,我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装着几件脏衣服和路过玩具店时我特意为叶淙灵挑的“礼物”。这时,身后汽车滴滴的鸣笛声将我惊了一跳。
回头望去,一辆本地牌照的白色宝马车在胡同口停住,车里坐着年轻的一男一女,不一会儿,女子从车中下来,一双穿着黑丝袜的修长的腿,上面是紧身包臀短裙和枚红色羊皮小坎肩,盘起一部分的波浪长发恰到好处地映衬着那张年轻娇俏的美人脸。
“拜拜哦,江少。”她笑容妩媚,若不是声音熟悉,我又差点没认出是未央。
“好,随时电话。”宝马车里的年轻男子戴着墨镜,衣着鲜亮,一看就是富家子弟。
我站在那里,两人分别后,未央款款走来,看到我微笑着招招手:“砂,最近好吗?听说谈恋爱啦?”
“呵。”我干笑一声,看着远去的宝马车,笑问:“男朋友?”
她娇羞一笑:“不是啦,普通朋友而已。”我没再多问,说话间两人前后进了家门。
薄云天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着,叶淙灵将自己和家里都装扮一新,见我进门立刻亲亲热热地喊:“砂砂可算舍得回来了。前段时间忙,你爸怪我没照顾好你呢。”
我淡淡道:“怎么会,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完这话心里就不是滋味,薄云天从厨房出来,笑着叫我道:“砂砂来给爸爸搭把手。”
“礼物在你卧室的衣柜里,你拿出来给她。”厨房里,他支着油乎乎的手叹了口气看我:“希望你体谅爸爸…”
我体谅你,可谁又能补偿我!我心里怒吼,嘴上却乖巧地应着。
薄云天准备的是一条品牌裙子,天蓝色毛呢料,我对着镜子在身上比了比,很漂亮。果断塞入衣柜深处,我将自己准备的礼物从背包里拿出来。
开饭了,他们果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宴。叶未央拿出一只精巧的纸盒,亲昵地攀着叶淙灵说:“姐,Happy birthday!”
她送她一条青色的丝巾,从爸爸赞许的眼神里我知道,丝巾和他选那套天蓝裙子很配,我望着他淡淡地笑,让你失望了爸爸,我不会让她的生活总是心想事成,这么完美。
我把桌边的一只粉色纸盒递给她,静静微笑:“叶阿姨,生日快乐。这是爸爸特意让我给你选的礼物。”
她明显意外,有些受宠若惊地看着我,顷刻绽开笑容,娇嗔地扭头对薄云天:“真是的,怎么能让孩子破费…”
爸爸有些怪我直言不讳,无可奈何地嘿嘿笑着,说:“快拆开看看,满意不?”
未央也催促着,只有我耐心地等待着。
叶淙灵面带笑容地拆开包装,却突然哇地一声惊叫。
手里的东西被她抛起然后嘭地掉在饭桌上,不偏不倚地落进了饭桌正中央的汤锅中。
然后,眼前出现的一幕诡异景象连我也有些悚然:一个一尺多长的咧着嘴笑的婴儿躺在冒着热气的汤锅中,黑濯濯的大眼珠直直望着众人。
恐惧而持续的尖叫声立刻充斥耳畔,叶淙灵脸色煞白,惊恐地睁着眼睛连连后退:“宝宝…活的…宝宝…云天,快救他,快…”
她疯了般揪住他的衣袖,又把脸紧紧贴在他的背后,不停叫着:“他是不是死了,死了…”
爸爸慌了,一把从汤锅里将“婴儿”捞出来扔在地上,转身抱住她,连连道:“没事了,没事了,那是假的,假的。”
叶淙灵被勾起伤心事,抱着他嚎啕大哭:“他死了,我没有宝宝了…”
我走过去,弯腰拾起地上的娃娃,找了条毛巾将它弄湿的衣服擦干,伸到她面前,说:“爸爸没骗你,这真的只是个布娃娃,你看他还会哭呢。”
我一捏布娃娃的胳膊,这个光头胖脸穿着红肚兜的小娃娃立刻发出“哇哇”的哭声,却是十分逼真。薄云天怒对着我,一把夺过娃娃扔到门外:“砂砂,你在搞什么鬼!”
我冷冷道:“不是您让我给她准备生日礼物的么?礼物不合心意就迁怒于我么?”
“你--”他瞪着我,脸涨成青红色。我转身拿起沙发上的背包,冷笑对薄云天道:“我是你亲生女儿,但现在我是外人,是这家里多余的一个。我走,你们满意了吧。”
我摔门而走,外面阳光正暖,可我回想起刚才那幕,身上也是一阵发寒。
“薄砂,你站住。”身后有人追出来喊,我回头,看到叶未央。
她的脸色也凝郁着,走上来对我说:“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我僵着脸,闷声道:“这是我们家的事。”
她有些不悦:“可她是我姐,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上跟她和平相处吗?你不能把过去的不幸全部归责在她身上。人生很多事情,或许都是命该如此…”
“我命该活得卑贱痛苦是吗?”我冷冷望着她的眼睛:“像你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理解我的感受。”
她默然,阳光下涂了眼影的脸跳跃着光彩,过了一会儿她伸出左手抚向我的肩头:“可是薄砂,人总要向前走…”阳光射下来,她手上的光芒突然刺到了我的眼睛。一枚亮晶晶的戒指套在她的左手无名指上,我仔细看了下,没有钻石,只是一枚样式略显古朴,看起来像银质的玫瑰花蕾形状的戒指。
少年时的一幕恍然又回到眼前,下着雪的冬天,三个少年的小酒馆。清秀的少年将一枚亮晶晶的玫瑰花银戒郑重地从苍蓝色盒中取出,想送给美丽的女孩,却遭到拒绝…
时光会改变一切,曾经坚决表示不肯接受的女孩,却戴着男孩饱含多年深情的银戒指。叶未央,你是何其幸运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