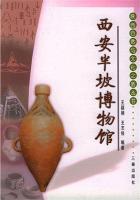张先生的学术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在中国近代考古发展史上,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的考古研究领域,在中国“三代”的文明起源发展与世界文明起源的学术问题上都有不俗的见解。自改革开放以后,他更是把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中国考古领域中,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多学科整合”的新局面。随着张先生的系列著作中文译本陆续出版,他的许多论述和观点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这对年轻一代考古学者来说影响尤大。而此时张先生在国内考古学界的声望和地位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国内学者陈淳这样评价张先生:“中国考古学的起步是本世纪(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建国后的四五十年中,中国考古学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展,使得大部分的研究还停留在国外50年代以前的水平。因此,中国考古学迫切需要第二次西学东渐,以赶上国际水准。而张先生完全堪称这第二次西学东渐开山祖师。[10]”可以说,张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一笔相当丰厚的遗产。这笔遗产不仅仅是张先生的著作,还包括了他为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思考和想法。下面试图从六个方面来谈谈张先生为我们留下的遗产。
(一)推动中国考古学界与国外考古学界的交流
张先生每次来华访问都向国内考古学界的领导进言,提出和美国考古学界合作以及选送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深造的建议,但是由于在建国后考古学成为维护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一个象征,再加上张先生那令人怀疑他别有用心的“特殊”身份(生在北京,长在台湾,在美国成名,但是研究的却是中国大陆的考古),所以导致建议每每遭到拒绝。他的良苦用心在与童恩正先生商定的中美合作计划胎死腹中之后,受到极大的挫伤。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考古学与外界交流的努力在当时也几乎变成了一种“美意而徒劳的尝试”。所以他写《哭童恩正先生》,其实也是自己内心的流泪,哭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错失了一次良机。这大概就是朱启新先生所指的“张光直先生哭童,不仅仅是哀悼其人,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之所在。张先生在文章里再三强调:“我和童先生都深深地体会过中国这个弱小的民族在西方侵略之下所受的痛苦。我们所写的合作计划不可能是以西方的利益为先驱的”;“这工作如果可以完成,可能是很伟大的。”遗憾与痛惜之情,溢于言表。童恩正在生前也对他和张光直先生合作计划的夭折感慨万分,表达了和张先生同样的惋惜:“中国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包括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和秦俑坑在内,都是群众无意中发现的,并非学者的科学预见。所以在考虑考古学的成绩时,应该把资料本身和发掘水平、研究水平区别开来。前者是祖先的创造,后者才是学术水平的真实反映。感谢中华民族先人的创造,中国得天独厚,有着如此精美而丰富的地下宝藏。如果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思想上不受禁锢,在中国现有的条件能够得到更好的技术装备,在某些暂时不具备条件的领域内与国外学术界进行真诚的合作,那么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许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
不管怎样,张光直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架桥人,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为中西考古学的接轨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古代文明原生地之一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有其重要的地位。张光直的理论就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定了位,他认为:中国考古学“提供足够的资料,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文明如何在中国开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中国、玛雅和苏美尔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这个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二)强调重视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80年代中叶,随着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张先生趁美国考古学家布鲁斯?坎格尔的《时间与传统》(中译本)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际,在序言当中对中国考古学轻视理论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重视,“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由于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有系统的探讨,所以在这种历史观里发展起来的考古学也就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张先生指出,虽然中国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其实它的工作包括三项不同的境界,它们是技术、方法和理论。在研究过程中,“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在考古实践中,我们应当先知其然才能决定其所以然,使得我们能知所以然的便是考古学理论。理论帮助我们在考古作业的每个步骤上知道我们的选择,提出有关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的系统看法和想法。他还强调,考古学资料是物,如何从物去研究人的生活,这便要借助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考古人类学打破了以往古物学和金石学几乎完全关注“器物”的限制,转而关注“人类社会的过去”,通过对某一特定时空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或者与人类社会相关的遗迹(sites)、遗物(remains)、遗址现象进行研究来理解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
(三)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
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探索是张先生的研究强项之一。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从概念上来看,文明是指一种广泛而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而国家是根据政治与地域界定的等级社会,但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常常是文明的载体。
张光直在研究中发现,国家的起源,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其特征是在兴起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代发生断裂。西方式的国家起源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生产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二是东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东亚的中国,也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它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确立开创新的时代。其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东方式的国家起源中,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包容了新的地缘关系。因此,东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连续性的。
在阐述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后,张光直提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式的国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态。因此,现代社会科学里自西方经验总结而来的国家起源理论的一般法则没有普适性。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仅仅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事实得出的,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尤其是东方文明中的国家起源进程。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张光直进而提出:“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
张光直的上述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001年9月,美国罗莎?兰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编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Breakout-TheOriginsofCivilization)一书,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张光直提出的国家起源的断裂——连续理论。可见,张光直的学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光直的理论不仅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独尊”的局面,而且还为中国文明争取到了初步的“话语权”。因此,现在是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来展示世界文明起源的一般法则的时候了。所以,张先生提倡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共同来研究中国极为丰富的考古资料。他非常赞同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的,要打破“国学”研究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到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他为中国学者提出了3点建设性意见:一是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史料,二是要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要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3个条件,我们才能看出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史,哪些理论需借中国的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的史实中可以得出哪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法则。这里的史实应当包括了考古学的最新成果。他预言,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当是中国的世纪。
(四)聚落考古学的推广
张先生向国内同行介绍较多的是“聚落考古学”。他指出,聚落考古是把我们的目标从对“器物”的研究转变为对“人”研究的重要方法,聚落分析可以把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结合当时的生活环境、生活状况、生活制度来进行复原和推断,从而进一步了解社会演化的一般法则。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将考古遗存及其空间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和文化活动研究方式的具体操作的一个框架。聚落考古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之后已成为西方田野考古方法的主流,但是在国内,挑选个别大遗址和重要遗址仍然是传统的做法。张先生60年代在美国就编撰过有关聚落考古学的论文集,对西方聚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完善做出过杰出贡献。他在国内大力推广这种方法,其目的是想推动中国的考古学从器物描述和分类转向对人与社会的研究。
(五)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借用
由于人类学与考古学之间有相依相倚、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考古学需要人类学的指导。考古人类学的研究不再是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法,而是通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来获得对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的认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性的,它包括人类社会的不同类型,其文化内涵比传统考古学大的多。也正缘于此,张光直教授大力提倡人类学分析方法,而且还频频告诫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要熟读文化人类学。他指出,中国传统的考古研究受金石学影响极大,即从器物本身来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样的结果便是“见物而不见人”,研究缺乏深度。实际上,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器物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研究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具备所有种类的蓝图这些习俗与制度,在考古遗址里面,只有一点物质痕迹残留。不熟知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很自然地将这些遗物只当作物质文化处理。熟知各种习俗制度蓝图的考古工作者,便有可能根据残存的部分将全部习俗或制度复原。人类学的蓝图帮助我们提出许多问题的新解释,如仰韶文化中的巫师,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沟通天地作用,商王庙号与王位继承制的关系等等。他还提出,用人类学的蓝图与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之间,史料为先。不能拿史料去凑合蓝图,要用蓝图去对拼史料。读人类学的书,也要和别的书一样,必须融会贯通,切忌半瓶醋的读法。
(六)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关系的思考
早在1980年,张先生应夏鼐先生之邀在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做了一个学术报告,对刚刚开放不久的考古学界同仁谈了他的看法。在高度评价中国考古学的优越性后,他指出,中国的考古学应当借鉴西方考古学,将考古学和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并进行社会演变规律的探索。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