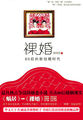《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乡土中国》是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之作,代表了费孝通先生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费孝通先生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具有开创性。
(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国民族学
1951年费孝通开始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曾随中央访问团访问调查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50年代中期到贵州、云南进行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此间,著有《我这一年》、《大学的改造》、《兄弟民族在贵州》、《话说呼伦贝尔》,后又著有《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1988年,费孝通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在泰纳演讲会上发表了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点》为题的主题演讲,提出了他关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他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六大特点:(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核心先是华夏族团,后是汉族。汉族人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但也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牧业,在统一体内形成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类型。(3)除回族、畲族外,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语已成为通用语言。(4)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但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汉族的农业经济是汉族凝聚力的来源。(5)中华民族成员众多,人口规模大小悬殊,是个多元的结构。(6)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此论一出,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民族研究的核心理论,是解开中华民族构成奥秘的钥匙,进而推动了民族研究的发展。
三、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影响巨大
1988年11月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上作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在该演说中,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地表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矛盾运动,它们相辅相成地始终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纵观历史,中国自秦汉为开端,几经分裂、统一,终于在清朝确立稳定、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进程中,民族间总是在一体中做多元运动,统一局面也不断扩大,其关键在于形成了华夏民族这个凝聚核心,它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摇篮,“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民族,越滚越结实就在于其非凡的凝聚力”。农业文明是其经济基础,南北农牧互补,相互依存与斗争。大一统总是以局部统一为前提,我国的疆域、历史、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既是各民族的多元发展,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体发展。各民族历来命运与共、兴衰相连。中原统一则边疆安宁,中原分裂则边疆纷争。任何在政治上占优势的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开放、团结政策就共同发展,采取封闭、歧视、排斥政策就两败俱伤,最终衰亡。汉、唐采取优待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和亲、互市、“因俗而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因而汉、唐是最兴盛的朝代。王莽新政实行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是其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建国后,新型的民族关系应运而生。汉族和少数民族插花分布、交错杂居、互补共生,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不与“多元一体”特征密切相关。
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特有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其必将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带来深远影响。强调民族的多元性能使少数民族得到更好的发展,首先,在承认“中华民族一体”的前提下,我们必然要重视各民族之间确实存在的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现实,虽然我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对各民族平等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有许多问题并不是单单的法律平等所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予那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于制度、政策上的优惠,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变劣势为优势。其次,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我们只有承认了民族的多元性,才能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等,才能相互尊重,友好相处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才能使各民族更加体会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对处理民族问题不仅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他指出民族发展有量变和质变,各民族客观存在,整体认同也客观存在。用“多元”与“一体”概括,是名与实的辩证关系。民族间的同和异还会长期存在,“同”不是完全一样,“异”也不是大家分开。今后既有各民族繁荣,又有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事实上,尊重“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也反映出我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即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反对民族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民族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等。我们应大力支持少数民族人民,帮助其开发丰富的物产资源,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从“异文化”到“本土化”:研究道路的光辉楷模
就传统的人类学学科而言,对“异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基本的学科要求和学术立场,这基本上成为一种常识。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研究之路也无例外地始于对“异文化”的研究,具体地说,是对广西大瑶山(金秀县)花蓝瑶的田野调查。
这一段“异文化”的研究经历悲壮且感人至深,也为费孝通先生在其后的岁月里探索中国社会人类学“本土化”的研究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人生经验和学术上的参照坐标,它不独表明了中国人类学家在“异文化”研究道路上跋涉的艰辛,也表明对“异文化”研究经验的积累在他以后的“本土化”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异文化”这一概念自人类学诞生之初,便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话语痕迹和殖民主义扩张的某种“霸权”色彩。从单纯的学术角度,“异文化”也是从民族志学者个人的族属身份以及由此产生出在田野调查中的“主位/客位”视野而言的。然而,费先生对“异文化”的认识不限于此并有创新,所言说的“异文化/本土化”一方面是从传统的人类学知识体系中去定位,即人类学家从学理上应该遵循到本民族以外的其他“异民族”,去生活、体验、参与观察;对费先生而言,瑶族便是他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所需习得的“异文化”;而他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和经历都在进行他自己所属民族,即汉民族的研究工作。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从“异文化”到“本土化”的研究轨迹。另一方面,瑶族在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又成了“本土化”研究范畴的有机部分和确认边界。这便是费先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国家领导者的一种超越单一性学科的眼光和视野。这正是他“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
费先生的从“异文化”到“本土化”的学术道路不啻为中国人类学研究、人类学者的探索之道的样板,道之道,平常道;道之道,非常道。费先生的人类学研究之道为我们指引了一条中国学者的学习和学问之道,更是年轻一辈的人类学者沿着这一条研究之道去追索中国的人类学特色,去探求人类的普世性真谛。
(三)推动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中国化”
民族学与社会学都是20世纪以后自西方传来的,为了将这些西方产生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和民族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将这几个学科“中国化”的任务。他说:“必须建立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使这些传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但是,如何实现中国化,学者们往往有不同的主张。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和探索中,费孝通先生像一位旗手,一直走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他毕生致力于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费孝通不是单纯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解释,不是注重于西洋理论的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的罗列中国的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的范围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从可以证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的解释,使对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
费孝通先生用行动告诉我们,从事学术研究,要不拘一格,不闭门造车,要重实地调查。他的研究,从来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他认为,从事研究的最高目的,是为国家、为社会、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服务,在这些研究中,无论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民族学,都只是一种工具。他说:“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和实际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解而了解,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了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也就是说,费孝通认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不是学科的理论、学科的发展,而是应用,是认识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会。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正是出于这样的目标,他一直有宽广的胸襟,反对搞小圈子。他说:“要开创一个新的学风,实事求是、互相学习的学风,不搞门户之见,这三个学科是一个集团,三科并立,可以各有重点,又互相交叉。”在国际学术界,费孝通先生被公认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的数十部专著,已成为这几个学科永恒的财富。
(四)一生“志在富民”
“我一生有一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这是费孝通学术价值观的核心和学术研究的动力。他把个人的命运熔铸于社会,在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半个多世纪里,“行行重行行”,在祖国大地的东部、西部和中部29个省市自治区的270多个市县的许多乡村、农民和牧民家庭、厂矿企业都留下了他考察社会、关注民生的行行脚印。他沿着村庄——城镇——区域发展轨迹不断深入地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概括总结了农民实践进程中的经验,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发展“模式”。费老的志在富民研究是从他的家乡“江村”开始的。“江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如何在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农民还有富余的资金。也就是说,如何在农村找到一条小康之路。他从早年立志认识和改造社会,可以说,一生的心思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农民。推动他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
解放后,费孝通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严酷批判。他的学术研究专业生命因此停滞了宝贵的20年。但费孝通说:“意外的政治运动打断了我这种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反右’斗争中,我被划成‘右派’,失去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从那时起直到文革结束。我这篇富民的文章做不下去了。”但他富民的心不变。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的富民政策开始实施的时候,也正是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时候;他埋在心头的“富民”火种又燃烧起来了。他一生中所作的农民和少数民族怎样从贫困到脱贫,从脱贫到富裕,从富裕到小康的文章已成长卷,并已产生了显著的效益。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理解、体会是独到而深刻的。费孝通对乡土中的农夫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其实是一个士大夫的情感。费孝通觉得,只有改变乡土中国的现状,才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提出“工业下乡”。1949~1978年,三十年间,中国走上了一条奇特的工业化路径,在城乡之间修筑了坚实的藩篱——户籍制度。中国选择工业化的路径,却排斥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最后经济都走到崩溃的边缘。1978年以后,邓小平立志改变中国贫困的状况。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贫苦的凤阳农民吹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号角,邓小平将它推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农民获得了实惠,乡村经济活跃起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策的倾斜,城市迅速发挥出活力,城市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农村经济改革而有所缩小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落差,又迅速拉大了。农民出路何在,农业出路何在,农村出路何在?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出现在农村改革十多年之后,邓小平邀费孝通出面参加政治活动。费孝通先生成为人大副委员长后,立即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的视察,完成“乡土中国”和“多元一体”的田野调查工作。我们可以说,近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能够像费孝通一样如此关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田野工作,除了西藏和台湾,费先生踏遍青山,也没有一位政治家如此勤奋地视察了祖国的山山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