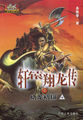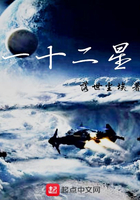小羽突然生病在家休息,放学后,我和恺然一起去看她,因为临时召开班干部会,所以错过班车的我们不得不抄近路去小羽家。途经一条幽僻的小巷时,突然蹿出几个小混混,真是冤家路窄,那些人正好是恺然的死对头,曾因为恺然揭发他们考试作弊而被学校开除,早就对恺然恨之入骨,离校时还扬言要放恺然的血。”不好!”恺然说这话时,迅速地拉起我往回跑,无奈那帮混混早有准备。”陈恺然,我看你往跑?”为首的家伙抽出一把匕首向恺然的背部刺去。”恺然,小心!”我尖叫着,想也没想便挡了过去,那把匕首就这样刺进了我的身体。一瞬间只有一种钻心的痛,我捂着伤口,殷红的血从手指缝间不断往下流。那些混混没料到会砍错人,拿着带血的匕首溜了。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往下坠,恺然冲过来抱住我说“子柔,你怎么样?”我很吃力地摇摇头,嘴微微动了几下,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我喜欢他,因为我担心自己会死去,我不想让恺然感到愧疚。
我的眼泪疯狂得像断线的珠子,不久便因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醒来时,恺然守在我身边,眼圈黑黑的。见我醒来后,他特别的高兴,并告诉我伤口已经缝了针,让我好好休息,父母没有来,我想离了婚的他们只想通过钱来扔掉我这个包袱,又怎么会来看我呢?恺然的父母倒买了很多东西来看我,并且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让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同病房还有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但我们从未说过话。
恺然每天都会来看我,那天,他急着从医院赶去学校,将外语书忘在了桌上。我随手翻开,从里面掉出一封信。”小羽,我们分手吧,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真的好累,从开始到现在,我喜欢的人都是子柔,跟她在一起,可以直来直去,很轻松,而且她现在还为我受了伤,我更应该陪着她。千万别再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了,我真的不值得你这样做,你是个好女孩,一定会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我什么都明白了,眼泪不争气地又流了下来。
也许是当天着了凉的缘故,第二天我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说“可怜的孩子,这么小竟然染上了艾滋病。”我以为是自己在做梦,便又昏昏沉沉地睡去,醒来时,高烧仍然未退,但却被护士送到了主治医生的办公室。那位医生一直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告诉我:“经医院检查,你可能通过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后面的话我没有听见,只感觉自己的心猛地一沉,艾滋病!通过输血感染?以前在电视中看到的故事竟会在我身上重演!虽然医生一再地说还要复查,但我想到艾滋病的前兆是发烧,顿时确信无疑,毛骨悚然。
回到病房时,恺然已经来了,他握着我因发烧而滚烫的手说“子柔,你怎么起床了呢?你的手好烫啊。”我像个傻瓜呆呆地站在那里,脑中不断地重复医生的话“通过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子柔,你说话呀,是不是被烧坏了呀?”我只是看了他一眼,仍然一动不动地呆站在原地。”你到底怎么啦?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恺然,恺然啊。”恺然突然紧紧抓住我的双臂大声说着,眼里满是心疼,我这才回过神来,恨不得马上扑到他怀里,可是想想我的病,想想我和他不可能再在一起了,我又变得忧郁,我该怎么办啊?我现在有病,而且我的病是会传染的,我不能拖累恺然的。我猛地甩开他的手,冷冷地说“别碰我。”接着拼命地往后退。”子柔。”恺然又向我靠近,惊慌之中,我撞到了墙上,牵动了伤口,痛得我蹲在了地上,恺然马上过来扶我,“你走开啊,我不想看见你,更不需要你的可怜。”我朝他大声吼道,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声音惊动了护士,“病人需要休息,你还是改日再来吧!”恺然极不情愿地走出了病房,在他回头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水。
犹豫之中,我还是给妈妈打了电话。刚刚再度离婚的她迅速赶来了,并决定把我带到武汉去治疗,我没说好也没反对,只是不停地掉眼泪,妈妈迅速帮我办了出院手续和休学,走的时候,并没有通知恺然,我就这样与他不辞而别了,坐上飞机的那一刻,我双眼红肿,想哭却已没了眼泪,我在心里轻轻地说:“别了,恺然。”
辗转武汉的几个医院,医生的检查都是我根本就没有患艾滋。妈妈打电话到以前的医院,院长一直赔不是,原来医院弄错了,患病的是同病房另一个叫辛子柔的女孩。那一刻,我啼笑皆非,我决定再回去,可妈妈却说以前对不起我,现在只想好好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听着妈妈的忏悔,我的心又软了,只好留在她身边。我给恺然打电话,想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恺然的妈妈却告诉我一个震惊天地的消息:“恺然这几天心情很差,精神恍惚,过马路时出了车祸……”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拿电话的手不停地颤抖。
我和恺然就这样错过了,失去他也许是命中早已注定的。尽管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但恺然将一直停留在我心中,永远,永远。
午夜清寒。母亲单薄的身躯依旧苦苦地等待着,等待着异乡儿子的声音,哪怕是只言片语,都足以让她满足。
毕菪茎
母爱,是一笔债
从教室出来,已是深夜十一点。
校园中飘荡着一丝丝由绛红色褪去的余辉,使整个夜空黑得不太纯粹,我被一种若即若离的心情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或者说是绊了跤。
今天是母亲的生日,而我却只记得今天是家长探视日。为什么就记不得是母亲的生日疃?!
我的心里一下子潮湿得透不过气来。
有一种力量要将我静止在原地,让我的思绪全都空格。虽然我是情愿的,但我始终没有停下,因为淹没于放学的同学中的我身不由己,双脚只得带着身体机械地跟着人群走。
寝室里母亲洗的衣服总是显得格外干净,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粒悄然汇集,从衣物上滑落,“倏“地坠地,沉闷而干脆。我的心也禁不住一阵颤动,流水般的记忆开始在心湖泛起涟漪。
我不记得“牛日“这名词是在什么时候刻进我的脑里,只依稀记得那时候每年总有一天会有很多的小伙伴去我家,然后一起在外边疯玩,.母亲叫也不回,直到被母亲揪了耳朵回家。桌子上是让人一下子忘乎所以的香喷喷的蛋糕。我的眼睛发光,嘴里溢出了口水。母亲笑着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吃蛋糕的日子!”“什么日子吃蛋糕?”“我的生日。”说后便忍不住扑上去。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蛋糕是为我的生日而做。而后即便是不在家的日子,母亲也没有忘记在生日那天给我祝福。多少年过去了,童年的欢乐如同黑暗中挥霍光焰的月魂,于宽泛无垠的天空中漫过记忆的树木、沙滩、池塘。我成长的幸福与辛酸至今仍保留在母亲深深的皱纹与回望中。
可是今天我却忘了母亲的生日!
我临窗而坐。没有任何月光泻进来,眼前只有那条被蜡黄色的路灯苦苦撑起的校道孤独地伸向远方。
在路的另一端,在夜晚的深处,在一盏灯的清辉里,母亲或许正坐在镜前梳理头发,屋里没有吵闹,只剩偶尔扯下一根银丝时绵长的叹息或者是正在担心异乡求学的儿子是否能够适应骤变的天气;抑或伫立阳台,静静的与影子独处,检视生命走过的痕迹。
此刻的母亲大概最为孤独吧?
她的身边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器物,却回荡不出往日嬉笑欢乐的情形;身边有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却游离着业已不能再令她感动的感动。
午夜清寒。母亲单薄的身躯依旧苦苦地等待着,等待着异乡儿子的声音,哪怕是只言片语,都足以让她满足。而这些却是我应该做的啊!
“丁冬!”又一滴水珠滴在眼眶中,溅起柔和的白光,落到眼球的底部,而心似乎被拉成了细长细长的丝。就这样在孤寂的黑暗之中,整理着自己今夜复杂的心情。忽然想到,既然还没有错过,为什么不去好好地珍惜?
有风吹来,顺着心事的方向。
我站起身,走出寝室。夜已经很深了,我快步走到电话亭,迅速拨下熟悉的号码。
“嘟……嘟……”绵长!
我明白了母爱原来是一笔债,一笔要用一生来偿还的长长的债。
婷的眼波深处有一片善良的温柔,可在她那温柔深处隐藏着的哀伤又怎能瞒得过我呢?婷,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于智超
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我真不知该怎么对婷开口,只不过上了一年大学,我那颗曾经许诺说永远属于她的心就变了,我也变成了一具对我们的爱情无动于衷的木乃伊。
记不起是哪个教育家说的:“高中的恋爱绝对不可能发展成婚姻,它只能打造一段人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我也曾经倔强地把这句话打翻在地,认为这是他因为嫉妒别人而说出的胡言乱语,认为自己的恋爱不会是他说的那种青春期里心灵的萌动,认为我的爱情永不褪色。
于是我信誓旦旦地接受了一份来之过早的爱情。那是在高二时,我和婷——一个淡雅的女孩之间的爱情,之后我给自己稚嫩的肩膀新加了一个用途,就是让她依靠,给她温暖。一种成熟的感觉侵入了我的心,我有些沾沾自喜了,因为我恋爱了,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是这就是成熟吗?难道只是在爱隋的溶液里浸泡一下就算是长大了吗?天上的那弯新月不就是我的爱吗?为什么那么苍白,那么空洞?
毋庸置疑,人的感情是流动的。升上大学,来自四面八方几千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聚集到一起,在一所花园似的空间里生活,有许多新鲜的东西会闯进来,让人目不暇接。由于我对大学生活的不适应,不久就“患“上了大学生的通病——孤独。
这时总会有一种东西乘虚而入,那就是感情。就是在这时我认识了芳,我们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给婷的信里提到芳的次数也逐渐增多。
婷好几次在电话里和我开玩笑警告我:“要小心点儿,心别让人给偷了去。”我一笑置之。
可是还是应了泰戈尔的那句“理解是爱的别称“的名言,随着我和芳之间了解得不断加深,我感觉到我已经寻到了我以前曾经找了无数次而现在终于找到却又不敢承认的东西——爱情。
街角的霓虹灯快速地闪跳着,那角裙裾是她的,是婷来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那长长的花裙曾给我的心里留下无尽的牵挂,可是现在它却像一条长锥扎进我愧疚的心里,刺出一摊鲜红的血。
她走近了,盛开的笑靥仍把我当作她的唯一,我心里又是一阵抽搐,我简直撑不下去了,我真怀疑,这还是以前那个自称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的我吗?
“走吧,志。”她的声音仍是那样的轻柔。
“哦。”我勉强移动了双脚,挪着沉重的步子。一块砖头绊了我一下,我立刻颠踬得就像一头瘸腿的驴子。
“没事吧,志?”她关切地问我,“没崴着脚吧?我看看。”
“不,不用,没事的。”我就像一个演技拙劣的三流演员尴尬地摆摆手,继续着这漫长的散步。
又到了那片草地,我忘记了和她来过多少次,但是我记得每一次的到来都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清风朗月,树影婆娑,我们并排躺在木椅上,惬意地浴沐在柔和的月光里,没有升学的烦恼,没有分离道别的忧伤,只是静静地听着河水与小草的合唱,任心弦被微风拨弄得发痒。那时她总是轻轻地用手指拢着我的头发,在高三的日子里,那也是抚慰我憔悴的心的最有用的方法!可是谁又能想到这片乐土今天竟然变成了勾起回忆的伤心地。
“坐坐吧。”她轻轻地把裙幅拉紧,躬身坐在椅子上,我也坐下来,冰冷的木椅咯吱咯吱痛苦地呻吟起来,一如那冰冷伸进我心里搅起的痛苦呼喊。我坐不住了。”还是躺下吧。”我说着就躺了下来,她躺的动作还是那么轻,就像一只小猫在打哈欠。
静静地躺着,月亮仿佛随着我的心在不安地动,里面的桂花应该已经掉得所剩无几了。
“婷,你好吗?”我不敢看她,眼望着深蓝的天空。”不怎么样,大学里的生活倒是丰富多彩,可没有你在身边,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怎么会呢?你这么漂亮,在那边找个男朋友好了。”我充满侥幸的声音变得有些发颤。
“好啊!”又是以往那种调皮的语调,以前这样说的时候我总是胳她的痒,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婷,我是说真的,“我撑起身,看着她,“我们分手吧。”
婷的脸一阵错愕,很不自然地笑着说:“志,你——你是和我开玩笑吧?”询问的眼睛里已经笼起了一层水雾。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从嘴里勉强挤出两个字:“不是。”
婷痴痴地看着我,泪水像坠落的流星从她的眼里飞挂下来,她的小脸在银色的月光下显得越发苍白,嘴唇抖动着似乎想找出一句要说的话,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她颓然地低下了头。我低头看着她身旁的草地,那里开着一朵惨白的小花,被风吹得只剩下了几瓣。
这无声的几分钟像借用了我几十年的生命,我的身体就像一具无知的空壳硬硬地撑在那儿,我不敢再去看婷的那份凄婉,我不忍心。我真浑,我怎么能去伤害一个这么爱我的女孩呢,可我也是为了你呀,婷,如果我现在不这样做,那以后给你带来的伤害会更深,你会恨我一辈子的。”唉,“过了许久,婷幽幽地说,“志,你转过头来。”我的目光转向婷躺的地方,然而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挪了几步坐起来了,两滴透亮的泪珠还在那儿悬着。”志,其实我们的爱情是不牢固的,我早就料到了,只是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快,也许我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像以前我们想的那样,它不代表爱情。每个人走的路不同,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你的路,那么即使你不再属于我,我也不会怪你,我们还是朋友,是吗?”婷纤细的手指梳拢着我的头发,动作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么地轻柔。
“婷,我……”我的嗓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再说一个字也变得那么艰难。
“别说了,和你相爱我不后悔,以前不会,现在和以后也不会。我也相信你以前对我的爱是真诚的,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嘛,对吧?”婷的眼波深处有一片善良的温柔,可在她那温柔深处隐藏着的哀伤又怎能瞒得过我呢?婷,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给一个伤害你这么深的男人蒙上一块尊严的遮羞布呢?是我负了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