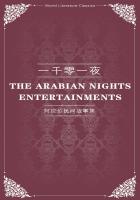在人类学研究中,被研究者主观上对人的看法,即他们的人观是我们理解其行为与思想的重要依据。人的观念还包括对于空间与时间的分类及社会文化构建。因此,对人观、空间和时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文化的深入理解。
一、人观的内涵
1.有关人观研究的回顾
人观即人的观念,试图以“人观”作为理解研究对象文化内涵的一项概念工具,是人类学较晚近的尝试。在人类学早期,以“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与它最有关系,但这一学派的研究,由于一直深受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及实证论的限制,忽略了被研究者主观上对人的看法。后来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发表了他的论文集《社会学与心理学》一书,在这本书中,莫斯本来的目的是指出对社会现象的了解,必须兼顾生物的、社会的环境,以及心灵的活动三个层面。当他试图用人的分类为题来呈现他的观点时,他提出persona及individual两个相对的概念:persona是社会所给予的人的观念,individual指生物上的个体。在近代西方社会,这两者是合而为一的,但在其他社会却不尽然。
不过莫斯所关怀的主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因功能论在人类学上的支配地位而没有引起人类学家的注意。直到1970年,人类学家杜蒙(Dumont)在对印度种姓制度的研究中,提出了证明阶层的基本原则——纯净与非纯净是了解印度种姓制度的关键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印度人的观念,是来于他们的种姓制度。在此制度下,所有人是天生不平等的。也就是说,个人因其阶级上的不同,而有不同且不平等的人性特质。这里杜蒙不只强调印度人的观念是存在于其社会整体中,更强调了终极价值或世界观对了解这类观念的重要性。由此杜蒙开导了人类学家透过被研究者的世界观或宗教信仰来了解被研究者对人的主观看法的新视野。这后来形成了一种研究趋势:由信仰体系或宇宙观着手,以了解被研究者对人的看法即人观的研究。为呼应这种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文化组于1991年2月主办了“人的观念”研讨会,与会学者藉由各自的民族志材料做大范围的“人的观念”的泛文化比较研究,提示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不过,在这一新的研究趋势中,讨论主题与方式虽异,但主要仍环绕在人主观上认识到的“个体”、“自我”及“社会人”是什么上。
2.人观的内涵
(1)个体
首先要指出作为生物体的“个体”而为人类的单一成员,存不同文化的主观认识上,并不一定有现代解剖学对人体的看法,也不一定有近代两方所强调的独立与自主性。这自然与对每一“个体”的成分为何及“个体”之各成分或整体之界限的认定有关。比如,有许多民族认为每个“个体”都有它的精灵(也许不只一个)。这些精灵存于躯体内,也可随时离开身体,而有其流动性。像毛利人的酋长之mana,可以跑到各种物体上,也可跑到平民身上而造成伤害,也可以因神的不支持而离开酋长而使他打败仗。[1]更值得注意的是毛利人认为个体的不同器官分别控制个人的各种不同经验。比如ngdkau(肠内的器官)保持人的心智之清醒、敏锐;manawa(在心、肺、胃内之器官)则控制一个人的耐心、勇气等。一个“个体”的运作或行动,并不是由一“主体”来控制,一个“个体”的行为也没有必要是一致的。因此,“个体”其实并不是整合的。比较之下,中国人在概念上一直保留一个“个体”的完整。不过,中国人对人体的认识不但复杂,而且似乎一直在演变。在春秋之前,中国人对人体认知只限丁表面,但已肯定“心”的重要——掌管人的意志、情绪以及精神等抽象的活动。即使到战旧时期已肯定五脏是各有不同功能的感官,但仍以心为主宰。不过,原已有的有关魂、魄、精神、神鬼等概念也日渐发展,到战国的道家更发展成一套以气为主的生命论。因而与儒家的“以心使气”之说产生争辩,而造成形体与精神的二元生命论,但在儒家不得不吸收道家之说以后,则又二元合一而有唯物色彩。
(2)自我与社会人
这里所说的“自我”,是指作为经验存在的人,包括那人对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经验。一方面,“自我”是主体,是“个体”所有的行为中为其所知的创造者。另一方面,“自我”是客体,它是藉由正常一般人能知觉到自己在知觉的能力,而得以把一个人的其他不同层面集合在一起。这种知觉活动造成人的自我意识。
至于“社会人”是指一个人被公认为从事某一特定目的的行为之创造者,在一社会秩序中有一定位置,而被视为是社会中的行为者。因此,它与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可分,也与社会规范以及道德不可分。也因为每个“个体”对社会规范与道德遵循的程度不同,而使个人有部分或全部成为“社会人”的现象。一个已成“社会人”的人,也有可能后来丧失部分或全部“社会人”的情形。换言之,“社会人”与社会情境或脉络息息相关。而一个“社会人”,更因其生命的成长过程所纳入的社会情境与角色不同而不断改变。在较复杂的社会中,地位较低的次级社会虽纳入于较大的社会中,却有它自己所特有的社会秩序,其间相关的社会情境之孤立程度则与不同“社会人”观念的形成与使用方便与否相关。
(3)有关人观的个案
以台湾布农人为例,布农人认为一个人至少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外在的身体部分(个体层面),称之为logbo,得之于母亲。第二部分是精灵,称之为hanido,得之于父亲。hanido有两个,一个在左肩,可影响一个人去从事粗暴、贪婪、生气等伤害他人而追求私利的行为;另一在右肩,可影响一个人去从事慷慨、利他的活动。而真正决定一个人活动的是人一生下来便有的is-ang(自我),这也是人的第三部分。is-ang(自我)在人初生之时力量很微弱,实际上还不太能做什么决定。这时一个人的成长,主要是在身体部分。由于身体来自母亲,因此,布农人小时便必须依赖母方亲属之精灵的福佑才能顺利成长。直到举行Magalavan(小孩成长礼)仪式之后,is-ang(自我)才真正主宰“个体”的发展。但在青年乃至壮年时,is-ang(自我)则常困扰于左肩与右肩hanido之间的冲突。直到老年才比较能维持两者或者是个人与群体间的竞争与矛盾的平衡。到了死亡及葬礼后,is-ang(自我)转换成hanido之后才离开身体而真正解脱于两肩精灵间的对立。但只有对群体有大贡献的人,死后的is-ang(自我)才能达到永存之地——maiason。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代表自我的is-ang,不能与个人的社会角色或责任脱离。事实上,个人的“自我”在完全解脱之前,必须先达到个人与群体角色的平衡,也使“自我”与“社会人”趋于合而为一。这种强调“自我”与“社会人”的平衡,更与他们社会整合的机制有关。上述有关布农人的人观,可参阅图ll。
3.人观研究的意义
透过有关西方人观的探讨,我们不但可了解西方现代人观是从12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而成的(它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质)。并且,人的观念的探讨也会影响甚至帮助我们了解该社会的性质。其实,何止社会的性质。比如拉弗登(J.S.LaFontaine)便讨论过政治权威与人观之间的关系:职位愈高,愈强调“人”的自主性,个人的生命仪礼愈被社会所忽略;反之,人观愈缺乏个人的独立自主性,生命仪礼愈趋以集体方式行之。[2]人类学家南迪(A.Nandy)的研究,更替殖民主义的统治提出新解释:殖民地的统治不能只是依赖功利主义的权力观念来理解,殖民地社会秩序更是透过有关人的象征秩序的重建来合法化殖民者的统治地位。[3]还可以通过对人观的研究取代以往以“神”来理解宗教的特性,以及人观而不是亲属观念来理解新的不同族群亲属制度的差异。[4]
二、空间和社会
1.空间的内涵
如果我们要探究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那么就不能从数学家的抽象、同质的空间出发,而是必须观察人所能感受到的具体空间,人类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空间。这种空间并不是如那种人为虚构的空间一样统一而无组织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的。
人类学家认为,空间是以自然的地理形式或人为的建构环境为其基本要素及中介物,但那不是最终的,而是在其上依人的各种活动而有不断的建构的结果。
空间更可被视为宇宙观或一种象征。这在有关汉人的八方或风水的讨论上特别明显。因为只有在了解天、地、人合而为一的宇宙观之后,我们才可了解汉人如何透过对风水的操弄以争取个人的财富、健康与安危。
空间更被建构为有如意识形态或政治经济条件。历史上我们看到传统中国士大夫阶级强调居住格局的内外论常观,而民间社会则信从八方吉凶论。虽然,士大夫也并非不讲究术数,民间社会在能力范围内也尽力仿效士大夫,因而无上下阶层之别。
人类学家图登(Turton)通过对泰国北部村落的研究发现他们房子空间的秩序,是由方位、高度及内部深度来决定。而它也可将家中成员分辨为因年龄、性别、辈份、姻缘及继嗣等之不同而来的分类,也明定成员间的阶序关系。比如,家长在家中的东北角落里生活与睡觉,这儿也是用来祭拜祖先的地方。反之,西边是最脏而南边是最弱之地,因而也成为家中盥洗及招待外人之地。
空间更被视为文化习惯,包括文化的分类观念与个人的实践。但这种主观的习惯或其背后的分类,却是由过去的历史之客观结构所产生的。例如台湾的雅美人认为,人的生命周期或不同阶段的“人”是与房子的建造过程相互界定:一对新婚夫妇婚后先住夫方父母工作房,妻子怀孕生产后就另建一、二门屋与父母分开吃饭而正式独立。以后,在夫妻共同努力下,房子由二门改为三门,之后加盖工作房,再改建为四门屋。等到一方失去配偶后,家屋亦停止发展。而葬礼后,原房屋建材被拆掉而由继承者继承后另建新屋之用。在家屋存在的期间,夫妻不但得分工以维持及发展实际生存所需,更必须在每年的“飞鱼祭”活动中,由男人在自己家屋的后室煮食飞鱼,颠覆男女的角色及家屋中的男女空间之分隔,也将男人所代表的聚落之集体象征转化为个人与家的存在。
2.人类学的空间研究
人类学关于空间研究的探讨,是从涂尔干开始的,他认为当社会的人和事物被分类之后,这些群体又按其相互关系被分类,为了防止冲突必须给每个特殊群体一部分空间,意即人对空间的划分、区别与安排之后,反过来这些安排必须为该社会的个人所理解,这是源自于该社会的集体表现,非取决于个人的力量而是一个有组织且稳定的特质,社会绝不是无逻辑或反逻辑的,它不是乱糟糟或荒谬的存在,所有社会的成员必须承认同样的社会分类基础。空间所呈现的意义对涂尔干来说,是一种先验的基本分类,最终该社会的知识体系才能建立。涂尔干和莫斯在进行空间研究时,认为空间、时间、数字、因果等是每个社会最基本的分类概念:一个社会的整个知识系统,就是由这些基本的分类发展出来的。由于这些先验的基本概念,才能推演出整个知识系统。因此,有关空间的探讨,最终目的就是要了解知识是怎么来的?以及这种知识发展过程背后的基础是什么?也因此,在这些研究背后所蕴藏的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而涂尔干对这回答总是倾向于社会起源的解释。这也是后来大部分人会把涂尔干当成是社会决定论者的原因。
到了功能论,空间被人类学家主要用来反映社会的亲属或社会结构。功能论基本上是想把人类学带上科学实证的道路。例如,人类学家吉莫(D.Gilmore)在对西班牙东南部的一个小镇Fuenmayor做了一个研究。这个小镇18世纪以来就发展出三个阶级:上层阶级是地主,他不需要自己工作,很自由,由佃农或专门出卖劳力的人来替他工作。第二阶层是自耕农,也就是他有土地,但必须靠自己去耕作,有时还必须找一些临时工来帮忙。第三个阶层,也就是下层阶级,靠替别人工作,出卖劳力的人。这社会很清楚是由这三个阶级构成,在这小镇空间组织里,可以看到核心部分是上层阶级所居住的,所有重要的公共设施,包括教堂、医院、学校、城堡等也都在这里。其次就是中产阶级所居住。最外围的是下层阶级居住的,是最近二十年才发展出来的,都是违章建筑,几乎没有街道。像这样的功能论研究,主要目的是在反映社会组织或空间本身是客体化的社会组织。因一般上、下阶级的界定并不易分辨出来,但若透过空间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不同阶级的存在。
功能论不只是把原来的涂尔干学派讨论的问题简单化、机械化,同时忽略了空间分类本身其背后心智上的基础。即它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知识或分类要领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不只是一个先验的分类概念,也是与这知识背后人的心灵机制相关连的。这样的问题,功能论多半忽略了,直到结构论才被认真的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