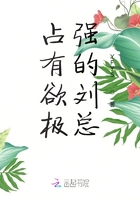花香染襟,一曲琴音婉转悠扬。一丝微风,掀起她眼眸深处的眷恋,无限。回首间,沉香亭畔,春风牡丹,一窗相思,宛若灯火阑珊处的水色胭脂。轻弹如梦的季节,任一双明眸,净若雨露,只想与他花下缠绵。
只一眼,她便醉在了那一弯细描柳眉间。那一点相思,竟让她分不清,于窗前轻舞水袖的佳人究竟是那个从历史的沧桑里走来的女子,还是她的枕边梦里人?窗外花开正浓,芳香四溢,微风吹来,有丝丝缕缕的馨香沁入心扉,更让她思绪缥缈。眼前的如花美眷,无法不令她惊艳,可是她究竟是沉醉于佳人的风采,还是陶醉于他的风流?
她抿嘴轻轻地笑,仿若走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旖旎而又多情。那化了浓妆、甩着水袖的女子,顾眸流盼莲步姗,眼中那抹娇羞,令人沉醉。那一袭梨花白惹蝶翩跹,仿若从远古的墨香里深情地走来。然,伴着远处幽幽的琴音,那女子轻轻一个转身,瞬间便冷了眸中的思念,只留下陌上飘过的胭脂梦,还有那笺上残留的怨君泪,在她眼前明明灭灭。
淡淡水墨风,浓浓古典情,一幅朦胧的景象呈现在她眼前。淡烟微雨中,那一袭青衣、一抹青纱、一柄油纸伞,走在小巷里的丁香女子,却惹得她无限感伤。是畹华。是的,是她的畹华。他娇美可人的扮相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便连她这个枕畔人都无法不沉醉其中,更何况是那些痴迷于他的票友呢?很多时候,她已然分不清他到底是男是女,更不明白,她更留恋男儿身的他还是更欣赏女子装扮的他?究竟,眼前的佳人是她王明华的夫君,还是戏文中的悲情女子呢?
院内,琴师茹莱卿继续忘情地拉着怀中的月琴,轻柔而缠绵。而他,她的畹华,在花间浅吟低唱,仿若烟雨江南的伤情女子,独坐于画舫之上,水袖轻拂,一任那空灵缥渺的曲音,幽怨婉转倾诉无尽的哀怨。凝眸处,他,或是她,静静地在夜中思念,直至有一滴紫色的泪在眼角滑落,滴在她窗前清瘦的琉璃瓶中,滋润了摇曳着的紫色花瓣。转身,一枝花影,千娇百媚的风情,一场隔世爱恋,缠绵缱绻。再回首,千里烟波,水云深处,他水袖轻舞,演绎出古人的万种风情。而那古色古香的景致,却又于她的脑海中流转出一份婉约,一份飘逸。
畹华?真的是你吗?她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盯着他,仿佛眼前轻启朱唇的女子真是从遥远的古代走出的绝世佳人,可是,他又真的不是她的畹华吗?她不禁潸然泪下,却不知是被戏中的情节打动,还是为他的凄凉身世感伤?四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小小年纪不得不背负起家庭的重担。如果不是生逢乱世,抑或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他还会走上这条被人轻贱的戏子之路吗?他红了,可他真的感到快乐了吗?他每天都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女子,不断在台上迎合观众,博取一笑。然,这一切真的都是他心甘情愿的吗?
他是喜欢唱戏的,亦是热爱着那方舞台的。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可自打他走红后,便如同夏夜亮起了油灯,免不了招来各种虫蛾在身边乱扑横飞。她知道,演员受骚扰而影响事业、受诱惑而步入歧途的不乏其例。更何况他的扮相是那么娇美、那么可人,便连她都时常分辨不清,又怎能不提防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对他怀有不好的企图?虽说是民国了,相公堂子早已取消。可畹华在云和堂学戏之初的确曾和表哥王蕙芳一起陪过酒,这便更让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想入非非。到底,该怎样才能还畹华一个干净世界,让他一心一意地唱好戏呢?
叹息声里,只想把魂牵梦萦的相思愁曲卸下尘世中所有的悲与喜,执起他温柔的手,依偎着他宽厚的肩膀,不问世事,化身为蝶,随风而去。然,她亦明白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于是,只能托腮凝望窗外,任思绪顺着风的流向,蔓延。哽咽里,她庆幸自己能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他,可以静静感受他的浓情依恋,却又感伤于而今不知该如何给他一片宁静的天地。畹华啊畹华,该如何,我才能给你一个不浮华、真实、平淡的世界呢?
她不知道,一如既往地茫然。每次他唱戏回来,在替他收拾打点时,总能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三两封语涉猥亵的信笺,而每每这个时候,她的心情便变得异常沉重。都是些什么下三滥写来的不要脸的东西?!激愤之下,她真有给写下这些信的人两大耳光的冲动。然,这样做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谁让畹华身为戏子,必须以女儿身出现在舞台上呢?她开始心灰意冷,甚至生出不让畹华再去唱戏的念头。可畹华除了唱戏什么也不会,这一大家子的人个个要吃饭穿衣,难不成让她出去抛头露面挣钱养家?
畹华仍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唱得她心烦意乱。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畹华的扮相和唱腔都是第一流的,这样的天分如果不唱戏便又大大的可惜了。到底,该怎样才能让他不再受那些无聊之人的骚扰?不让他唱戏是不可能的,别说畹华自己不会放弃,就是梅家的大大小小也不会放任他有这样的想法。
“畹华!”望着俊美的他,她心里突地一颤,立马直起身子,脱口喊了出来。
院外,茹莱卿的月琴声随着她一声断喝,戛然而止。她早已趴伏在床上,泣不成声。
“明华,你这是……”他连忙冲到她身边,伸手抚着她微凉的背抚慰她说,“平常听我唱这出《金山寺》,也不曾见你这么伤心难过,今儿个倒是怎么了?”
“畹华!”她回过头,伤心欲绝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咱们能不能不唱了?”
“啊?”
“咱们不唱了行不行?畹华,就算我求你了!”
“刚才不还好好的,怎么一眨眼的工夫,你就……”
“你只要给我一句话就好,到底是唱还是不唱?”
“这出戏,是刚刚跟陈师傅学来的。怎么,我唱得不好,还是剧情太伤感了?”
“不是!都不是!”她知道,畹华所指的陈师傅是著名京剧兼昆剧演员陈德霖。从上海唱红返回北京后,畹华便于次年,即1914年1月在庆丰堂与王蕙芳同拜陈德霖为师,学习昆曲。陈德霖与谭鑫培合作多年,是清代光绪以来青衣演员的代表人物。其主要特色在于继承老派青衣演唱的传统,偏于阳刚一路。而在唱法上较前人略有变化,在表演上,更是从剧情出发,根据剧中人物的性格来安排行腔的高低急缓,将青衣行当的演唱引领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被人们称做“青衣泰斗”。他不仅唱功极好,是京剧演员以昆剧为基本功的典范人物,且德高望重,由他教出来的戏文又怎会不好?
“那……”
“我就是不想让你唱了!”她抬起头,泪眼蒙眬地望向他,显得有些蛮横不讲道理。
“我……明华,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了?你再唱下去,咱们这个家就要毁了!瞧瞧你,堂堂七尺男儿,做点什么不好,偏偏要扮成女儿身去讨好观众。你要是有个好歹,可教我和大永、五十怎么活?”
“我唱戏,扮女儿身,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吗?”他轻轻拍着她的肩,语气平缓地说,“再说,这是艺术,又不是……”
“艺术?艺术就可以让什么苍蝇都能叮到自己头上来吗?”她突地起身,拉开抽屉从里面掏出数百封齐如山写来的信,瞬间撕了个稀巴烂,“要再唱下去,你就毁了!”
“明华!这些信可都是齐先生写来的,齐先生可是正经人!”他一边伸手抢她没来得及撕毁的信,一边劝她说,“齐先生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我只知道,再让你唱下去,这日子便没法过了!三天两头收到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写来的信,你就不怕有一天弄得身败名裂吗?”
“咱们唱戏的,不就是靠自个儿自觉吗?”他叹口气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你又何必操这个心?”
“再不操心,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她哭得眼睛红红的,“畹华,你听我一句好不好?求你了!”
“你知道的,唱戏就是我的命。我是不会离开舞台的。”
“可你也得替大永和五十着想。我……”
“明华,你在担心什么?是怕我受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贻误了性情?”
“我……”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他深情凝视着她,轻轻吻着她凌乱了的发,“放心,我是不会让你和家人蒙羞的。”
“可我……”
她不是不放心他,而是实在不能相信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也许,只是她想得太多,事情本身并没那么恐怖。然,出于对他一片赤诚的爱,她还是无法让自己做到无动于衷。于是,她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像他一样,走到后台去。只要走到后台,便可以替畹华排除干扰,何乐而不为呢?
“什么?你不知道后台历来都不让女子涉足吗?那可是祖师爷定下的规矩!”
“规矩是人定的,为什么改不得?再说现在都民国了,哪还有那么多讲究?”自从嫁到梅家后,她不仅成为他生活上的贤内助,更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虽然从未跟父兄正儿八经地学过唱戏,但出身于梨园世家的她在梳妆上却是极有天赋的,不论多么复杂的头型,她都能够梳得漂漂亮亮。所以在畹华初期演古装戏时,出门往戏馆去,随身总会带着一个木盒子,那里面装的便是她在家为他梳好的假发式。畹华上台前只需要把假头发往头上一套,一个精致的古代美人便立刻活脱脱出现在观众眼前了。她梳的发式甚至连戏班子里专门负责梳妆的老师傅都梳不出来,所以他也总是乐意带着她在家为他梳好的假发式去赶唱各种堂会和营业戏。一来二去,演戏的、听戏的都知道了她这一手绝活。再后来,时间一长,便有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她是亲自到后台为梅兰芳梳妆的。既然大家都如此认为,为何不趁此机会直接走出去呢?
“田老板是不会同意的。”
“你刚刚演了田老板的时装新戏《孽海波澜》,票房那么好,这点小事他怎能不应承?”她知道畹华说的田老板是他眼下搭班的翊文社老板田际云,“给他赚那么多钱,为你破个规矩就不成吗?再说,事先做好的发式毕竟不如现场做的好,一来可以让你的扮相更美,二来也好替你打发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有什么不好?”
“你容我想想。”他不无为难地盯着她,“几百年的老规矩,不是说打破就打破了的。”
“你要面薄开不了口,我自己找田老板说去。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一个大老爷们说不出口的话,就交给我去办好了。”
便这样,她终于打破陈规,走进了祖师爷禁止女人涉足的后台。毅然将畹华演出前的梳头、化妆等活通通揽了过来,不仅得以时常相伴在他身侧,更让他身边顿时清静了许多。那些个日子里,她每天都穿着男人的衣服,跟着他出没于各种堂会和营业戏的后台,精心为他描眉、梳妆,兢兢业业,从不倦怠。她把自己当成了他的影子,这世间,他若安好,便是她一片晴天。月影朦胧,星子无声,夜已深了,可她却毫无睡意,仍然独守窗前,捻一丝月夜的缱绻与孤寂。心,有着淡淡的喜,又掺杂着淡淡的哀愁。
他的辛苦,他的无奈,他的汗水,他的隐忍,他的种种不得已,都随着她走进后台,一一进入她的眼帘。此时此刻,她对他更多了一份心疼、一份眷恋,这么好的男子,到底要怎样才能给他更加明媚的天空?回眸,清风舞着心绪在子夜独醉,看似无意却泪眼纷飞。冷寂的月下,徘徊在忧伤的窗口,她轻叹,忧郁的心儿却更加迷恋那幽暗里的朦胧月色。畹华啊畹华,你所有的伤所有的痛,我都看入了眼里烙进了心底。可是除了给你梳出更精美的发饰、化出更美丽的妆容,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可知,我若是那一缕飞絮,定会飞入你的梦,让你夜夜梦中与我共舞?然,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愿意与你一起挣扎于这个污浊世界里的平凡女子。只能与你紧紧相偎,却不能陪你走出那片黑暗的森林,更不能为你分担哪怕是一分一毫的忧愁。
他不知,她和他的相遇虽然平淡无奇,却留给她此生最深的眷恋。回首,昏暗的月色,照着他朦胧的脸颊。她却不敢看他留在纸笺上的缱绻情丝,不敢冥思他话语间的爱意缠绵,不敢凝视他如水的清眸,只因不知他温柔的怀抱能容下与她的几世情缘。总是喜欢在子夜细细品味他唱过的戏文,品戏文里属于他的柔情缱绻,品戏文字属于他的寂寞孤单,品戏文里属于他的婉约哀怨,那一字字的缠绵、一言言的缱绻,都令她泪眼婆娑。
都说人生如戏,那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唱词不仅折射出万千相思,更让世间缠绵悱恻的情丝在他指间捋成锦锻。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从古至今,有多少情伤揉碎了多少痴心,又有多少痴情男女迷失了自己?舞台上他扮演的悲情女子如是,舞台下他身边的她又何尝不是?借着一缕暗淡的灯光,她又在镜前为他梳起了古代仕女的发髻。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她必须在年底他再赴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新戏前把它设计好,那样便能让上海观众见到一个有别于去年的全新的梅兰芳了。她知道,虽然仅仅过去一年,但此时丹桂第一台的老板却已由许少卿变成了尤鸿卿和文凤祥。不过老板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畹华有了第二次南下上海演出的机会,她一定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让他给上海观众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夜,像千年的媚狐,诱惑着灯下孤寂的灵魂。无边的忧郁,在她眼底缓缓洇开,眼前亦不断回放着有他相伴的每一个片段。总是想让他成为众人眼里的焦点,所以总是想为他做到最好,可又担心做得太好,他又会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再次招来些不三不四之人的骚扰。于是,她总是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便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的灾难。
轻轻掉转过头,紧紧咬着嘴唇,她手里的梳妆活做得越来越麻利,而心里却仍然裹着一股无法言述的惆怅。到底,是什么让她变得如此魂不守舍?她说不上来。她只知道,这些日子里,她毫无来由地爱上了这片晦暗的夜、这片摇曳的灯火,还有指尖轻触假发髻的微凉。总是乐于守着一份夜的寂静,伴着熟睡中的他,任一束乌发于指间拢来又散去。
畹华,你不会知道的,这片寂静的夜,却能让我的灵魂变得平静,让我为你流下满地晶莹的泪。如果说这世间除了你还有谁更加懂我知我,便是窗外这片晦暗的夜了。你可知,若你也有同样的忧伤,那我宁愿独守花残、独伴月落,用尽一世痴情,换你今生不再伤怀?
发髻在她手里几经转变,然而她仍然不能满意,如果不能为他梳出最精美的发式,那么她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更夜寒,月儿美,幽暗的灯火朦胧,梦中的他是否依旧还在笺上为她写下心间的情丝?心在等,眸在盼,她固守在梳妆台前,用缱绻的情丝把他的忧愁轻弹,若是没了忧愁,他唱出的曲曲深情戏文便会更加动人。只是,她默默等待的又是什么?是他的功成名就,还是他对她的款款深情?她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辞辛劳又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博他一笑,抑或是博取众人对她在他背后默默付出的赞扬?
她只是想为他做些什么,再多做些什么,仅此而已。他红了,红遍了京城,红遍了上海,已然是京剧舞台上首屈一指的龙头人物。然而在她心里,他却依然是那个懵懂天真,甚至有些木讷的畹华,所以她总是想方设法地为他付出更多,更多……
再回首,颦眉间,一个崭新的、繁复的而又精美的发髻终于在她灵巧的手指下成型。她终于长吁了一口气,为自己的再一次成功自豪并骄傲着,亦为他可以以全新的形象再一次站在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舞台上与上海观众见面而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