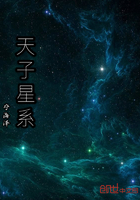“妈,开大灵还是小灵?”蓝强走到母亲面前,本想安慰两句,说出口却是这句硬邦邦的话。
“你婆说拿一张席子把她拖出去,挖一个凼凼埋了就是。”李桂兰不住地捶打脑壳,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张五娘走过来把李桂兰搀扶到屋檐下坐着,安慰道:“人都死了,哭也没有用。你又没有姊妹,啥子事都要你来撑。你要立起,不要倒下!”
李大婆的卧室在底楼,光线不好,窗子又被她用塑料胶布封得严严实实。其实除了睡觉,她哪有时间在卧室里呆。可她就是讨厌光,讨厌来自外界的干扰,也许她把自己早已交给黑暗,交给她的私塾先生。她落气后,爆了火炮,邻近的邓老表跑过来把床拆了,只剩下一堆木头支架贴在黑黢黢的墙壁上。人一死,床就不叫床,叫停尸板板了。如果不立即拆除,死人会回来返魂。消除了死者的最后回路,人们叫李桂兰赶快将屋子里所有的渣滓扫拢,撮起来专门装着,名曰“财”。说来也奇怪,死者用过的东西要毁掉,死者房间里的渣滓却要保留,真不知道哪朝哪代的哪位大仙将此法传给记性特好的农人们,就成了农村雷都打不动的规矩。
蓝丙一把望山钱托回来了,找来一根最长的,梢尾有鱼竿一样弹力的一年青竹子,把望山钱立在场坝边。红纸扎的望山钱表示死者满了六十岁,有寿终正寝的意思,算是喜丧。望山钱的纸片数是死者的岁数,李大婆的虚岁是八十又四,算是农村里的寿星,她的望山钱扎了三层。外面红,里面白的纸片在空中翻飞,像一团飘荡的鲜血,能立刻把人的精气神活活捉住。大多数人是不敢看望山钱的,尤其是在阴风惨惨的傍晚,瞄一眼青皮的竹竿就把人的魂魄镇住了,更不要说看血红的望山钱。
按照习俗,人死了在家停三天,长明灯也要一直点着,每顿饭也要换上新鲜的。这一切蓝强都一手做了,晚上他坚持坐在堂屋里看书守灵。人们告诉他第一天晚上最好不守,保存体力,第二晚才必须守。蓝强不听,一句话也不说,晚上守,白天照样跑上跑下,连羊都不管了。还好,丧事帮忙的人特别多,不需要主人家多操心,蓝丙一只好长驻竹里馆了。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烧香的人来了很多,吃斋饭的人也不少,这一切都是李队长安排人应酬。蓝强一家跟着道士到井水边取水,然后在堂屋里胡乱地敲打两下,唱了两下,那些道士就脱去道袍,抽烟的抽烟,打手机的打手机。蓝强气愤不已,狠狠地盯着那些亵渎外婆魂灵的伪道士。
“嘻嘻,蓝连长,没有办法,你不要那样子望着我。咱是弟兄,我就嘴里有半斤,说出来五两,有多少说多少吧。你妈硬要开小灵,我们劝都劝不到。你想想这个年头哪个还开小灵嘛,人家城里的有钱人做道场还是七天呢!你妈舍不得钱,一百二十块钱的小灵本来就不必带锣鼓家伙的,更不必叫上这几个哥们。我完全都是看在亲戚的份上,等于自己掏钱给你婆开灵。再加上你们运气好,我们哥几个聚齐要到李村那个大家都晓得的廖老师家去。廖老师今天早上死的,他家六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有的当官,有的当医生,有的在部队头。他到城里住了近十年,人家天天由保姆照顾,活了九十多岁。现在要弄回来埋,叫我们去开灵,做昼宵。咱们该明天早上才去,人家硬要叫我们今天就去看地,设道场,要整得巴适。没得办法,一千八的价钱,我们几个也要吃饭,对不住了。当然,你现在加钱喊我继续整,我也不会答应你。李大婆对我好,我才这样说。你晓得现在再整都是什么重丧三丧之类的,这样不好,而且都是假的,我不会整你们。啊,对不住了!”陈道士猛抽完最后一口烟,手一招,一行人转身走了。
蓝强很想叫他们回来,给钱重新开一个大灵,又知道不可能。外婆生前不信这些,他也明白这些都是形式。可是看着堂屋里只有一盏孤灯陪着一口木头本色的素棺材,什么经幡,道场都没有时,他的心被抽离了。人生的告别仪式就如此草率,如此凄凉,难道这就是外婆的宿命?一辈子就这一次了,为什么不应该热热闹闹地送她一程?外面喝酒吃肉的人正酣,他觉得那与自己无关,他的心已经随着外婆的灵魂去了,再也不愿意留在这个热闹又嘈杂的人世。
“哎呀,蓝连长,在这里呀,快出来说话。”夏清明站在门口对着棺材作了一个揖。
“有什么事跟我妈说。”蓝强坐在棺材旁边头也不回。
“出来嘛!哦,蓝幺娘来了。来,出来我跟你说,肯定是要土葬的是不是?当着大家的面收两千的丧葬费,跟其他人家是一样的,不能因为你家有村干部就例外,是不是?”他边说边回头看,发现场坝里吃斋饭的人都往这边望时,故意提高音量大声说。
“啥子丧葬费哟,你这不是敲棒棒嘛?你以为娘家没人吗?”李大婆的侄儿侄女一拥而上。
“三个菩萨两烛香,没你们的事!”夏清明急得直跺脚。他想拉李桂兰到旁边去说话,却被团团围住。在人群里东张西望,终于看到蓝强从堂屋走出来,他连忙叫道:“蓝连长,蓝连长,你过来看看。”
“看啥子看,你想欺负他年轻不经事吗?”
“哎呀,你们再这样围着我,你们要后悔的。你看,蓝连长叫我到那边去说话呢!”
众人看见蓝强确实在屋檐下站着,也就不便阻拦。夏清明一个箭步冲上去,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说完又走开了。
等蓝强回堂屋时,手里捏着一叠钱。夏清明跟着进来接过钱,把一张发票递给他后就走了。
李桂兰上前一把夺过发票,看见上面分明写着两千,脸色骤然一变,一把甩在地上,恶狠狠地问:“你三更天做梦呀,昏头昏脑的,你在哪里拿的钱?”
“我没有拿钱,”蓝强有气无力地说,“他说他来实践诺言,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李桂兰忽然想起什么,捡起发票,满意地笑了一下,转过身来对着那些不解的亲戚又装模作样地骂了一通。
蓝红突然挤上前,把李桂兰拉在屋里问:“你晓不晓得人家村长没有收钱?”见李桂兰点点头他放心地舒一口气说:“刚才村长见我个人守金井,小声跟我说他叫幺弟代他敬香时,故意放了两千元钱在幺弟的衣服口袋里。然后他和幺弟当着大家的面演了一场戏,让大家都知道收了钱的。幺弟有点精神恍惚,他害怕我们蒙在鼓里,叫我来告诉你。他还问了我老板的电话号码,让我给老板打电话,希望老板来投资办水钻厂。他说村里出土地,不要钱,只要老板把马路修进来。”
“这个事等你幺弟清醒后,跟他商量。听你幺弟说诺言,我就晓得是你幺弟跟他一起去收丧葬费的事。不过你婆的这个事千万不要伸张,别人晓得后人家不好相处,你幺弟以后也不好做工作。”两人商议定后走出来,见蓝强还在棺材旁呆着。李桂兰大声地对着场坝说:“钱都交了,算了,不说啦,大家吃饭哈吃饭!”
第三天早上八点,没有道士,蓝丙一握住曾经被李大婆放过鲜血的公鸡,挤破冠子,在堂屋门口洒了一地的鲜血后,把公鸡一抛,大声地对着抬棺材的八个大汉喊:“出不出?”
“出!”曾经抬了蓝丙一家水泥板的抬匠发出沉闷的回声。
蓝丙一挥舞弯刀在门槛上一砍,棺材就被抬出去了。李桂兰走在前面拿着镰刀边走边砍,蓝红举着引路幡,蓝强端着米筛,里面放着灵位、钱纸、蜡烛和香。
送到后面的竹林边,那地方是李大婆自己看上的。阴阳先生说:“‘弯弯屋基,嘴嘴坟’,那地势有依靠,能发后人。”
端着灵位跪在金井旁,看着外婆的棺材轻轻地落下,看着一铲一铲的泥土落下,看着一堆黄土耸起,好像跪在冰川雪地,蓝强的心都凉透了,一个劲地猛烧钱纸。从此,她就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留下的只是一堆土,一堆啥子也不晓得的土。
队里的人收拾桌椅板凳回了家,李桂兰按照惯例给抬棺材的人包了红包。还有煮饭的,洗碗的分别也包了,全交给李队长去分发。亲戚陆陆续续散了,一家人把孝布和麻绳取下来由李桂兰存着满“五七”时用。李桂兰查看账本,蓝红收拾家具,蓝丙一去了竹里馆,葵花快生了,呆在房间里,却不见蓝强的踪影。
蓝红四处寻找呼唤,不见影子,猛然想起把外婆送出去后就没回来。急急忙忙跑到坟前一看,发现他还披麻戴孝地坐在坟台上。蜡烛已经燃完,剩下一根染过红泪的竹签,钱纸灰飞遍蓝强的全身,香还有一寸长没燃完,差点就点着他的裤腿。失魂落魄的蓝强就那样睡着了。
“幺弟,回家。”蓝红把蓝强摇醒,蹲下来想要把他背回去。
“回家?不要吵我!”蓝强睁开眼睛一看又闭上,嘴角还保持着微笑。
“走,到床上去是一样的。”蓝红用力,背着走了两步,突然一个趔趄两人一起又滚回坟台。
蓝强的脑袋在砖砌的坟台上一磕,一个血红的大包把他唤回人间,他才发现倒在地上的哥脸色乌青。压抑太久的怨气猛然上升,他像一头发疯的狮子一样喊叫:“哥,哥你不要死!哦,哥,快起来!”
把哥背回家,轻轻放在床上,喂了一些糖盐水,看见他的脸色渐渐恢复,蓝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来到堂屋,空空如也。他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