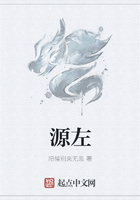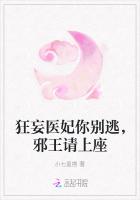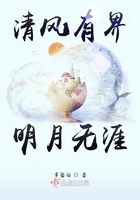梁国京城酒楼,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大梁国的酒客一改往常的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却是将那国祚大事作下酒菜把酒言欢。且说一年前,大梁国皇帝御驾亲征,一路过关斩将,直接将战火烧到南秦国都,端的是骁勇之士,王者之师。而今更是大梁军队凯旋而归的良辰吉日,偌大梁国举国上下日月同辉,普天同庆。
要说这大梁国,本是东胜神洲,天启王朝的新立属国,天启525年,天启王朝西楚公国,国君昏庸无道,上不觐天朝,下不理民政,时逢连年大旱,公国上下饿殍遍野。楚国地方太守荀志雄在李文禄的扶持下领兵起义推翻了西楚公国,自立国号梁,而后又经过几年休养生息,几年战火纷飞,大梁国终于得到了天朝认可,获封大梁王国。
天启553年,天启王朝正值春秋鼎盛的天子肖溟因修行缘故走火入魔最终身死道消,年仅十岁的小天子肖恒继位。天启555年王朝的统摄力日益衰弱,诸多属国自立为主,不在朝觐天启王朝,其中以南秦王国尤为甚之。南秦王国,坐拥江南富硕之地,国富民强,南秦国主对于天下共主之位蓄意已久,竟趁着小天子刚刚继位不韵朝事的空子,驱兵北上,灭掉沿途姜国,乐国等拱卫王朝的王国直捣黄龙,干起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更是过分到将南秦王国改为大秦帝国。这倒也罢了,大梁王国本着事不关己己不劳心也就没有太过在意。谁成想,仅仅两年光景 西楚帝国越发的得寸进尺,竟然打着天启王朝的幌子,公然挑衅曾经结果梁子的大梁王国,旧事重提,以大梁王国国主荀志雄得位不正为由,削藩。
为此已近古稀之年的荀志雄大动肝火,不顾高龄御驾亲征,打着勤王。清君侧的旗号,征讨南秦。南秦虽国力强盛,近几年的养尊处优,却是让秦国人忘了什么是居危思安,供养的几十万兵将尽是些酒囊饭袋,大梁军队所到之处,南秦兵将如树倒猢狲散,仅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秦国国主的脑袋便被悬挂在天启城的城门之上。荀志雄匡扶了天启王朝的社稷,被天子赏赐了秦国的土地,成为天启王朝的数一数二的强大王国。
梁国京都,一身金红龙袍,垂垂老矣的荀志雄正襟危坐于大殿龙椅之上,俯视群臣。其身旁下方不远处设立一略小的红木座椅,上面坐着一位耄耋之年精神却是依旧抖擞的魁梧老者。此人便是为大梁国武道第一人,同时也是大梁国开国第一功臣,被誉为大梁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柱国李文禄。
“诸位爱卿,若无公事禀报于寡人,便散去吧!”荀志雄老态龙钟,神情略显疲惫的挥了挥手边衣袖。
大殿下方的几名官员,神态略有局促,相互对视几眼,终有一身着红色獬豸官袍的中年汉子一脸愤慨的站了出来。
“陛下,微臣请奏!”
中年汉子,身材纤瘦,一脸的正义难掩悲愤之相。
“哦?何爱卿,所奏何事?”
荀志雄略显头疼的问道。对于这个何显昭,荀志雄着实是不甚待见。这也难怪,纵观历朝历代,哪个御史言官不是帝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陛下,臣素闻国柱之孙李长风,恃宠而骄,在整个京城嚣张跋扈那是无人不晓,前些时日陛下凯旋之际,此子竟然在明月酒楼大放厥词,扬言李家应与陛下共分天下。这等不臣之言理应问斩”说话间,何显昭身形颤抖,胸腔怒火愤愤难平。
此话一出,满朝文武百官尽皆失色,窸窸窣窣的轻声细语遍布朝堂。
李文禄双眼微眯,细细打量着整个朝堂,当他看到正一脸玩味等着看自己笑话的当朝宰相林若甫,李文禄心中有所思量,不过他并没有对此发变任何言语,只继续气定神闲的把玩着手中的石球。
“荒谬!”荀志雄狠狠地将手拍在龙案之上,眼中凶光毕露的看向何显昭。
“陛下息怒!”一众大臣见此尽皆寒蝉若禁,天子一怒赤血千里,稍有不慎,这朝堂之上便会有人脑袋搬家。
“来人呀,何显昭妖言惑众,企图离间君臣,殃及国本,拖出去杖责五十!”荀志雄大袖一挥,愤然离去。
何显昭见此顿时方寸大乱,“还望陛下圣明呀,李文禄之心,路人皆知,天下是陛下的天下.......”
“这......陛下,陛下开恩!”一众御史台官员连连叩首,乞求皇帝开恩,就连自以为稳操胜券的林若甫也是一脸诧异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李长风平时是跋扈了一些,在酒楼也的确有过一些言语,不过不是何显昭所言这般,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浪荡话,被有心人胡编乱造一通,传到了这位刚正不阿的御史大夫耳中。
李文禄在朝中树大招风,功高震主,素来被人所诟病,一些人气不过,便想通过何显昭的嘴,敲打敲打李家,谁成想陛下非但不追责李文禄,反倒重杖何显昭,杖责言官这可算是开创了历史先河。
荀志雄离开不久,李文禄也在一群武官的簇拥下老神在在的走出大殿,只留下一群文官不知所措。
京都城,上柱国府。
“见过老爷!”
李文禄走进府内堂屋,一路上李家下人们恭敬的打着招呼。
“爹,您回来了!”此时,李家次子李义石早已在厅堂之内恭候多时。
“嗯!”李文禄点了点头。“你大哥和三弟有消息了吗?”
“前两日探子来报,巨鹿,九灵两国节节败退,想来大哥他们不日便会凯旋而归。”李义石恭恭敬敬的回答道。如果说对于自己的父亲,李义石是敬畏有加的话,那么对于他的大哥李义山便是钦佩不已。从小到大,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为人处世,李义山一直是李义石的榜样。而他这三弟李义儒更是不简单,轮修为武功,不能与他的两个兄长相提并论,可要是说到谋略真是深得老爷子真传。
“哼,小小巨鹿竟然在我方讨伐秦国之际,联合九灵举兵来犯,真是不知死活。”李文禄冷哼一声,语气有些冷漠。
“父亲大人,儿臣听闻朝堂之上有些不太平,不知父亲打算.......”李义石小心翼翼的问道。
“石儿,你这消息来得倒是挺快,都是些跳梁小丑罢了,不足挂齿。至于这个林若甫,他修儒道,我入武道,速来就与我政见不合,有点小动作,只要不殃及国本,倒也不用放在心上。”李文禄端起茶杯,缓缓地抿了一口御赐的上好参茶。
李义石有些担忧的说道:“可是陛下那边,父亲......”
“呵呵,你呀,终究是没有老大老三通透。陛下何等聪明之人,就算长风真的说出了那不臣之言,只要边境一日不安定,咱们李家便一日不会倒。”李文禄微微一笑,食指轻轻的敲打着桌面。“去差人,将我那宝贝孙儿叫来,我有些话要与他讲。”在李家第三代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还真就非这李长风莫属。
李家三代,李文禄育有三子,李义山,李义石,李义儒。
长子李义山又育有三女两子,大女儿李言欢已经下嫁到礼部尚书府,二女儿李言歌入大梁道家大衍道门修行。至于这第三子便是李长风,不通兵法,不喜修行,整日里不修边幅的在酒楼里与诸多狐朋狗友吟诗作对好不快活,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浪荡子却又深得李家老爷子以及自己两个叔叔的喜爱,原因不在于他是李家的嫡长孙,而在于长了一张好嘴,最会讨人欢喜。李家第四子名为李长空,憨憨傻傻,忠厚老实。至于这最后一位李言玉并非是李义山的亲生女儿,而是李义山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从死人堆里捡来的,收养为女,只是李家人看她年幼便一直没有将此事告知于她。
次子李义石,膝下一儿一女,儿子李长河忠厚仁义,在外界名声好过李长风千百倍,次女李言舞跟着李言歌入了道门。
三子李义儒膝下无儿无女,一心只在谋略,并未娶妻生子倒是李家老爷子的一块心病,不过整个李家除了老爷子,要说谁最宠爱李长空还就非李义儒莫属了。
“好的父亲,我这就差人去办。”
李义石刚准备动身,一个身着蟒袍,长相阴柔的男子,正用一手托着拂尘,另一只手端着黄色卷轴在一圈锦衣护卫的陪同下走进李家厅堂。
“上柱国李文禄接旨~”
尖锐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堂屋。
李文禄连忙起身,连同身旁的李义石齐齐下跪领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尉李文禄,初随寡人打天下,立下战功无数,而今又是随朕征讨秦国,劳苦功高,今封尔为大梁国第一等公爵,镇国公,享粮三千五百石,封地为北燕,李家长子李义山北拒巨鹿九灵,功勋显著,次子李义石,李义儒素有功劳,今封李义山为兵部右侍郎,赐爵忠勇侯,李义石为京都城兵马司,御史副都尉,赐爵靖节伯,李义儒为礼部左侍郎,赐爵安泰伯,钦此。”
“镇国公,还不快接旨!”
说话间,这位宫里来头极大的公公身体微微弯曲的将圣旨递到李文禄面前。“镇国公,今后可要多为陛下效力,陛下可是待你们李家不薄呀。”
“微臣领旨,谢主隆恩。”接过圣旨,李文禄起身满脸堆笑的说道:“有劳公公了,石儿,快去取来金银细软,犒劳一下公公们。”
“哎吆,镇国公严重了,不敢当,不敢当呀。”嘴上这样说,大梁第一大太监章玉还是接过了金银珠宝,递给身后的侍从们。
“章公公,今后在陛下面前,还望美言几句!”李文禄客气的寒暄道。
“那是自然,今个咱家还得回去复旨,就不讨饶了!”
“石儿,还不快送送公公们!”
李文禄手中拿着圣旨,目送着离去的众人,喜忧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