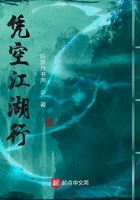天色渐暗,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平静的湖面,溅起一圈圈涟漪。湖面上水雾弥漫,将远方的森林变得模糊不清,低沉清冷的空气一阵荡漾,带来了雨天特有的沁人气息。
一艘寻常的小木船在湖中飘着,雨珠落在棚顶上,顺着边缘滑下,在檐角连成一串。雨幕轻轻笼罩在小船周围,似要将一切隔绝。
却有一根长竿划破雨幕,从窗中直直地探向水面,其顶端垂下微不可见的细线,落入清澈的水里。
细线尽头拴着一个串着饵的小钩,香味渐渐在水下传开。突然,一抹黑影窜了过来,它瞪着硕大的眼,一身黑鳞光滑细密。黑影绕着钩游了几圈,缓缓靠近那散发着诱人气味的饵,还有隐藏其内锋利的钩。
一种莫名的危险感让它有些犹豫,但还是抵挡不过食物的诱惑。它顿了顿,嘴巴开阖间,紧紧含住了饵的一角,鱼鳍快速拍动着水,死死地往后拉扯,船中人握竿的手感到绷直的鱼线上传来一丝丝力量,他手轻摆,湖边翠竹做的长竿随之颤动,一股奇巧力道顺着透明鱼线传入湖中,鱼线抖成一条波浪,线那端挂的铁钩骤然破饵而出,往鱼唇内刺去。
那鱼却反应极快,它流线形的身子一侧,铁钩只在它紧密黑鳞上擦出一条细痕,它满意地吞下已无束缚的饵食,尾巴一摆,轻飘飘地游走了。
船中人提竿收线,不出意料钩上光溜溜的。
“我还真不信了。”他面露狠色,把空荡荡的钩子收回手里,然后将另一个备用的铁钩也一同绑了上去,两个锋利钩尖朝两边突出,船中人再取出一块切成长条的肉,一圈圈绕在了双重钩子上。做完这些后,他盘腿在小船的雨篷下坐好,一甩竿,双重钩牵着鱼线飞向不远处的湖中落下,一线水纹荡开。
那只尝到了甜头的黑鱼还未游远,此时见到又有食物坠入水中,它瞪着眼摆尾游来,想故技重施吞下那块香喷喷的肉,正当它靠近的时候,却仿佛接收到什么指令一般,不仅没再往前游动,还后退了几分,悬停了下来。
一个几乎有这条黑鱼近十倍大的黑影从湖底上浮,看似缓慢,但很快就到了相对小巧的黑鱼边上,那庞大的身躯才显现出来,那也是一条同种类黑鱼,是不知在这湖里活了多久的老怪物了,身长足有七八尺,一身漆黑鳞片硕大厚实,唇边已生出两根如虬长须,连端坐船上之人都能看到水下的巨大阴影。
“哟,来了个大家伙。”船中人顿时兴奋起来,他坐正了身子,右手握竿,眼神紧紧盯着那水中隐约可见的模糊影子,就待它一触即发,那嘴生虬须的巨大黑鱼谨慎地停在距那块饵肉稍远的地方,却没有直接去试探,而是用力一摆尾,一道无形水浪击出,撞在了双重钩上,鱼钩带着透明细线左摇右晃,船中人咧嘴一笑,敢情是在挑战我?
船中人回敬似的一抖腕,长竿偏转,隐藏在饵肉内的锋利钩子猛地荡了过去,去势极快,大黑鱼虽庞大却很灵活,不见它的宽大侧鳍如何动作,整个身躯便稍稍横移,恰好避过袭来的铁钩,船中人笑容不减,那钩子绕了一圈又划破水流荡回,速度更添几分,大黑鱼毫不惊慌,它左右鳍连连挥动,躲过这一钩,以及接下来数次如一的回马钩。
船中人脸上笑意愈加浓郁,他每次抖腕后钩子的借力回弹都会越来越快,这难得一见的超大号黑鱼不可能始终避得过去,更何况接下来还有他准备好的一招。
那双重钩袭去复杀回,大黑鱼面对着速度渐增的饵中钩开始有些捉襟见肘,根本没注意到那不起眼的透明鱼线已围着它绕了一圈又一圈。
船中人眼中精光闪现。
“收!”
他沉喝一声,闲余的左手在竹竿一侧重重拍下,碧色长竿顿时弯出一个大弧,然后竿身瞬间崩直,水中胡乱缠绕的鱼线随即如山林中捕到野兽的铁夹迅速收拢,其中大黑鱼再如何灵活,都是那瓮中之鳖逃脱不得。
可还未待船中人高兴几下,清澈的水里再起变化,只见那活了百年有余的大黑鱼迎上笼罩过来的天罗地网,浑身黑鳞接连倒竖,道道暗流若利刃般横冲直撞四散炸开,将结实的鱼线之网斩了个七零八落,同时大黑鱼身形前冲,一口咬住已从钩上掉落的肉块。
这一切只发生在瞬息之间,船中人还没反应过来,大黑鱼就已挣脱捆缚,含走饵食,甚至浮到水面拍了拍大尾。
船中人脸色奇差,挥手挡住那该死的鱼拍起的水花,收竿回来,别说钩子,连线都少了一大截。
在他旁边放鱼的大桶和放饵的小碗里空空如也。
“哎,今天又是空手而归。”他叹道,将鱼竿收起,瞄了一眼篷外的天。
这雨短时间内是不会停了。
他边想着,身体就往后一倒,双手枕在脑后,听着雨珠落在船板上哗哗的声响。
雨声依旧动听。
小船随着湖水涨落轻轻摇晃,他闭上双眼,嘴角微微上扬,弯出一抹极淡的弧度,似已沉沉睡去。
...
另一处。
微弱的烛火摇曳着,照出一片昏黄。
这里是一间密室,四周皆是粗糙厚实的石壁,除了这烛火外,再无半点光亮。
密室中央有一石台,此时却有人立于石台边上,面目都融于黑暗中不甚清楚,只隐然可见其身着华丽的锦袍,在烛火的照耀下隐隐反射出金红色的光。
他伸手抚上石台,有种凹凸不平的触感,那是石台上刻出的纹路,一条条延伸交错有如血管一般满布整个石台表面,它们游动着,汇聚石台之上。
他目光随手掌的抚摸缓缓上移,到纹路汇聚的中心,眼神忽然冷冽起来。
在中心处,纹路汇聚成了一个大致为圆形的图纹。
可那繁复无比的图纹,赫然只有一半!
凝视片刻,锦袍人熄灭蜡烛,黑暗刹那间弥漫开来,他却有若未觉。锦袍人转身走出狭窄的密室,石门外是一道同样简陋的石阶,在黑暗中向上延伸而去。
锦袍人稳稳地踏在石阶上,一步一步往上迈去。片刻后,他停了下来,石阶似乎到了尽头。
“咔咔。”几声轻响,几道光线从石缝中透了出来,紧接着大放光明。
石墙完全敞开,外头却是一排排整齐的书架,房间正中摆着一张宽大的书案,如墨般浓稠的暗色令它显得很是低调深沉,其上却放有一方掌心大小的古砚,砚台一端立起几座险山,古松倒挂,绝壁间若有道湍流垂下,直直落入砚中的天池,一看就是极为名贵的艺术品。
此处是一间书房。
锦袍人自漆黑通道内走出,石壁缓缓合上,他缓步走到宽大的书桌边,桌前有张同样暗沉色调的硬木大椅,座椅上没有任何软垫,靠背扶手棱角分明。锦袍人坐下,背微微往后靠,身板挺得笔直。
书房内光线不暗,映出锦袍人的脸,他看起来年岁并不是很大,顶天就三十岁左右,但他眼角的细微皱纹和双鬓的霜白却遮掩不住,人已中年却依旧英俊倜傥的锦袍人轻轻拿过那方桌上的砚台,砚中池隔夜浓墨仍如新磨。这方古砚名为“绝松”,质温如玉,扣之无声,存墨不腐,于端砚中也是上上之品,经名家之手雕出绝壁倚松象,那位大家如今故去,此砚即成绝响,其价连城。
锦袍人从笔架上拿起一支最常用的硬毫笔,在砚中左右轻蘸,端正姿态,一笔落在桌前铺开的大宣上,他表情无比认真,毫墨挥洒,一气呵成。
宣纸上出现一行如龙蛇舞动的字,笔画劲力十足,弯折处若刀削般锋芒尽显。
“山雨欲来风满楼。”
锦袍人低头望着这行字,轻声念道。
他放下笔,在旁边书架上随意抓了一把,然后径直走出书房,穿过走道,进入亮堂的长廊,兀地停住了,身上若有威势散发的锦袍人负手站定,一言未发。
在其身后,一个人影忽然自长廊中浮现,同时一个嘶哑的声音传来:“踪迹已确认。”
锦袍人默然几息,轻声说道:“知道了。”
说完,他身形一动,重新往前走去,那人影静立不语,尚未动作,直待锦袍人不见后,其身体竟渐渐淡去,化成了阴影。
锦袍人继续顺着长廊走着,廊道两旁栏杆布满古朴而精美的雕纹,如云团聚又飘向一人合抱的栏柱,廊顶离地一丈,两端檐角突出之处皆挂上了小巧风铃,此时风起,风铃便轻轻作响,大有一种清泠意味。他走过长廊的一个拐角,出了纯色黑瓦搭建的屋檐,踏在错落有致的卵石道上,步入院中。
说是说院子,但似乎称为园林更为合适,院中细碎的卵石道旁皆是各类观赏绿植,叶子上还挂着不少露珠,瞧着就清新喜人,绿树一过便是假山,近两人高的山岩极为逼真,巨石古松银瀑一一不少,仿若直接将一座崇山峻岭用那仙人手段给搬了回来。锦袍人如散步般慢慢走着,赏过山再赏水,连着卵石道的是一条不宽的木桥行于清澈池水上,其实说池也不太妥当,这分明已是一片湖,锦袍人凭栏低头望,湖中自己的倒影随水波荡漾着,一条条寓意祥瑞的锦鲤窜来窜去,时不时跃出水面再复落下。
一只似女子般纤细的手伸出栏外,手指细细搓揉,把刚才在书房里取的鱼食一点点洒进湖中,顿时不知多少锦鲤簇簇拥拥如泉涌来,挤在一堆,争抢起今日的第一餐。
“二十年了,你终究要死。”锦袍人看着鱼群涌动,低声说道。
锦袍人静静凝视粼粼水面,天色却突然变暗了些,他抬头望向天空,朵朵乌黑的云团正飘过来,同时似有点点雨滴落下,他捏了下拳头,直腰再行,步速不急不缓,踏过横跨整片清湖的木桥,穿过错综的亭阁廊道,最终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殿中。
四根凤舞鎏金大柱撑起了大殿的四角,头顶横梁交错如穹顶笼罩,锦袍人踏上金红色的地毯,顺着台阶,一步步走向大殿正中。
“扑通。”他伸手按住微微起伏的胸口。
锦袍人转身,此时在强盛的光线之下,他身上的锦袍清楚显现,那是一袭以金色为底的华丽袍服,一条条红色绣龙跃然于身,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然后,他坐在了那张独属于他的王座之上。
王座棱角飞扬,金光闪耀间,如有一把大剑气势凛然地倒插于背后,剑身两条雕龙嚣张地盘旋而出环绕于两边扶手上,锦袍人坐正了身体,双手紧握龙头,眼中突然探出无比凌厉的光芒!
“来人!”锦袍人一声大喝。
话音刚落,便有穿着蓝色宦官袍服的一人从大殿门口疾步走来,躬身抱拳,道:“回陛下,奴才到。”
“宣风统领入殿。”
“是!”又是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大殿内已无他人。
锦袍人略微倾斜了身子,一手撑着自己的脸颊,头上皇冕珠帘垂下,遮住了半张面孔。
轰隆!一声巨雷鸣响,大殿内随即也闪起白光。
锦袍人一动不动,目光飘向了殿外。
外面的天空愈加灰暗,云阴沉得像要压下来一样。雨似乎越下越大了,却不在繁茂的枝叶上停留,冰冷的雨水顺着叶纹流淌着,最终落在地上,沉没在泥土中。
在无人知晓的这一刻,故事悄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