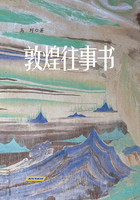“杨凡,我让你去超市买1+1新型环保洗衣粉,你竟然给我买回来的是卫生巾,这事儿用着你了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还有,前几天去市场买生鲜猪肉,你竟然让卖肉的女屠夫暴打一顿,你还是个男人吗?”
“对啦,这化粪池两周前已清理过一回啦,怎么现在又清理?弄得臭气熏天的,难道你是只屎克郎么?”
杨凡不紧不慢做着自己手里的活儿:我怎么就是生不起气来呢,她的声音带着磁性,简直就是打击乐。
“杨凡,你不说话是不是不服气?你是不是个屎克郞?”
“董事长,回您的话,我是屎克郎的孙子,小屎克郎。”
秦柳的火气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枕头上:世界上竟有这么低调的人?或者说,世界上竟有这等一号厚脸?
她疾步上楼,像躲避新冠重症患者一般。
昏睡了两个小时,醒来煮了咖啡,心情才逢松开。这些天来她十分劳累,精神憔悴、火气钻心,回到别墅就想对杨凡发火,因为他是个‘专业’出气筒。
作为秦氏集团的新生代掌门人,一代白衣女神,那在整个碧海市也是高高在上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仅仅在集团里有时就感觉高处不胜寒。
而后天同学聚会,那几个吃撑了的同学竟然约定:参加者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另一半,飞机族和女光棍不能参加!
下周又是爷爷的七十大寿。虽然她跟杨凡有名无实,不过是歪打正着的产物,可爷爷的大寿怎么能少了他这孙女女婿!
这些活动如果带着那货去,岂不是丢人显眼?
杨凡收拾好化粪池,做在楼下洗衣服。她的一些衣服从不用洗衣机,那洗衣机什么衣物都往里扔,她嫌不干净。
一件旗袍空降在他面前的衣盆里,又有两双袜子从楼上丢下来,一只竟搭在了他的天灵盖上,接着就闻到一股酸馊味儿。耐心地把袜子放到另外一个衣盆里,袜子是不能与其它衣物混洗的。
一副黑色罩罩仿佛像带着翅膀,不偏不倚,正落落在他的头上,他从对面残缺的镜面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就像二战时期的飞行员。
苦笑着拿下来时,感觉自己的手指被刺了一下。不好,它上面可能有针儿刺儿什么的,这实在太危险啦。可能是极小的细玻璃茬儿,找不到于是铺在胸前,只要感觉到疼就找到它啦。
秦柳又把被单和浴巾拿出来,本来这被单是用洗衣机的,但是她要惩罚一下他。
上个月,那中学同学朱小一,为了能够接近她,充当送桶装水大叔的儿子来到别墅。杨凡热情地帮着朱小一往二楼上扛桶装水,两人一前一后,不知怎的那朱小一刚踏上最后一级台阶,连人带桶滚下楼梯,摔成了脑震荡。
朱小一本不是什么好角儿,来送水就是只想吃腥的猫,她都想踢烂他的蛋蛋。但是,他如果摔死在她自己的别墅里,且不说他的父亲不是省油的灯,现在的媒体专门涉猎这种花边新闻,那会是种什么样的影响啊。
通过反复细看当时的监控,她发觉竟然是杨凡这个酸坛子使了绊子,而朱小上至今还蒙在鼓里。因为杨凡把朱小一送进医院,而朱小一出了院,还请杨凡喝了酒。
现在,秦柳抱着被单和浴巾正要丢下去,她竟然发现,下面洗衣的杨凡竟然把她的黑色的罩罩,围到他宽大的胸前!
“杨凡!你个变态狂!竟然还想戴上我的那个?实在太打眼、伤神啦!”
“哎呀,我只是仔细看看……”
“然后再戴上是吧?你这是赤裸裸的不要脸!”
“我怎么会戴它,我发现与前天我给你洗的那小里裤也是……”
“对啦,那只蓝色的里裤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呢,原来是你穿上啦!你赶快给我脱下来!”
她气得满脸通红,搬那大盆花没有搬动,接着两眼闪闪地跑进屋里。杨凡知道,她是想用那花盆砸他,而细看那花盆却发现,那只小里裤正挂在花枝上!
怪不得一直没有找到呢,原来竟然是挂在了那里。
秦柳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书,而杨凡已经在马桶上跪了四十分钟啦。
风把带着空气清新剂的香味送进屋里,她的心情好了许多。
因为劳累,自己今天提前两小时下班回到别墅,否则那化粪池早已清洗完毕,怎么能骂他屎克郎呢?真是有些过分啦。这货虽然缺乏男人的阳刚之气,但把家料理得还算井井有条。
她现在之所以原谅他,也因为自己那小里裤被他找到啦。
“杨凡哪,下来做足疗。”
“现在不行,我再跪一会儿,要深刻检讨和反醒。至于足疗,晚上睡前一小时做,效果才好。”
“我让你现在做!”
他十分熟练地跳下马桶。她心里直嘀咕:跑得跟兔子一样快,怎么会被一个大妈暴揍呢。
有时候他的自卑言行让她生气,而有时候又感觉,他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养的宠物。
秦柳热水泡着脚,再加上他的穴位按摩,感觉十分舒适,好像在瞬间充满了电一样。
泡脚用的中草药,是他从山上采来的,比集团治药公司生产的足浴粉好得多,她因此都想升级足浴粉的百年配方啦。
而她理性地思考一下,本是不能对他大呼小叫拿他当出气筒的,相反应该感谢他。连续一周一天一次的足疗,让她感觉身体还可以支撑。倘若是以前,她可能要住院调养啦。
要不,干脆让他参加同学聚会吧,就当是块挡箭牌,挡住那些糟烂的丘比特破箭,让朱小一之流早早断了那些洞房大梦。
“过几天同学聚会,我们起去。这购物卡里有三万块钱,你拿去买身上好的西装,你配棕色的皮鞋洋气一些,也会掩盖你这土包子的形象。”
“行,我定不辱使命。”
秦柳没有再搭理他。她对他十分反感的另一点是,这货大多数时候跟个憨瓜一样,有时却有些张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