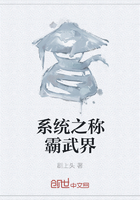酣战结束,袁开把刀收起来,往小院废墟处走了两步,又站住想了想,掉头返回捡起青色妖丹。
这青色妖丹浑圆而精致,如碧玉一般,入手沉绽绽的,光滑而温润,不沾一点尘土。
袁开心道“好宝贝,可不能让暴风看见!”拿着妖丹心满意足的把玩了一会,才恋恋不舍的把妖丹塞进了储物袋中,又细心的用衣服把妖丹盖上。
袁开收好战利品,才慢悠悠地走到废墟上开始翻找,边找边喊道:“师侄?暴风师侄?你还活着吗?赶紧答应一声,师叔甚是担心你。”虽然袁开嘴上说的是关心的话,但细听之下,语气却好似有那么一丝幸灾乐祸。
“……”
“暴风师侄,你不是真的死了吧?”
“……”
“我那苦命的师侄哦,年纪轻轻就已英年早逝,痛死我啦!”
“……”
没听到暴风答话,袁开也不着急,自顾自在这“猫哭耗子”,语气悲痛欲绝,面上却见不到丁点的哀伤急迫,在房屋废墟之中慢慢翻找。若非担心做的太过,袁开恐怕要在这废墟上载歌载舞了。
袁开不紧不慢的翻找了好一会儿,才在废墟深处找到暴风的“尸体”,单手拉着托到空地上。
只见暴风全身被尘土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直如泥捏的塑像般一动不动;再看头上,斗笠已经破的不成样子,皱皱巴巴套在脑袋上;大圆脸上一窃不通,只能看出个轮廓,却找不到眼窝和鼻孔;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达到了连最穷的乞丐都会嫌弃那种破烂程度;脚上鞋子早已不翼而飞,脚指甲断了好几根,其中还有一根藕断丝连在脚趾上,弯出美妙的弧度,挺翘而傲娇,遗世而独立!
看着暴风的样子,袁开表情怪异,眼睛眨啊眨的,小脸红朴朴的,鼻翼晗动,老牛一样直打响鼻,只怕一个不慎,便会大笑出声。
袁开憋的实在辛苦,哆哆嗦嗦的转身,咧着大嘴在废墟里找到块破布,又返回暴风身边,耐心而又细致的擦拭暴风身上的土层。
直擦了好半天,期间又换了好几块破布,才使暴风恢复了一些本来面目,担心暴风窒息,袁开又好心的用草茎给暴风通了通熊鼻,这才满意的坐在暴风旁边休息。
暴风全程闭着眼,一动不动,好像真的死了。
袁开等了好半天,见暴风毫无动静,又跪坐在暴风身边,低头看着暴风的大圆脸,貌似关心道:“师侄醒醒,千万不要睡过去,否则就真的死啦!”
暴风猛然瞪圆眼睛,怒喝道:“你死我都不会死!枉我昨夜还想着要好好辅佐于你,如今看来,你不配!”
暴风越说越来气,忍无可忍,握爪成拳,拳出如风,结结实实的打在袁开眼眶上,把袁开打的又坐到地上。
袁开恍如不觉,瞪着一只熊猫眼,故作诧异道:“你没事了?太好啦!你都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哦,我知道了,那彩衣下的根本不是毒,你又皮糙肉厚,所以一碰到新鲜空气你就恢复过来了!真好!真的!”
暴风小表情都狰狞了,一字一字道:“请你关心我时不要把嘴咧那么大好不好?”余怒沸腾,脏了吧唧的鼻子喷出白色雷电,跳起来开始对袁开拳打脚踢。
袁开虽然自知理亏,但让他老老实实挨打却是绝对不可能的,奋起余力,与暴风战在一处。
二小边打边唇枪舌箭。
暴风:“嗯!让你踢我踢的那么用力!”
袁开:“我是怕力气小踢不到床底下!”
暴风:“嗯!你咋不再加把力把我踢出房子?”
袁开:“我怕力气太大把你踢死!”
暴风:“你就是故意的,接我一拳!”
袁开:“我真不是故意的,接我一脚!”
……
正应了“哀兵必胜”这句话,暴风连番受虐,本来就满肚子怨气,等了好半天,袁开才把它从土里刨出来,虽说了一些关心的话,可任谁都能听出来袁开话语里的兴奋,再加上袁开咧着个大嘴,暴风心中的凄苦实非言语可以描述,只得化悲痛为力量,朝着袁开泄愤,生猛无比。
袁开本来与暴风的战斗力不相上下,但毕竟有伤在身,只招架了十几招,便伤势复发,弯腰吐血。
暴风眼见袁开吐血,只得悻悻的收回握紧的拳头,冷哼一声,道:“若不是看你有伤在身,我定要把你脑袋打成两半!”见袁开还在吐血,冷冷道:“别撑着啦,赶紧坐那调息吧,装可怜给谁看?”
袁开抹了把嘴角的鲜血,抬头看着暴风故作冰冷的脸,竟然感觉有些感动和愧疚,又赶忙咬了咬牙头,暗暗提醒自己:暴风这个王八蛋阴险狡诈耍贱卖萌样样精通,我可别一时感动,把妖丹的事说出去,那样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啦!
袁开调息了一个时辰才稳住伤势。二小一商量,今天与彩衣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莫不如趁着彩衣也有伤在身,合力结果了她才好。
计议已定,袁开又犯难了,道:“彩衣小娘皮跑的太快了,现在都过了一个多时辰,咱俩上哪去找她?”
暴风高昂大圆脑袋,傲然道:“无妨,现在地上还有彩衣的血迹,她被打出了内伤,一时之间定然难以痊愈,我闻着味就能找到她!”
袁开大喜道:“我只听说狗鼻子最灵,没想到暴风你也不惶多让!”
暴风:“……”
二小横眉立目,杀气腾腾,由暴风带路,循着彩衣留下的气味全速追杀,誓要辣手摧花。
……
虫尾山脉距离小院百里处,一条小溪流水潺潺,溪旁鸟语花香,微风轻拂,宁静而和谐。
溪旁,一男一女席地而坐,正在吃着干饼,间或用手捧起清澈的溪水润喉。
只见这男的是个半大和尚,看来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头顶锃亮,上面整整齐齐点着六个香疤,面如冠玉、墨眉如剑、目若朗星、鼻如悬胆、唇若涂朱,身穿一身净白僧袍,脚蹬芒鞋,静如渊、美如画,好一个风神俊郎的美貌和尚。这正是浑如极乐活罗汉,胜似菩提无诈谬!
而这女子正值桃李,眉目如画,天生带三分媚态,语声旖旎,自有妙音于其中,虽身穿一身村妇衣裳,却难掩美色,不是彩衣又是哪个?
只听彩衣娇声道:“奴家遇仇家追杀、身受重伤之际,幸得小长老相救才保住性命,奴只愿给小长老做牛做马,以报小长老大恩之万一!”
和尚被彩衣一番言语说的脸色涨红,连忙摆手,一不留神,手上没抓住,咬了一半的干饼被甩入了溪水中,顺着溪水转眼漂远,白白便宜了水中鱼虾。
和尚想要去捡,又觉颇不礼貌,只得失意的叹了口气,不敢看彩衣的眼睛,讷讷道:“女施主不必多礼,出家人慈悲为怀,佛教导我们要普渡众生,做善事要做成,事如春梦无痕,才是功德无量,若是要回报,功德便会少了。”
彩衣见和尚正经,心痒难耐,又以袖掩面,哽咽道:“小长老慈悲为怀,奴家甚是佩服,只是你护的了奴一时,却护不了奴一世啊!等仇家找过来,奴家难免还是要死于非命,正所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还请让奴跟在小长老身边以保性命可好?”
彩衣字里行间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跟在这半大和尚身边,若是一般男性,早受不了如此美女软语相求,大拍胸脯保证“照顾美女一生、用生命去守护”云云,直恨不得马上入洞房成就好事方才满意了。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和尚显然并非凡夫俗子可比,脑袋摇的拨浪鼓一般,急道:“小僧游历天下修功德,怎好带着一位女子同行,况且小僧身无分文,全靠化缘度日,你与我同行必会受尽苦楚。还请施主休要再提此事!”
衣袖下,彩衣嘴角微翘,眼含笑意,口中却还哭诉道:“小长老有所不知,我那两个仇家各个穷凶极恶、阴险狡诈,兼且好色成***家若是落到他们手上,真个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奴家实在是怕的要命,小长老莫非要见死不救吗!”
和尚听彩衣说的凄惨,心生恻隐,想了想,正色道:“施主但请放心,你也说了‘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小僧一会儿就带你去找你那两个仇家,晓之以礼,动之以情,定要他们放弃恶念。”
彩衣被和尚一番义正言辞弄的哭笑不得,心道:这是哪里来的傻和尚?看他长的俊俏绝伦,怎会有如此天真的想法,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到现在的!看他人俊心又善的面上,我彩衣就破例不害他,逗他玩玩算啦!
彩衣还在胡思乱想的功夫,就听溪对岸不远处有人说话了。
“哟呵,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不到两个时辰,咱们又见面了,彩衣姐别来无恙!”
“嗯!小师叔,跟她废什么话?咱俩一拥而上,赶紧结果了她得啦!”
彩衣吓得浑身一颤,猛然抬头看去,失声道:“天弃黑蛋,是你们两个?”
可不正是袁开(天弃)和暴风(黑蛋)一人一熊么?
暴风恶形恶相地大笑道:“哇哈哈哈,还天弃黑蛋呢!不怕告诉你,我名暴风,旁边这位是我小师叔袁开,等你到了阴曹地府,别恨错了人!”
说罢,袁开与暴风一前一后,纵身跳过小溪,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对彩衣大打出手,那般形态,直如恶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