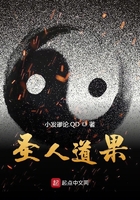见虞权在叹气,虞彤走向榻边,问:“阿弟可知今-天什么日子?”
“啊?”虞权将头扭到里面,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我如何晓得?”
“今-日是祭祖之日。世父、叔父都来了,阿弟还愁出不去?”虞权边说边拉虞权,轻声安慰着。
“祭祖?对了,那阿兄自然也来了……”虞权猛地起身,自语着。
看着虞彤认同的表情,虞权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好阿姊,我们这就去……”
说完,虞权就拉着虞彤,飞快地跑向祠堂。
祠堂中,虞潭正同虞亶(dǎn)、虞察两个兄弟谈着事情。
虞权迈步走进去,拱手唱喏道:“愚侄见过尊世父、贤叔父。祝尊世父锦绣前程,贤叔父鹏程万-里!”
一个龙眉凤目,髭(zī)须掩口的男人,稳步走到虞权面前,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嘴里还喊着,“侄儿几日不见,都长这么大了啊!不错,不错!”
虞权刚看到的时候,只觉得这人像张飞。这人便是虞权的叔父虞察,常年从军,孔武有力,力能扛鼎。
虞权经受不住,快要摔倒的时候,虞察猛地攥住虞权的胳膊,怒目圆睁地呵斥:“侄儿身体如此孱弱,将来如何上阵杀敌?又如何光耀门楣?要是喜儿、预儿也这般柔弱,吾定会水鞭伺候的!”
“叔父教训的是,愚侄知错了,”虞权擦擦头上的冷汗,战栗地回答,“愚侄今后定会多加锻炼的,定会的。”
这时虞权的世父虞亶哈哈大笑,走过来踢了一下虞权的屁-股,说:“騑儿和二侄在外面。赶快滚吧,阿奴。”
虞权迅速退出祠堂,长舒一口气。看见虞騑(fēi)、虞喜、虞茂三位兄长,便快步走过去。虞喜先看到虞权,笑着走过来:“阿弟,近来可好?”
“好什么好,”虞权摇摇头,叹息道,“我快愁死了,还等三位阿兄救救我呢……”
虞騑感到疑惑,问:“阿弟有何难事?不妨说来听听,也好待我们……”
“就等阿兄这句话了,”虞权没等虞騑说完,欣喜若狂地说,“事情是这样的……”
虞权添油加醋地将事情描述了一遍,又表达出了自己非出去不可的意愿。听完后的三位兄长面面相觑,虞预先开口了,“这能行吗?阿弟……”虞权刚要开口,见随任管家虞康和书童虞舒从旁边走过,会心一笑,又生一计……
正厅中,大母巩氏盘腿坐着,也不去理虞权,只是自顾自地吃着。
“大母!”虞权上前跪下,恭敬地问候,“近日可安好?孙儿甚是挂念。”
“起来吧,郎君劳心了。”巩氏冷冷地回了一句。
见大母还没消气,虞彤便将虞喜送来的青釉茶盏递给大母。“大母,快看。这个茶盏,直口微敛,深腹斜弧,平底饼足。圆形敞口托盘,托圈壁直,用来放置杯盏也挺好的。”
巩氏拿起茶盏,上下打量着,嘴里还念念有词:“通体青釉,内外划有勾线莲瓣纹,纹饰清晰自然,造型朴实雅致,我倒挺喜欢的。”
刚说着,便见管家虞康端了一大碗参汤,啰嗦着:“郎君晓得郎主身体虚弱,便日日唠叨小人去寻这上等得仙参。费尽千辛万苦,嘿,还真让小人寻到了。郎主,您快尝尝,鲜的很。”
巩氏让管家放下,问道:“如何寻到的?我倒想听听。”
虞权刚开口,虞騑便打断他,说:“叔祖母有所不知。侄孙我上月里刚到京师,便收到阿弟的来信,托我买棵上等的参。侄孙正发愁去哪里寻呢,正巧碰到一个名叫石勒的人参小贩,本是上党人。一番打听之后侄孙明白了,他将野生人参移植到自家菜园栽培。”
“那这棵不是野生的了?”巩氏冷冷地问。
“那哪能呢,”虞騑继续说下去,“为了治好叔祖母,也为了不辜负阿弟的重托,侄孙便反反复复地同那贩子周旋。最终在阿弟的孝心和侄孙的诚意下,那贩子终于将珍藏多年的野参卖给了我。听他说此参原产自西域,有起死回生之效。叔祖母,您快尝尝。”
一番声情并茂的陈述下,并没有打动巩氏。巩氏怀疑地问:“上个月?侄孙确定吗?”
虞騑愣了一秒,还是肯定地回答,“没错,叔祖母。就是上月里,侄孙去京师的时候收到阿弟的信的。”
虞权突然明白过来,只是还没来得及解释,就听到大母冷冷地说,“上月里权儿还在卧榻不起,怎会给你写信?”
众人一惊,全都愣在了原地。千算万算没算到这点,完了,这次一出完美的计划失败了。正在这时,在里屋啃胡饼的虞楚进来了。看见桌子上有汤,就直接端起来几口喝完了,最-后不忘记打个饱嗝。
虞权愤怒地说:“三弟,你在干什么?这是我给大母熬的!”
“那有什么的,”虞楚用小手指剔了剔牙,满不在意地说,“阿兄,我跟你可是亲生兄弟啊!而且大母也不会介意的,对吧?”
虞楚看向大母,巩氏哈哈大笑,“不介意,不介意。我怎么会介意楚儿喝我一碗汤呢……”
见大母站在自己这边,虞楚挑衅地看向虞权,“怎样?阿兄,我没说错吧?”
“你,”虞权紧紧攥着拳头,眼中充满了怒火,道,“欺人太甚!看拳!”
说时迟那时快,虞权一个拳头打在了虞楚的眼睛上,给他疼得直哎哟。
大母见状将虞楚护在怀里,质问道:“你要做什么?楚儿可是你亲生兄弟……”
虞騑和虞喜死死拉住虞权,不让他再打虞楚。一直站在旁边的虞茂,赶忙打圆场,说,“伯祖母,消消气,阿弟他太冲动了……”
“哼!谅他也不敢动手,”巩氏叹了口气说,“权儿,我晓得你是一片孝心,喝了就喝了吧。我也没有怪过你。”
旁边蜷着腿的虞彤看不下去了,嘟着粉-嫩的小嘴,不满地说:“大母就知道偏心……”
这时候的人跪坐的方式不固定,也有蜷着腿的。也是社会风气导致的,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可以的。在这个比较开明的家里,虞权还是比较幸福的。
“吧嗒”一声,巩氏敲了虞彤脑袋一下,笑着问:“彤儿,可曾记得几年前你跟仡儿争吃得?那时大母向着谁了?”
“我……我记得,”虞彤摸了摸脑袋,嘟囔着回答,“大母向着彤儿了,那次阿弟被打的很惨。”
“那就好。老妪我几时真偏心过?只不过是你们有输有赢罢了。”巩氏长叹一声。
虞权这时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杯,笑道:“大母,快看!”
“那是什么?”
虞权将怀中的琉璃杯递与大母,解释说:“孙儿从西域胡商那里得了一件椭圆形纹琉璃杯。此杯呈淡黄绿色的透明状,口微侈,凹圜底,器体自颈部以下全部抛光,内壁光洁……”
“有什么说法吗?”大母问。
“‘杯’与‘辈’的音相近,送大母杯子,代表了孙儿想跟大母永远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就属你最贫嘴,”巩氏听的也笑了,忙将虞权拉着坐下,说,“你们都快坐下,饭都凉了。快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