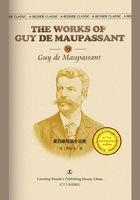第十六章 (1)
在被他当作城堡的客栈里唐吉诃德有何遭遇
一见唐吉诃德安安静静横躺在驴背上,店主便问桑丘那人得了什么病。桑丘说他主人什么病也没得,只是从石上一直栽下去,伤了点肋骨。店主有个老婆,同一般类型的家庭主妇大不相同,为人宽厚,关心旁人疾苦。于是,她忙着去医治唐吉诃德,她还把长相漂亮的女儿喊来当她的助手。店里还有个女佣人,是个住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威尔士人,宽脸盘,平脑勺,塌鼻子,邋里邋遢。她一只眼瞎了,另一眼也快不中用了。不过,她的体态也足以弥补其它缺陷了。从头到脚,她还不足三英尺高,她的肩膀就像灌过铅似的,显得很沉,再加上肩上肉很多,使她只好眼睛总盯着地上。这么漂亮新颖的一位姑娘也去给老板娘她们帮忙。
这位女佣同老板的女儿一起替骑士铺了床。这床破破烂烂的。床就安在阁楼上,这阁楼多年用来堆放切过的草料,就是现在还有堆过草料的痕迹。阁楼顶离唐吉诃德的床铺较远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一个骡夫。这骡夫的床上虽然只有骡鞍和骡披盖,但比唐吉诃德的床铺好多了。唐吉诃德的床铺只是用四块粗粗凿成的木板和两条不平的阁凳凑合起来,床上铺着毛屑垫子,垫子薄得如床单,这里那里都有疙瘩,要不是从许许多多的窟窿眼里露出些羊毛,可能还会以为里面填的是石头呢。剩下来的便是一条床单和一条被单了。床单与其说是用亚麻布做的,还不如说是用皮革做的;被单烂兮兮的,一丝一缕都能数清,要真去数,保证一根也不会数漏。
骑士鞍马劳顿的身躯就躺在这张讨厌的床上。此刻,老板娘和她的女儿正给他浑身上下涂药膏、贴膏药,而那个名叫玛丽托内斯的阿斯图里亚斯女佣则举着蜡烛在旁照明。老板娘见唐吉诃德浑身都是青一道紫一道,心里觉得奇怪,便一面涂药一面说:
“我看呀,这些条条块块看来更像挨了打,不像是摔的。”
桑丘说:“不是打的,太太,我向您保证。我知道,那岩石上这里尖,那里突,我主人就给这些东西弄成这个样子了。”桑丘又接着说:“顺便说一句,请您将那些软布呀、油膏呀留一点,也给我一些。真的,我也不知道我的背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想,我也得要用点油膏。”
“怎么?我猜想,你也摔交了。”老板娘说。
桑丘说:“没有的事。不过,我看到主人从岩石上摔下去,心里一怕,身上也就痛起来了,就像给棒打了一般。”
店老板的女儿说:“你说的真没错。有好几次,我梦见自己从塔顶上摔下来,也还没碰到地面,醒来时,发觉自己浑身不舒服,到处痛,就像真摔过一样。”
桑丘说:“我的情况正是这样,太太。只有运气差了才会这样,才会感到自己差不多就像我的主人唐吉诃德那样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不过,我当时没做梦,就像现在一样,清醒得很。”
阿斯图里亚斯女佣玛丽托内斯问:“那位绅士叫什么名字?”
“他叫唐吉诃德?台?曼查,”桑丘答道,“他是个游侠骑士,是自从有太阳以来最出色、最勇敢的骑士之一。”
“游侠骑士,”那个威尔士女佣喊道,“请告诉我什么叫游侠骑士?”
桑丘说:“嗨嗬!怎么,连这都不懂呀?游侠骑士这玩意用两个词便可给你讲解得一清二白。一是‘棒打’,二是‘皇帝’。今天是世上最倒霉的人;明天他就会有两三个可以赏给侍从的王国。”
“那么,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老板娘说,“您是这个大人物的侍从,为什么连最起码的伯爵爵位都没捞上呀?”
“不急不慌走得远,”桑丘答道,“嗨,我们出来才一个月,还没碰到一次名符其实的冒险。还有,我主人唐吉诃德要是这次能安然无事,恢复健康,而我又不残不跛,我肯定能有份儿,把西班牙的最好头衔给我,我还不接受呢。”
这边唐吉诃德一直在认真听着他们的谈话,这下,他硬撑着支起身子,很有礼貌地抓着老板娘的手说:
“相信我,美丽的夫人。您能有机会在您的城堡里款待我的人,这是件值得很好珍重的幸事。自称自赞不符合有头有面的人的身份,因此,我不想为自己说点什么。我的侍从会告诉您我是何等人物的。我只想添一句:在我的记忆宝库里,我将永远记住您的好心,而且要寻找各种机会来证实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我现在已是爱情的忠实奴隶,完全被我那位倨傲的美人的妩媚迷住了,她独自占有了我那些更温柔的想法。我真希望上帝不是这样安排我的命运,不然的话,我会自豪地把我的自由奉献给这位美丽的姑娘的。”
店老板、她的女儿和好心的玛丽托内斯听着这些浮夸的话,感到莫名其妙,你瞪着我看,我瞪着你看,就如听到的是希腊语一般,谁也弄不清骑士的意思。不过,她们相信,这些无非是些恭维奉承的话,也就钦佩他,把他看成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她们便用客栈里的套语向他答谢了一番,留下他一个人去休息去了。只有阿斯杜利亚女佣玛丽托内斯留了下来替桑丘擦伤,他像他的主人一样,也需要她的照料。
再说骡夫和玛丽托内斯巳约定当晚一起欢聚,她答应他,一等客栈里所有的人都上床睡觉了,她就一定投入他的怀抱,为他效劳。据说,这位脾气好的女佣只要答应了人家的此类事情,尽管这种答应是在深山老林,无人作证,她还是要信守诺言,践约前往。虽然降贵纡尊,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小客栈里侍候,但她常说,只有十字架和贫穷才能让她在这客栈里受委屈,因此,她崇尚礼节,一诺千金。
在这间蹩脚的住房里,唐吉诃德那张又硬、又狭、又陋、又糟的床是四张睡床中的第一张。紧挨着他的床的是桑丘的窝,床上除了床垫和床罩外什么也没有,那床罩不像破布,倒像一块薄薄的帆布。再过去就是骡夫的床铺了,正如上文说过,是用他喂养的十二匹骡子中两头最好的骡子的鞍和披盖拼凑成的。他那十二匹骡子匹匹都膘肥体壮。这部传记的摩尔人作者同他熟,在传记里特别提到他,说他在阿瑞巴洛的骡夫中是个首富;有的人还说,作者跟这骡夫很可能还有点亲戚关系。不管怎么说吧,作者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是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对那些不足道的琐事也要详细交代,这倒是很值得称道的态度,是其他历史学家应该效法的榜样,别的一些历史学家,叙事过于简洁,他们要么出于疏忽,要么出于恶意,要么出于无知,把事情的最重要部分淹没在墨水瓶底,令人们读来感到索然无味。我们真该为《塔希朗读?台?黎加蒙特》的那位精细的作者,还有撰写佗米阿斯伯爵的生平业绩的另一位孜孜不倦的哲人千遍万遍地祝福,因为就连最细微、最不重要的情况他们都要用一种特有的精确去叙述。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