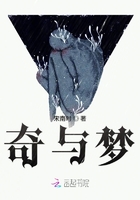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都说有些人用童年治愈了一生,有些人却终其一生都在治愈童年。那我一定是后者。
我出生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小村子,96年炎热的那个夏天。到如今我的记忆里,好像只有家门前的那棵梧桐树,摇摇晃晃的陪了我十几年。典型的留守儿童。奶奶很小的时候便没有了妈妈,家里的哥哥把她拉扯成家,年纪轻轻便得了关节炎,我几乎在每一天夜里都能听见她因为疼痛而发出的呻吟。那些声音在我每个密密麻麻的夜里让我有些喘不过气。至于爷爷,他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农忙的季节里,小小的我清晰的记得他每每天黑回到家里坐在凉椅上的疲惫。都说穷人家的小孩早当家,于是乎家务活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都会了。踩着木板凳,滚烫的猪食,还有比我高的黄牛,包括那门口的梧桐树,是我幼年记忆中的所有。
最期盼的时刻是家里来客人,特别是重要的客人,好像比过年还会期盼,很简单的理由,因为会有平时吃不到的好菜,青椒炒的腊肉,煮熟晾过的猪耳朵。是我记忆里最美味的。每当吃饭前,奶奶会说,让客人先吃,小孩子不要在桌子上吃饭。几乎每家都有这样的规矩,家里有客人,小孩子不要在桌子上吃饭。每次爷爷都会偷偷夹肉给我,这好像是最温暖的事。好多年之前我并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给小孩子那么多的规矩。在慢慢长大的日子里,我知道是因为家里穷。
那些旧的时光,脑海里还有冬天里冻开裂的手。水稻收成之后,天气就凉了,不像夏天那样有聒噪的蝉鸣声和夜里田埂上不停的青蛙声。只剩下白发发的树,还有水管子里冻住的水。爷爷会早早的起床,去挑一整天需要的水。冬天里都是离不开火的,是的,柴火。奶奶说挑小的萝卜在火灰里面烧一烧,在长冻疮的脚上滚一滚,慢慢会好的,所以我用焦焦的萝卜在脚上滚了好几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