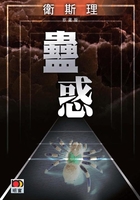每天晚上,睡觉前,锦一取下眼镜时,世界就模糊一片。
一小时前,停车场上有一堆垃圾,锦一绕过它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被丢弃的布娃娃。有些脏,那是一个手工做的中国男孩子,头发很少,或者很多,但被撕掉了。锦一下车去捡那个布娃,才发现,刚才只是幻象,那根柱子边上只有一个矿泉水瓶子,没有了盖,那么突兀,像一个孤单的发言者。
锦一最近老是这样把事情弄模糊。
晚饭后,他刚刚在卡车画廊的大工作室里随首画了一个布娃,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画那个脏兮兮的布娃,表情有些孤单。
画完以后就离开了,大概是这些天工作有些沉闷。卫星频道新换了一个领导,部队转业的,为了体现出他的特有的性格,竟然要求大家坐班。
有时候,一点细小的变化,会导致一团生活成为麻绳。
隔避国际阻的专题女记者曹明明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到单位办理离职手续。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因为坐班。锦一刚到办公室就听说了她的情况,大家伙一人一句,像很多个人合作写一个电视剧,台词有的重复,有的格外离谱。
大致的情形如下:曹明明刚修完产假上班不久,以前上班管理不严格,她都是做好早餐后才上班的。可是,台长要求坐班,来不及给家里人做早餐。曹明明的爱人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整天晚睡晚起,婆婆去世得早,所以,公公一直跟着他们一起住。结果,公公第一天买早餐就忘记带钥匙了,大冬天在外面转悠了一上午。因为曹明明的老公睡觉睡得死。接下来开始相互埋怨,老公公听不惯曹明明和他儿子一句一句对骂,一生气出门去找工作了,竟然找了一个保安公司的工作,保姆因为家里有事辞职,刚满一岁的儿子忽然没有人照顾了。然而曹明明依旧要按时早起挤公交车。周末的时候,终于有了时间,曹明明和丈夫抓住了周六周日集中地吵架起来,竟然还翻出了她老公的一次身体出轨事件。曹明明整理地下室的时候,发现老公很早以前找不到的一个公文包,里面竟然有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里面夹了几张合影,在北京长城上,在圆明圆,在故宫,姿势和表情一样,亲密得厉害。曹明明一问,她老公就承认了。吵架的时候,曹明明还说起恋爱时的事情,有一支圆珠笔,是她老公送给她的,她一直不舍得用,一直不舍得用。她老公不理她。曹明明知道,从一开始,都只是她喜欢她老公,他对她并不在意。那天,不知道是谁先说了一句离婚,然后,曹明明就大哭起来。孩子也哭了。曹明明跑到卧室才发现,孩子光着身子在木地板上,她们家根本没有用暖气。那么凉,孩子的身体都冻成冰块了。
插话的人很多,分别介绍了曹明明的老公,长得帅气,就是有些低,戴个眼镜,一说一笑,是个和气的人。还有人说曹明明上大学的时候就和老师谈恋爱,最后打了胎,差一点怀不上孩子,也不知道后来是如何治疗好的。
和曹明明关系一直比较好的是我们部门的会计,因为她同时兼做卫星频道的会计。她补充说明曹明明的悲剧与她活得没有自己有关,整天也不知道美容,不注意修饰,才三十岁多一点就暮气沉沉的,胸部那么大连个好一点的胸罩都不舍得买,有一次,我的一个胸罩想扔掉,她知道我那个胸罩的价格,硬是捡了去,真不知道,她收入这么高,都做什么用了。
结局是离婚。孩子归曹明明。
锦一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报纸上的内容没有看进去,只记得有一个诗人自杀了,原因是没有钱。
当他听到曹明明故事的结局时,内心里的一把钥匙突然掉在地上了,他赶快往地下看了一眼,是的,冬天,办公室的地板有些凉。他看到一双高跟鞋向他走来,原来是收发室的小金,给他一个特快专递。
按时坐班以后,对于锦一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不用坐班,他不是记者,也不是编辑,最重要的,他的编制是聘用的,不是台里的正式员工。所以,他依然自由。
唯一遗憾的是,每天上班时坐电梯总是一个人。他固定每天上午十点钟赶到办公室,差不多这个时间,他会和法制频道的一个美女播音员遇到一起。几乎成了惯例。锦一甚至喜欢上了她衣服上的香水味道。以致于有一阵子,他在其他场合闻到这个气味的香水也会想到那个女播音员,那个女播音员是警察学校的毕业生。
他们在电梯里认识,也知道对方在哪一层楼,哪个办公室,却并不问彼此的名字。锦一想了一下,他们一年里碰面的次数有三百次以上,但一句话也没有说话,每一次都彼此点一下头,那么自然。
锦一的特快专递是一个书画邀请展的门票。锦一随手就扔进了垃圾篓里。
然后去吃午餐。自从来了一个新领导,餐厅里的午餐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因为新来的频道总监也在餐厅里吃。锦一并没有在意,而是圆桌子上的一个摄影记者问他,说老兄,你好像喜欢吃素啊。锦一不认识他,以为他和别人说话。没有理会他。
那个人又说,锦一兄弟,你素食主义。锦一才抬起头来,忽然想起他来,叫做来一统,是经济生活频道的摄影记者,很活跃,他们曾经在一起参加过一次台里的联欢会,然后坐在一起。那天仿佛他们谈得很投机,是关于女人的。
锦一和来一统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知道了餐厅的饭菜质量最近有很大提高,鱼肉降价了,鸡肉也降价了,红烧茄子加了肉沫,还有免费的那个四川泡菜特别好吃。
然后就睡午觉,锦一在办公里的角落里睡,另一个女同事趴在桌子上睡。更多的时候,锦一回家睡,下午不去办公室。
锦一下午在家里画画。有时候,他光着身子,画着画着想尿尿了,就直接尿到画架旁边的一个盆子里。
有一天,邵娅领着她的女儿来参观,锦一刚刚尿完。
听到敲门,锦一连忙穿上衣服,结果,他忘记收拾那一个尿盆了。他的尿有些黄,被邵娅的女儿露露发现。那是一个爱打破砂锅的女孩,她问锦一:叔叔,这个盆子里是什么啊?
锦一说,是画画用的。
那个女孩便用手往里面伸。
锦一连忙制止了她。
那个女孩说,为什么不能往里面伸啊。
锦一说,是尿。
邵娅格格地笑,说,我看着也像是尿,你真是个怪人,原来用尿来画画。
锦一本来想仔细解释给邵娅听的,他只是喜欢在夏天里光着身子画画,怕尿意来了影响绘画感觉,便在旁边摆了一个尿盆。但当着露露的面,他的这些话说不出来。
他在那里想着该如何解释这盆尿不是用来画画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他忽然想,如果真的用尿画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在内心里获得了巨大的快感,不小心笑出了声音,而邵娅又在他笑出声音之前说了一句什么暧昧的话,结果一下子就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气氛。
锦一躺在床上想邵娅那天到底说了什么呢。他想到邵娅刚搬进他们小区时的情形。
他想来想去,脑子便开始模糊起来,隐约隐约地想到了邵娅的身体。
是邵娅吗,他忽然又不能确定。他想到露露,一个掉了一颗牙齿而影响说话的小女孩,邵娅的女儿。现在,锦一忽然不能确定邵娅有没有这样一个女儿,那是在小区里遇到的一个孩子,她正在地上画画,两只打架的猴子,一个猴子的脸画得很愤怒。
锦一问她,为什么要画得那么愤怒。
露露说:他饿了,可是,苹果被别人抢了去。
锦一看了看她画的画,问她,苹果呢。
露露歪着头,想了一下,说:苹果被妈妈吃完了。说完露出牙齿。
锦一告诉露露:你画的猴子不一样大。
露露说:我要把我喜欢的猴子画得大一些,我还要给糨画好看的衣服呢,彩色的。我要它拿着如意金箍棒和别的猴子打架,我要它打赢别人。
锦一哈哈地笑,纠正露露,说:猴子发动战争时,不会大猴子欺负小猴子,而是等级分明地战在一起。小猴子和小猴子打,大猴子和大猴子打的。
露露,用手拿着粉笔在那里抹衣服,蓝色外衣上马上有了粉红色的印迹,她反问锦一说:那么,性别呢。猴子打架时候会不会男孩子欺负女孩子啊。
锦一被露露的问题难倒了,想了一下,说:不知道。
锦一的一幅油画没有画完,全是草,绿色的。
露露就笑,说,我想在草地上小便。锦一想了一下说,我给你画一个厕所。
远方的风景?远方的风景是什么呢。露露问。
锦一想到自己原本计划画一头牛的,随口说:你会看到奶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