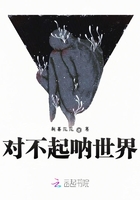在我父亲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她让他皈依了你。我父亲成为教友后,母亲对于之前父亲让她受到的委屈,从未埋怨过。她真是你的忠诚的婢女。凡认识她的人,都因为她的高尚品德而赞扬你、热爱你;他们感受到你在她心中,她的忠贞、善良证明了这一点。她“用忠贞侍奉丈夫,用孝顺侍奉双亲,用诚信治理家政,有贤德的名声”。她教养子女,每当看见他们疏远你,就再进行教育。主啊,至于我们,你的仆人们——由于你的仁慈,我们敢这样说——她在去世前,领受了洗礼的恩泽,我们都已同心同德地生活在你的怀抱里了,她是我们一生的慈母,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她又像我们一生的孝女,服侍我们,照顾我们。
临近她去世前的某一天,——她去世的那天你是清楚的,我们并不知道——你在冥冥之中安排着,让我们母子俩倚在同一个窗口,放眼于室外的花园,这时我们在远离尘嚣的梯伯河口作短暂居住;长途跋涉后,稍微休息一下,即将扬帆远航。我们两人非常悠闲地交谈着,“抛开了过去种种,向往着以后的种种”,在你——真理本体的照耀下,我们探讨圣贤们所享受的“眼所未见,耳所未听,心所未测”的永生生命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贪婪地张开了心灵之口对着“源于天父的生命之泉”的天上仙汁,渴望尽情畅饮,对于这个玄妙深奥的问题能捉摸到一些踪迹。
我们的谈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论我们肉体感官的享受如何丰美,不论所放射的光芒如何灿烂,如果跟那种生活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神游物外,凌驾日月星辰照彻天地的苍穹,徐徐上升,怀着更热烈的感情,向往“常在本体”。我们在心中铭证,在口中吟诵,目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持续升腾,达于灵境,又飞越而到达无边无际的“膏壤”;在那里,你用真理的食粮永远“养育着以色列”,在那里,生命融合于万物之源,融合于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真智。真智既然是永恒,那么它的本体自然是无始无终,永恒不变的;如果有过去和未来,就不是永恒的。我们这样谈论着,向往着,心旷神怡,刹那间领悟到了真智,我们相互叹息,留下了“圣神的鲜果”,回到人世语言有始有终的声浪之中。但哪一种言语能和你永恒不灭、无新无旧、更新一切的“道”、我们的主相提并论呢?
我们说:“倘若在一个人身上,血肉的困扰,地、水、气、天的形象都归于沉寂,并且自己的心灵也默然休息,超然忘我,所有梦幻,所有想象,所有言语,所有动作,以及所有瞬息生灭的都已静止——这一切必定会对倾听的人说:“我们不是自造的,是永恒常在者创造了我们”,说完也请它们安静下来,只倾听创造者——假如天主直接说话,不借助外物而自己说话,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声音不是来自尘世的舌音,不通过天使的传播,不借助云中雷霆的震响,也不用比喻隐语来让人猜测,而是直接谛听他的话语;我们本是通过万物来爱他,现在离开万物而听他自身,正像我们现在的勃发,感觉转瞬间就接触到超越万物、永恒常存的智慧一样;假如这种境界持续着,消除了其他不同性质的妙悟,仅凭这种真觉而控制并摄取了谛听的人,让他沉浸在内心的欢乐之中;假如永生与我们叹息向往的相一致,那刹那间的真觉,岂不就是所谓“进入主的欢乐境界”了吗?但什么时候能实现呢?是否在“我们全要复活,但不是全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谈话的内容是这样,虽然是用另一种方式、另一种言词。主啊,你知道在我们母子俩谈到世间一切俗世的快乐不值一顾时,她对我说:“我儿,对我来说,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不知道还有何事可作,为什么还留在此世;我的愿望都已满足。过去我之所以要暂留此世,不过是盼你在我去世之前成为一名公教徒。而天主的恩惠超越了我本来的愿望,让我看到你竟能蔑视人间的幸福,成为天主的仆人。我还需要做什么呢?”
十一
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她的了。大约五天过后,她发烧病倒了。病中,有一天她失去了知觉,分辨不清周围的人。我们赶到后,她立刻清醒过来,看着我和我的弟弟,仿佛要找什么东西似地向我们问道:“我刚才在哪里?”她看到我焦虑的神情,就说:“你们把我葬在这里吧。”我没有出声,极力忍住泪水。我的弟弟认为最好还是回到故乡,不要客死异乡。她听后面露难色,用责备的目光望着他,责怪他作这样的打算,然后又望着我说:“你听,他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又对我们两人说:“随便你们把我葬在哪里,没必要为此费心。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今后不管你们到什么地方,在天主台前要想起我。”她勉强说完了这句话,就默不作声了。她的病势垂危,痛苦也加深了。
无形无象的天主,我欢喜,我感激你!感激你散播在信徒心中的恩惠结出了美妙的果实。我想起母亲自知不久于人世,也曾经十分关心死后安葬之处,她怀着生同心死同穴的心愿,打算同丈夫合葬。——对于神圣的事物,人心真是不容易向往!——使后人羡慕她远航回来后,自己的身躯还能同丈夫的尸骨埋于同一块土地中。
我不知道你是在何时用无限仁慈把这种无聊的心愿从她心中除去,但在明白真相以后,我只有赞叹和欣慰;其实在我们凭窗交谈时,当她说出:“我现在还有什么事可作?”这句话时,已经表明没有死在故乡的愿望了。又听说我们在梯伯河口时,有一天我不在她身边,她怀着慈母般诚挚的心情,和我的几个朋友谈到要轻视俗世而重视死亡,我的朋友们都惊叹这位老太太的德行——这是你赋予她的——因而当问到她是否对死后葬身异乡感到忧虑时,她说:“对于天主自然没有远近之分,不必顾虑世界末日时天主会不知道地方而不来复活我!”
病后第九天,她圣洁的、真诚的灵魂离开了躯体,享年五十六岁,这时我三十三岁。
十二
我合上了她的双眼,无限悲伤涌上心头,化作泪雨;我的泪水在意志的控制下止住了流淌;这样强忍着真是觉得特别难受。在她咽气之时,我的儿子阿得奥达多斯嚎啕大哭,在我们的极力劝阻下才止住了哭声。如果没有他青年的声音、心灵的声音阻止,我幼稚的情感也差点要放声大哭了。但我们觉得对这样的安祥去世,不应悲伤痛哭;人们普遍认为在丧事中必须痛哭,那不过是为悼念死者的不幸,好像死者已完全毁灭。可我母亲的去世并非不幸,而且还有不死的灵魂永在,我们对此坚信不移。
但我为何感到肝肠寸断呢?这是因为突然失去我与母亲之间相亲相爱和煦温暖的生活而带来的伤痛。在病中,她见我小心侍奉,就抚摩着我叫我“乖孩子”,而且动情地说,从没有听我对她说过一句生硬顶撞的话,想到这些,我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天主,创造我们的天主,我的奉养怎能比得上她对我的辛劳养育呢?失去了慈母的怜爱,我的灵魂受到了重创,母子两人原是相依为命,现在竟分离了。
热心的妇女们知道我们办丧事也都来了。按照习俗,有专门擅长此业的人来办理殡仪,我就按例退到别室,朋友们觉得不应该离开我,都来作陪。我与他们谈论丧母的心情,用你真理的慰藉来减轻痛苦;他们都细心听我谈话,但他们并不了解,觉得我并不哀痛;只有你了解我的痛苦,此时我在你的耳边——没有一个人能听到——正在抱怨我的心太软弱,我极力压制着悲痛的激流,想让它平静下来,但起伏的心潮很难控制,虽然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内心却是波涛汹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真会捉弄人,我憎恨它,它让我感到另一种痛苦,此时是双重悲哀在折磨着我。
下葬时,一路往返,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我们按照当地风俗,在入土前,将母亲的遗体停放在墓穴旁边,举行赎罪的祭礼,并向你祈祷,此时,我也没有流泪。但是我却整天悲伤苦闷,我极力祈求你为我疗伤,你却没有应允。我相信仅此一件事,已能让我记住,对于一个已经听惯好话的人,习惯的束缚仍然会起作用。这时我想到沐浴,因为听说“沐浴”一词,希腊语的意思就是解除烦闷。可是天主,我要忏悔,我要面对你的仁慈忏悔:我内心的酸苦并没有因沐浴而减轻一丝一毫。但是当我一觉醒来,就觉得轻松了一大半;我独自躺在床上,默诵你的安布罗西乌斯颠扑不破的诗句:
“天主啊,万物的缔造者,
苍穹的主宰,你给白天
带来灿烂的光辉,给黑夜
带来恬静的眠睡,
让安息恢复疲劳的肢体,
能继续照常的工作。
松弛精神的劳累,
解除郁结的阴霾。”
这时,你的婢女一生对你的虔诚之心和对我的怜爱之情又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旦这一切消失,我忍不住在你面前为她痛哭,也为我自己痛哭。让抑制已久的泪水尽情倾泻吧,让酸楚的心躺在泪水的床上,安息吧,因为那里除了你,别人听不到,不会对我的痛哭妄加揣测。
主啊,我现在用文字向你忏悔。谁愿意读,就请他读下去,随便他怎样批评;为我痛哭、让我重生的我的母亲在我眼中不过是与我的暂别,所以我只流了短暂的眼泪,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罪过的话,请他不要嘲笑,而是在你、基督众弟兄的天父面前,为我的罪恶痛哭,倘若他真的有爱人之心的话。
十三
我这处所谓肉体情感造成的心灵创伤,现在已经康复了。我的天主,现在我的另外一种泪水也为母亲而流,为一切“死于亚当”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而流,这是因忧虑焦急而流下的眼泪。尽管我母亲的肉体存在之时,已生活在你的怀抱之中,并且用信誉和德行显扬你的圣名,但我不敢保证从她受了“洗礼”的再生之日起,从来没有一句话违背过你的告诫。你的圣子,真理本体说过:“谁要说自己的弟兄是疯子,就应受到地狱的惩罚”;如果一个正人君子把你的仁慈抛开来检讨自己的生平,也定会大为寒心!但你对我们的行为并不苛求,所以我们才衷心希望能在你左右得到一个位置。倘若有人想计算自己真正的功绩,那么除了计算你的恩惠外还能计算什么呢?唉!倘若人们能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那么“谁想夸耀,只应夸耀天主!”
为此,“我的光荣,我的生命,我心灵的天主”,我抛开了你赐予她的美德,只为我母亲的罪业恳求你,请你看在高悬在十字架上、“坐在你右边、为我们代求”、治疗我们创伤的良医的份上倾听我的祈祷。我母亲一生宽以待人,经常免去别人的债务;倘若她在受洗获救后的漫长岁月里欠有罪债,请你也宽恕她吧。主啊!求你宽恕,求你宽恕,“求你免去对她的审判”。“让哀怜胜过审判”,你的话真是不假,你曾经许诺以怜悯对待怜悯。“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遇谁,就恩遇谁”,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这样,都是出自你的恩典。
我相信,你已成全了我所愿。但是,主,“请你收纳我心口一致的献礼”。我母亲临终之前,对于死后的哀荣,敷体的香料从未计较过,也不要求建立纪念的墓碑或归葬故乡;对于这些,她只字未提,只是嘱咐我们在天主台前纪念她,她在你台前夜以继日地侍奉着,她要在台上分发神圣的牺牲,因为她知道这牺牲“已经勾销了我们的罪状”,战胜了记述我们的罪恶、挖空心思控告我们的仇敌,对于我们赖以致胜的基督,仇敌就更加无计可施了。为了从敌人手中救赎我们,基督献出了无辜的鲜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谁能偿还?你的婢女用信仰的枷锁把她的灵魂捆在救赎我们的圣迹上,以免有人使她脱离你的保护、有毒蛇猛兽用暴力与阴谋诡计离间你和她;她也不会说自己完美无缺,让狡猾的控告者无从反驳,她将承认自己的罪债,但它们已被我们无法报答的、完美至善而替人还债的恩主所赦免了。
希望我父母在和平之中安息,我母亲从处女到寡居一直有着贞洁的美名,她侍奉丈夫,把“辛勤得来的果实”献给你,使他归向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求你启迪你的仆人们,我的弟兄们,求你启迪你的子女们,我的主人们;我现在用灵魂、用言语、用文字为他们服务;求你启迪所有读这本书的人,让他们在你台前怀着虔诚之心来纪念我的父母,——你的婢女莫尼卡和她的丈夫巴特利西乌斯。你是如何用他们的血肉把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呢?我不知道。我们一起奉你为慈父,我们同是慈母教会内的弟兄,也是同属于你的漫漫旅途中的子民自始至终都念念不忘的永远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同胞。这样,我母亲最后的遗愿,通过许多人的祈祷必定比我一个人的祈祷能更有力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