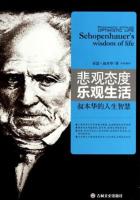假如我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死去,一定让慈母痛不欲生,我不知道这创伤将怎样治疗。她作了这么多的祈祷,她的连续不断的祈祷到哪里去了?不会到别处去,只能到你那里。你,仁慈的天主,难道会蔑视一个贞妇的“忏悔谦虚的心”吗?她乐善好施,顺从并伺候你的圣贤们,她从不停顿地每天上你的祭台前参加献祭,从不停顿地每天早晚两次到你的圣堂中,不是去听无稽之谈,或老太婆们的多嘴多舌,而是听你的教诲,你也倾听她的祈祷。她之所以流泪,不是为了向你索取财物,或人世间无足轻重的东西,而是要挽救自己儿子的生命,她之所以能这样,是出自你的恩惠,你难道会不顾及她的眼泪而袖手旁观吗?主啊,你当然不会的,相反,你在她身旁,满足她的要求,依照你原定的计划而实行。你在梦中给她的回答,上文我曾说到的和没有说到的,她念念不忘。在例行的祈祷中,她奉着你赐予她的信念,坚信你必然不会欺骗她。因为“你的仁慈是永不匮乏的”,你免去了一人的负债后,又对这人作出承诺,仿佛自己欠有债务似的。
你诊治我的疾病,你让你的婢女的儿子恢复了身体的健康,为的是能给他另一种更好、更可依赖的健康。
此时在罗马我仍然和那些骗人的假“圣人”保持着联系:因为我不但跟普通教徒、“听讲者”——我的房东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他家里患病并痊愈——而且还跟他们所谓的“选徒”来往。
那时我依然觉得犯罪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不清楚哪个劣根在我们身上犯罪,于是我竟以置身事外而感到自豪;所以,我干了坏事却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求你拯救我犯罪的灵魂,我习惯于推脱自己的罪责,却归罪于某个与我在一起但并不是我所有的事物。其实这全都是我自己,我的狂妄把自己一分为二,使我与我相互对抗,我不承认自己即是犯罪者,使得这罪行更是无可救药了;我是这样无赖野蛮,宁肯你全能的天主在我身上遭受失败而任我毁灭,也不愿你战胜我而拯救我。
你还没有“为我的嘴设下屏障,为我的唇装设机关,让我的心不倾向于邪恶的言语,让我不与作恶的人臭味相投”,所以我仍然与他们的“选徒”往来,但我已不打算再对这种荒谬的学说继续深造了;在我尚未找到更可信赖的学说之前,我决定暂时保留,但已较为冷漠疏远了。
这时另一种想法已在我心中产生,觉得当时所称的“学院派”哲学家的见识高于这些人,他们主张对一切表示怀疑,认为人不可能真正懂得真理。我觉得他们的学说就是当时一般人所介绍的,其实我还没有抓住他们的真实想法。
我也毫无保留地批评我的房东,我认为他过分相信摩尼教书中的胡言乱语。但我和他们的情谊仍然较之其他不参加摩尼教的人要深得多。我已不像过去那样积极地为该教辩护,可是因为我只和他们熟识——有许多教徒在罗马隐居——我就懒得探寻其他宗教,我也不再希望在你天地主宰、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的教会中获得他们先前使我脱离的真理。我觉得相信你具有人的肉体,相信你和我们一样具有五官四肢,是极为可笑的事情。想到我的天主,我只能想象某种物质——我觉得只要是存在的东西都是这样——这是我之所以坚持我无法避免的过错的主要而且几乎是仅有的原因。
因此我也相信恶的本体是存在的,它是一团可怕的、丑恶的、污浊的东西——摩尼教称之为“地”——亦或是一种飘浮不定的气体,这是他们幻想中在地上爬行的恶神。因为我还有一些宗教感情,我完全相信善神无法创造恶的本体,所以我把这团东西与善对立着;二者都是没有极限的,恶的势力比较小,善的势力比较大;从这个坑害人的理论上,产生了其他所有侮辱神明的荒唐论断。
每次我的思想打算返回到“公教”信仰时,总是觉得阻力重重,因为我理想中的公教信仰,并不是公教的信仰。我觉得设想你天主——我对你诵说你的仁慈的天主——除了与恶神对立的部分是我所认为的有限的之外,其余部分都是无边无际的,比起设想你的各部分都局限在人的形体之中,肯定更符合虔诚的宗教精神。我觉得相信你没有创造恶——因了我的愚昧无知,我心目中的恶是一个实体,甚而是物质的实体,因为我仅会想象精神是一种散布在空间的稀薄物体——比起相信恶的本体来源于你,也要好得多。对于我们的救主,你的“独子”,我觉得他为了挽救我们,从你光辉的巨大体质中分离出来,除了我的凭空设想之外,我对他一点都不相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生命不可能是童女玛利亚生养的,否则肯定和肉体混合杂揉;而依据我的想象,我无法看出如何能够既相互混合而又不遭污染。所以我不愿相信他降生成人,因为我没有办法不相信他也受到过血肉的污染。
现在,凡蒙受你荣光照耀的人看了我的忏悔后,将会善意地、亲昵地取笑我;可是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的。
十一
另外,我认为,摩尼教信徒对你的《圣经》所提出的批评,是不可能驳倒的。但我有时特别向往能和一位精通《圣经》的人讨论每一问题,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位叫埃尔比第乌斯的人曾对摩尼教信徒作过演讲和辩论,我在迦太基时,他的言论已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因为他引用了《圣经》上的几段很难解释的文字。我觉得摩尼教徒的答复是没有任何可信度的。因此他们也不会轻易地公开发表,仅在私下对我们提出。他们说已经不知道《新约》的文字被什么人篡改过,篡改的目的是把犹太人的法律掺进基督教教义,但他们却又拿不出一本未被篡改的本子。而对我来说,也只能想象物质被那些“庞然大物”所掌控,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使我不能呼吸你真理的纯净的空气。
十二
我在罗马开始从事教授雄辩术的工作,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先在家里招收了一些学生,因了他们的宣传,我开始被外界所注意。
在罗马我听说有一种在非洲看不到的情况。别人告诉我非洲青年的那些品质败坏的捣乱行为在这里确实不存在,但“为了不交学费,很多学生会串通好,突然转到另一个教师那里,因为钱财重于信义,他们甚至不惜违背公德”。
我很讨厌他们的这种行为,但不能说是出于一种正义的厌恶,因为我之所以仇恨他们,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损害别人利益的非法行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直接使我的经济遭受损失。
这种人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格,他们“远离你而犯奸淫之罪”,在时间所玩弄的幻影里流连忘返,贪嗜着弄脏他们双手的粪土般的利益,拥抱着这个逝去的世界,却鄙视永恒存在的你,正在召唤并饶恕所有曾被邪恶占据过身体但仍能幡然悔悟的你。如今,我一方面憎恨这种人的无耻堕落,另一方面却爱他们,企图使他们得以纠正,使他们比之于金钱能更爱所研究的学问,爱你、真理的天主。更进一步,爱真正的幸福源泉和纯洁的和平胜过爱学问本身。但那时我仅为我自己打算,不愿意忍耐他们的卑劣行径,而不是替你打算,希望他们改恶从善。
十三
这时米兰派人来到罗马,请罗马市长任命一位雄辩术教授,并授予其公费旅游的权利。我通过那些沉迷于虚幻之中的摩尼教徒——自此以后我将同他们脱离关系,但我们双方都还不知道——试图谋求这个职务。我写了一篇演说稿上交给当时的市长西玛库斯,他感到满意,就派我去了米兰。
到了米兰后,我就去拜访安布罗西乌斯主教,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超凡脱俗的人物,也是一个崇拜你的人。他凭借雄辩有力的言论把你的“麦子的精华”、你的“欢愉之油”和你的“甘甜的酒”散发给你的子民。我不知不觉地受你引导而向他走进近,使我自觉地接受他的引导而归附于你。
这位“天主的人”像慈父一样接纳了我,并以主教的风度迎接我来这里作客。
我开始敬重他,但最初并不把他当成真理的明师——我根本没有指望在你的教会中找到真理——只不过是把他看成一个对我和蔼可亲的人物。我很专心地听他对群众所发表的言论,但并没有抱任何目的,而仿佛是要测验他的口才是否和他的声誉相一致,是过之还是不及;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虽然已经被他的词句吸引,但对内容并没在意,甚至抱有不屑的态度;我欣赏他谈姿的优雅,觉得他比福斯图斯学识渊博,只是在论述的方式上,福斯图斯则更为幽默风趣,更容易打动人。如果只就内容而言,两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一个是沉醉于摩尼教的谬说,一个是把最健全的生命之道传给众生。
救赎还远离着如我这样的罪人,但我却在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向它靠近。
十四
对于他所谈论的内容我没有在意,而是只着眼于他论述的方式,——尽管我没有指望通向你的道路就此畅通无阻,但总是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我所忽视的内容,随着我所喜爱的词句一同渗入我的思想。我无法对二者进行区别和取舍。所以当我心扉豁然开朗接纳他滔滔不绝的词句时,其中所包含的真理也逐渐渗透进去了。
我开始感到他的见解确实有根有据,言之成理;在这之前,我认为公教信仰在摩尼教徒的刁难面前只能哑口无言;这时我认为公教信仰并不是强词夺理地坚持的,尤其是屡屡听了安布罗西乌斯解答《旧约》上的一些疑难文字之后;我感觉我过去是拘泥于字面而走入了死胡同。听了他通过文字意义来解释《旧约》中的许多记载后,我后悔我对基督教义的绝望,后悔我过去相信摩尼教对《旧约》律法先知书的驳议和排斥是无可辩驳的。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认为必须要走通往公教的道路,因为即使公教有博学雄辩之士能详细地、合理地解答疑难问题,我也觉得并不能据此就该排斥摩尼教信徒,双方势均力敌不分上下。总之,在我看来,公教虽不是战败者,但也不是胜利者。
这时我极力思考、寻找足以证明摩尼教错误的有力证据。假如我当时能设想出一种精神体,那么我会马上驳斥摩尼教的穿凿附会之说,把它从我心中驱逐出去;但我无法做到。可是对于感官所能接触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界,通过观察、比较后,我发现许多哲学家的见解更值得信赖。
所以,按照一般人所理解的“学院派”的原则,我怀疑一切,在一切之中游移。我觉得当我无法下论断时,既然看到许多哲学家的见解胜于摩尼教,就不应再在摩尼教中停留,所以我决定脱离摩尼教。对于那些不知道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不相信他们,也没有请他们治疗我灵魂的痼疾。
就这样,我决定仍然在父母所嘱咐的公教会中做一名“望教者”,等待可靠的光辉照耀我,指引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