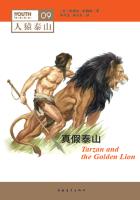后半夜,雨点渐止,深邃的苍穹上但见密密麻麻地布满璀璨的小星星,宛若珍珠玛瑙,一粒粒皆将自己的倩影投落在铜镜般平静的江面上,顾影自怜。那轮傲骄的新月确实不见了踪影,仿佛已坠入深深的海底,万劫不复。
“鹰面鬼手”身披黑色丝绒长斗篷,站立于罗刹江面一艘大沙船的甲板上,身后三十多名水手,正在卖力地转动沉重的挂轮,粗壮的麻绳与挂轮相摩擦时,发出“嘎嘎——”的撕咬声,要将巨型蝶状铁锚从岸边吊起,沙船准备起航。
一切准备就绪,此刻的江面无风无浪,“鹰面鬼手”一声令下,沙船朝临川湾进发。他正抬头仰望星空,一颗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扫过略带红光的银河,如飞蝇扑火般坠入远方海湾处沉睡的地平线下。他不禁哆嗦了一下,闭上眼,仿佛看见了海面上浮起大片大片鲜血,被巨浪旋转甩动,血色泡沫围绕临川湾中黑黝黝的礁石,如江河泣血一般,久久无法散去。
副手递过来一个单筒望远镜,前方海湾处风浪渐大,一艘白鹞海船正飘摇于风浪之中。
“鹰面鬼手”镇定了一下神情,下令道:“全速前进,追击那艘‘白鹞’!”
副手凑近他身旁,提醒说:“大人,咱们这是平底沙船,只能行驶于江面,经不起海里的风浪。”
“鹰面鬼手”怒斥副手道:“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副手急忙在甲板上跪下求饶:“大人,小的错了。当然得听大人您的!”
“鹰面鬼手”继续从望远镜筒里查看远处海里那艘白鹞海船,无心理会这个差役。
只见一个巨浪猛然打去,白鹞海船忽然间消失于茫茫大海。他着急地移动望远镜,在海面继续四处搜寻那艘船,“白鹞”确实不见了,可身后临川湾的暗礁旁却隐隐地出现了一批艨艟战舰。他浑身上下像突然被雷电一击,声音震颤地问道:“为何会有艨艟战舰?”
副手起身,接过“鹰面”手中的望远镜,也朝船后临川湾方向望去,果见一大批艨艟战舰似是在那蓄势待发。
“线报说,蓬莱元帅府里近日没有动静,那么定然只有……”副手恐惧地揣测道。
“建德怀孟万户府!”“鹰面”替副手把话补充完整,他也不禁打了个寒颤,真是万万没想到!
“鹰面”举着望远镜再朝海面望去,依然没有找到那艘白鹞海船,再回望临川湾时,刚才所见一大批艨艟战舰也已如幽灵似的全凭空消失了。
“撤!”“鹰面”下令道,今日出航也不算没有收获,仅是答案让他有些吃惊。
平底沙船急忙在海湾出拐弯,回到罗刹江的航道里,驶回临川府地界。
话说刘山甫自从象山书院回到临川,一心要参加秋闱,希冀鲤鱼跃龙门,定要步入仕途。因家住马市街旁,日日被小贩商贾的吆喝声,骡马的嘶鸣声吵闹地无法安心复习,便背起竹箱笼,告别母亲和兄长及嫂子,前往灵隐寺寄宿,做最后的冲刺备考。
在灵隐寺后堂的厢房内寄宿几日后,发现此地也非他理想中的清静之处,日日有香客往来,依然嘈杂声不断。他于是再次背起竹箱笼,沿着琅珰岭一路攀爬,最后来到五云山。但见小径两旁山茶遍野,古树林立;云山显翠,露草凝珠。远处山坳里隐隐显出星星点点几个散落的茅草房顶,好一处幽静之所在。他于是向一户农家租用了山坳深处孤零零的一间茅草屋。那家农户的男丁是个樵夫,见刘山甫衣着长衫,斯斯文文,似乎手无缚鸡之力,便提醒道:“秀才,此地经常有野猪豺狼出没,你一人寄居于此不害怕吗?”
刘山甫一脸不屑道:“比起市井的嘈杂,在下倒更愿意与野猪豺狼为伴,只要能清静地读点圣贤书,又怎会惧怕那些畜生?”
“哦哦,秀才您不怕便好!”樵夫瞅着刘山甫那副书呆子模样,料想此人定然从没见过什么豺狼野猪,也不晓得啥叫危险,既然他自己喜欢,就随他去吧,我该提醒的也提醒了,也别怪我不厚道。接着补充道:“要有啥事儿,秀才记得来我家找我……”樵夫边说,边用手指指山坳旁一大片茶园边上的几间土屋。
“谢谢兄台!”刘山甫拱手相谢,其实也是示意樵夫不要再啰嗦了,他刘山甫要进屋读书,你可以走了。
樵夫见该交待的通通交待了,便拿起斧头,顾自进山砍柴去了。
刘山甫住在这五云山下的山坳里,确实感得清静,日日诵读四书五经,学业进步极大。有时在屋里待久了,腻歪了,他便捧着书到一旁的竹林深处去念诵。竹林幽僻处,隐有花果馨香;远处青山下,淡菊清雅。
一日,他正在竹林里头默念《论语》,一阵微风裹着花香果香吹来,还携带着只言片语飘入他耳畔。
“埋这里行吗?不会被人偷挖走?”
“这地方除了野猪豺狼,还有谁来?”
“那边不是有座茅草屋吗?”
“空的,没人住。”
“那就埋这儿吧!”
……
刘山甫躲在竹林里的一块大石头后边,远远瞧见两个身着褐衣的男子,正在竹林的另一头挖土,随后填埋什么东西,鬼鬼祟祟的,一边干活还一边不停地四处张望,极怕被人发现。
待两人走后,刘山甫也不敢靠近填埋处。又过了几日,见无人再来此地,便在某个黄昏日落后,带了把樵夫留于茅草房中的破铲子,悄悄刨去被陌生男子填埋的泥土,挖不多时,露出一个金黄缎面的锦盒,他放下铲子,俯身打开锦盒,里面竟藏有一颗硕大的珠子,足有一只小奶猫蜷缩起来那么大。在昏暗的周遭,璀璨夺目,熠熠发光。
刘山甫被这亮光吓了一大跳,急忙盖上锦盒,心脏砰砰的上上下下乱蹦跶。
“要报官吗?或者……”他寻思道,“但秋闱在即,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考试要紧!”
“可这颗珠子怎么办?留在此处让贼人再挖走?”他猜测,此珠子定然是贼人偷窃来的赃物。
“那不行!我读那么多圣贤书,就是为了当官,为民主持公道,哪里能任由盗贼猖狂,肆意妄为?”想到此,他热血沸腾。便取走锦盒,用铲子将土填埋回原处,最后用脚将地踩踏平整,恢复本来模样。
他抱着锦盒,忐忑不安地回到租住的茅屋。“该拿这个锦盒怎么办呢?总不能随意搁置在屋里的案桌上吧?”他在茅屋四周环视了几遍,最后决定把锦盒埋到柴房里,踏平柴房的泥土后,他又在埋锦盒处堆放好些柴火,最上边放了些松枝做记号。
后边几日平静如水,日子淡淡地从指缝间悄然流过,那两个贼人再未出现,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他日日去竹林里念书,也不忘朝原先贼人埋藏珠子的方向探看,皆无人出现。
直到有一日睡梦中,他的茅屋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位女子。
女子衣着粗劣,面色黯淡蜡黄,俨然一辛劳的中年农妇。她披头散发地站立于刘山甫面前,向他哭诉道:“秀才,我系闽地织麻的妇人,这粒珠子原在我家的一只蜘蛛体内剖得,能明照一室,不幸被贼人瞧见,仅付我十五千夺去……奴家今想索要回珠子……”梦中的妇人瞬间变得青面獠牙,如野兽鬼怪般朝刘山甫猛扑过来。唬得刘山甫浑身上下冒了一身冷汗,从噩梦中惊醒,气喘吁吁,胸口上下起起伏伏,久久惊魂未定。
“这是不祥之物……不祥之物啊……”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因珠子惹祸上身,不禁紧紧抱住被子,哆嗦了几下。
当日黄昏时分,他的茅屋门外确实来了一位女子,只是这位女子与他梦中所遇的农妇截然不同。大约二十上下年纪,乌黑浓密的发髻,翠弯弯的新月眉儿,樱桃小口,粉扑扑的腮帮,杨柳腰肢,石榴裙下隐隐露着窄星星尖翘脚儿,一副娇滴滴的模样,脆生生地喊道:“屋里有人吗?”
刘山甫走出门,陌生女子便对他谄媚地笑道:“相公,你一人住这儿?”
刘山甫见到这位妩媚妖艳的女子,又打了个寒战,荒郊野外,日落黄昏,为何会出现这般模样的小女子?莫非是鬼?
女人见他害怕,便极力辩白道:“相公,我白天带着家仆上五云山游玩,因要采撷些野花带回去,跟自家丫鬟走散了,这会儿走山路走得我脚疼,想在相公您的宅邸歇歇脚,不知方便否?”
刘山甫意欲拒绝,还没等他开口,女子便“哎呦”一声倒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腿,哭诉道:“相公,我的腿实在疼的很,您就行个方便,让我进屋坐坐吧!”
刘山甫慌忙去搀扶女子,女子身上飘散出来的芬芳瞬间让他意乱情迷,神志不清……
等他清醒过来时,已是第二日的清晨,天色蒙蒙亮。那位女子娇羞地搂住他,刘山甫慌忙跑下床,发现自己竟然什么都没有穿。他是读圣贤书的人,秋闱在即,他却做出了有辱斯文的事情,真是对不起孔夫子,对不起孟夫子……
他蹲坐于床边,抱着自己的衣裳嚎啕大哭;那位妖娆的女子却在他床上,咯咯倩笑。声音婉转动听地劝说刘山甫道:“相公,您就别哭啦!……奴家都没有哭,你哭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