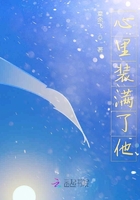紫鸩还记得今岁的正月初八,当时那方同整个大唐相比都是繁荣鼎盛不可方物的天水郡城,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新春的富足和喜悦之中,而小小的它则困顿的窝在它金丝笼,鹅毛眾的华丽鸟巢之中,怏怏的打着盹。
旁边泼辣喜动的豹精在它新猎来的老虎皮上翻了个身,还笑着对笼子里的它说道:“今天谢神,咱们家王爷要摆好大的一场戏台子,演的是许平王万里烽火赴家国呢,而且呀,出演许平王的是咱们家的世子,我还是今天才知道的,小鸟儿你要不要去,姐姐我偷偷的带你过去。”
结果当年奔赴万里烽火台浴火重生回到家国的许平王没有出场,而它近十年赖以生存的郡王府却烧的火光冲天,那天谢神之后,新登基不久的武后就以一道乱臣贼子,勾结谋逆的罪诏,火烧了天水郡王的府邸,老郡王仰天大骂武后祸国殃民,在一万大军的包围之下,从天水郡的烽火台上一跃而下,他家中的妻小仆人,全都被锁在王府里活活烧死。
只有当时跟着豹精偷跑出来的它,瑟缩的躲在王府门前的灌木丛中,才得以活了下来。
而它那个美丽泼辣,却又至情至性的豹精姐姐,当得知抚养他们的世子竟然也在王府之时,它只给紫鸩留下了一个背影,而后凄厉决绝的冲进了漫天的光火之中。
后来直到第二日的清晨,所有的兵马都踏过天水郡王府的残垣断壁,往洛阳拔兵之时,这只在幸福宠爱的包围里生活了近十年的小鸟儿,这才仰天大哭了起来。
但是突然有一只手,搭在了它的脑袋上,它顺着晨曦的暖阳和天水郡王府的焦木浓灰之中抬起头,看见一直抚养着他的世子,披头散发,灰头土脸的站在它的身后,他的手里,还握着豹精姐姐生平里一直珍重着挂在脖颈之上的玉佩,那是世子在捡到她的时候,送给她的第一件的东西。
它还记得世子当时脸上的神色,仿若万念俱灰如同天水郡王府被烧的只剩了一片灰烬一般,但是却从这余烬里,似乎又冒出了丝丝星火,它的世子从那一刻起,就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万念向善,而且温润如玉的公子哥了。
他带着它离开了满目疮痍的天水郡城,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的来到了那个害死他们家所有人,它最亲最爱的人的凶手的老巢,神都洛阳。
它的世子似乎变了,他变得不修边幅,混不吝,邋遢,开始吆五喝六的说话,时常酗酒,彻夜不归,时常会有人过来轰隆隆的砸门,而它守在他们在洛阳购置的那个小小的,似乎连天水郡王府十分之一都不到的院子里,整日提心吊胆的活着。
它放心不下他的世子,直到有一天,那或许是该来的那么一天,它的世子突然又重新替它梳理羽毛,给它买了一件很贵的,很华丽的衣裳,而后他摸了摸它的头,一如他十年来每日都做的那般,笑着对他说:“我现在养不了你了,但是洛阳城的工部侍郎是个爱鸟如命的人,他会很好的对待你的,到了新家,不要老是哭闹,毕竟……毕竟此时不是在天水郡城,而他那里,也不是天水郡城王府了。”
它记得自己被套上了鸟套,被一个穿着严实,带着布手套的人揽着往前走,它一直梗着脖子往回看,可是它的世子,却已经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淹没在洛阳城的繁华之中了。
小小的它想哭,可是世子说,它不能哭。
它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人对它同世子对它一般好了,直到到了那个工部的侍郎家里,遇到侍郎分配照养它的养鸟人。
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人,也是非常爱鸟的人,他无比的细心和耐心,而且常常同它一起玩耍,而它偶尔才会蹦出的一两声的嗯嗯啊啊,那个人听了之后,却发出了它见过的,和当年它第一次学会说话时,世子露出的那一样的笑容。
可当它逐渐接受这个新来的饲养人,并且开始依赖它的时候,它却开始发现,那个人的身上,开始长出了一个个的,瘤状的小疙瘩,硬硬的,戳不破。
它刚开始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怪病,直到有一天,它意外的看见了那个人跟马房的赤脚大夫说话,那大夫对他道:“你这是毒,鸩鸟之毒,你明明知道这鸩鸟吃了越有毒性的食物,羽毛之上的毒素就会越大,而你竟然也不戴布手套,穿麻衣,就敢这么触碰它。你现在已经毒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而那个人却依然温润的笑着,道:“侍郎大人只喜欢颜色靓丽的羽毛,要不然就会将它扔掉,它虽然是只鸟儿,但还是个孩子,要是把它给扔了,你让它自己,怎么生活,而我不戴布手套,是因为它喜欢我摸它的脑袋。不过,如果我当年的儿子要是没死,现在也差不多这么大了……”
那人还在断断续续的说着,可是小紫鸩却已经听不下去了,它自离开世子之后第一次哭了,而这一次,却已经不是为了世子,而是为了那个将它像儿子一般抚养的养鸟人。
那天晚上,那个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的摸着它的翎毛,边笑着道:“你怎么不吃晚饭?不饿吗?”
紫鸩抬起它浑圆透亮的大眼睛,定定的看着那个人,它的眼睛初而明亮,而后渐渐湿润,最后它低下头,泣不成声。
就连那个人什么时候倒在了它的面前,再也醒不过来了,它也忘了。
紫鸩抬起它湿润的大眼睛,定定的看着面前他的世子,哽咽道:“您说我们这种鸟,要是没存在那该有多好?我没想杀他,可是害死了他,我没想杀人,可是人们却用我的羽毛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