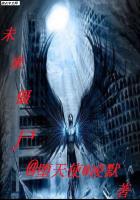门口的脚步声走远了,她爬过去捡起来看。陈以航漂亮的字体霎时闯进了眼帘,她抿了抿干涩的唇。
--阿荏,他们将一切都告诉了我,我很担心你。你曾答应我要陪我一起走下去,所以请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再哭了,乖。还有,也请不要怪你父亲,能有父亲疼爱是一件太过幸福的事情。虽然我不甚赞同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但他这样只会激起我更多的斗志,我一定会向他证明自己,让他相信我可以给你幸福。请等我。勿念,以航落笔。
寥寥数语,字虽不多,却句句情真。
她仿佛能看见他提笔的模样,阿荏闭上眼睛,有泪顺着脸颊落下。
他替她重新点燃了希望,让她心底的枝桠再度抽芽。
阿荏旋开台灯,抽出信纸准备回信。时间从身边不动声色地奔跑离去,甚至可以听见空气里秒针转动的滴答声,每一声都提醒着阿荏,又过去了多久,她还没能见到他。
写了撕撕了写。终于写完时,已是正午。
屋外的雨仍旧下个不停。佣人进来给她送饭,风萍也走进来。她刚看了一眼阿荏,红红的眼眶里就又落了泪。这哪儿是她的小女儿,那张巴掌大的小脸已经瘦完了,皮肤发黄无光泽,那个下巴都尖得似乎能割破人的手指。风萍扶她上床,苦口婆心:“听妈妈的话,跟你爸认个错,跟那个男孩子断掉好不好?等你长大了还会碰到更好的人的。”
杨颂荏不看她,蜷缩在被子里,咬着唇:“让我见姐姐,我就吃饭。”
风萍愣了一瞬,大喜。
门被关上。
杨颂荏压低了声音,满眼含泪委屈地望着姐姐,“我知道是你把信给我的,我求你帮我把它送出去,就一次,我保证就麻烦你这一次,姐……”她的声音放得很轻,眼泪一滴一滴,呼吸也断断续续,仿佛下一刻整个人就会化为一阵尘烟散去。杨昱美捏紧了拳心,很想拒绝她的要求。
“好。”她听见自己说。
凡事起了头,就很难停下来。
有了第一次,就会不间断地有第二次、第三次……
杨昱美快被他们传信的活给逼疯了。
第五封。
她平躺在床上,将信举高遮住炫目的吊灯,可刺眼的光芒仿佛仍能穿过纸张直直刺向她的眼睛,杨昱美恍惚看见眼前重叠成妹妹漂亮的面容、以航哥哥温柔的微笑,不断交替、旋转,他们一起在嘲笑她,恶毒的女生、得不到爱情的女孩子、以航哥哥永远不会喜欢你、你不要再奢望了……
她“蹭”一下坐起身。她凭什么要这样义无反顾帮他们!
杨昱美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她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不。
她不能把信的事情告诉爸妈,虽然杨秉文可能会夸她,甚至更加讨厌陈以航,但这样会破坏她最近在陈以航面前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新形象,她还不会这样愚笨。
那还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父母神不知鬼不觉,又可以让他们不再彼此鸿雁传书呢?
杨昱美依约来到了阿荏房里。
“什么!”杨颂荏满面惊慌,“你说爸爸发现信的事情了?”
姐姐点点头:“荏荏。”她拉起阿荏的手,面色诚挚:“是高子乔和我最近联系的太紧密了,今天他给完我信之后,爸爸一路跟到了我的房间,他问我手里藏得什么东西。”
阿荏倒吸了一口寒气,杨昱美又说:“我当时吓得手一哆嗦,信就落地了。不过你放心,我赶在他之前就捡起来将信撕碎了,他并没有看到信的内容。”杨颂荏耳边忽然变得寂静无声,她靠后退了几步,勉强倚靠着桌角,就连连日来的最后一抹希望也要被夺去了……沉默了半晌,姐姐的最后一句话变得分外清晰,她说:“我担心……以后可能都不能帮你们传信了。”
杨昱美说完就低下了头,让人看不清楚她面上的表情。
杨颂荏朝姐姐用力笑了笑,她哽咽说,谢谢,没关系的。然后就爬上了床,用力瞪着天花板。那是怎样一种绝望的神情,任谁看了都会觉得心悸。
屋外黏腻的雨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
天气预报说,雨季这才刚刚开始。
是不是谎话说多了,就会变成真话?
杨昱美没有一丝做了坏事的忐忑感,她得意地拿起抽屉里陈以航写给阿荏的信。带着一丝顶礼膜拜的心情,她拆了开来。
曾经做梦都想要知道那样冷淡疏离的男孩子热情起来又会是何种风景,她以为看了信之后就能离她的以航哥哥更近一些,可当她果真激动地一字一句念完全部内容了,她才发现自己就快要嫉妒的发狂。
所谓一字一刀,她至此方知她错过了多少时光,竟让陈以航和杨颂荏的感情,发展到这样深刻而无悔的地步!
杨昱美受不了般地叫出声来,她拼命地撕啊撕,最后信和信封都化为一片一片的雪花,飘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她被他们浓烈的爱情包围,她身处其中,宛如最卑微的小丑杨昱美换身衣服,跟司机报了个地名,出了门。手机屏幕一亮一亮,显示着“短信正在发送中”的字样。
TIMES-CAFé咖啡屋里,高子乔站在涂鸦墙边,陈以航则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靠着街边的落地窗。看到杨昱美走进来,他站起身。高子乔也立刻挥着手奔跑过来。
杨昱美冷冷一笑,心想这样子的欢迎,怕也都不是冲着她来的。
沉默。
所以接下来这句话就显得格外有爆炸力。
--信被发现了,我没让他看到内容,但爸爸很生气,恐怕之后都没法子了。
这句话宛如魔咒般,瞬间就将陈以航的声带剥夺,他张着口,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高子乔咳了咳,“我去拿饮料。”
杨昱美这才发现咖啡吧里坐着的人不多,大半空着。除了吧台那里的侍应生,有妈妈带着小女儿来吃布朗尼,或者两对情侣,幸福而甜蜜地依偎在一起。杨昱美看着他们,立刻浑身不自在。陈以航和她所坐着的地方是一个圆弧形的沙发,身边坐着的男生的腿长长撂过来,她的余光里怎么也除不去他的脸。男生抬着头目光直直看向窗外,眉心深蹙,她刚刚伸出手想要去抚平,陈以航恰好也转过来看她,杨昱美的手立刻神经质地发抖,血管也莫名其妙跟着地跳动。
男生瞧出了她的异样,“手受伤了?”
她慌忙收起手,快速地理了理卷发,自我嘲笑的同时,终于和他的目光接在一起。
“比起荏荏来,我这不算什么。”
果然,男生的目光更加温柔了。
高子乔有事先走了,陈以航出去同他在门边说了会话。
杨昱美坐到了窗边,陈以航回来时坐在了稍外一些的地方,原本三人的位置中间霎时留下了一个空白。杨昱美心里别扭起来。
“学长。”
“嗯。”
你再坐进来一个吧。她很想喊出声,最终却是说:“……你别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男生笑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他对她说谢谢。杨昱美转过头,窗外的天空明明是灰蒙蒙的一片,可她却觉得那里正不断闪着光亮。她紧咬着嘴唇,承认无比贪恋他在自己身边的感觉,既然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她唯有更加坚定的走下去,抬头挺胸。
她绝对绝对不要再将陈以航拱手让人。
深夜的书房还亮着灯,杨秉文还没有睡意,他正满面疑虑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大女儿。
“我能说服妹妹和陈以航分手。”斩钉截铁的、无比自信的语气。
杨秉文双手交叠,身子朝椅背靠了靠,“怎么说?”
杨昱美唇角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只不过到时候需要您亲自到场,看着他们分手,只有这样,才能分得彻底。”
她转身出了书房,一步一步走向三楼妹妹的房间。
阿荏将窗帘拉得大开,单薄的月光穿过雨层照在她的脸上,心脏似乎也跟屋外的世界一样,死了般的寂静。姐姐刚刚对她说了什么?哦对,说现在只有一个法子,可以让她走出这里。
她是无比极其非常想要走出去,可杨昱美竟然告诉她,那个法子是--分手。
--先假装分手,出去再说。我本来想要先去跟以航哥哥打个招呼,让他陪你演这一出戏,可又怕演的不逼真骗不了爸爸,所以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们了,等你以后再同他解释也是一样的。
--就算分手了又如何,他那么爱你,哪怕让他等你三年,到大学里你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话说回来,只要出去了,凡事就有希望,你先想办法把手机拿回来,到时候还可以偷偷发短信。一直关在家里,你不怕爸爸被你的犟脾气逼得走了极端,把你送出国了,那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
阿荏想着想着,就笑出声来,一边笑着又一边流下眼泪,本来以为被关在屋子里的这七天时间里,眼睛早已干涩得流不出任何东西了。可是现在,她一想到她重新获得自由、重新见到陈以航的代价竟然是和他分手,泪水便再次漫上眼底。
那个英俊而面容冷漠的男孩子,是她唯一的,全部的,世界啊。
阿荏将头埋在膝盖里,一遍遍哭喊着陈以航的名字。
以航哥哥,你到底在哪里。
我就快要被绝望吞没了。
事实证明这件事情由不得她。
她拒不同意与陈以航分手,杨秉文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目光里都是沉痛,“我有很多个办法让一个毫无背景的少年从凉城消失。我现在来不是跟你谈条件,而是在命令你。”
杨颂荏像在看陌生人一样看着自己的父亲。
--爱上陈以航,就是这样大逆不道不可接受的罪孽?
时隔七天,毫无神采的杨颂荏被推着走出了房间。
天空都在哭泣。
她心里忍不住地一阵一阵难过,眼圈在一瞬间红了起来。
似乎秒针才走过了一圈,就到了约定见面的地方。车门打开,暴雨的气息一瞬间飘进车厢里。她的少年,就等在不远处的雨帘里,满脸疼惜又欣喜地看着她。
他还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你知道该怎样做个了断的。”杨秉文漠漠开口。
杨颂荏身形顿了顿,这才关上门冲进雨幕中。少年拼命朝她奔过来,连忙将伞罩在她的头顶,从上到下心疼万分地打量着她,好半晌才哽咽着说:“瘦了。”
杨颂荏抬眸回望着他,轻轻挣脱开他的双臂,笑了笑:“我们分手。”
呼吸也似乎停了停,男生笑出声来,“我不信。你爸爸逼你的?”
杨颂荏的目光始终回望着陈以航,没有躲闪,也没有逃避,她大方地微笑着:“这七天里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是你根本配不上我,他们说的对,你是个孤儿,给不了我想要的一切,我不想以后跟着你吃苦。”
男生被这样的话彻底冷冻,她嘴角的笑容那样淡漠而陌生,连目光都是微带轻蔑,硬生生将他看扁。
“你是阿荏,还是杨昱美?”
她笑一笑,低下头,慢动作般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他衬衫的衣角,微微扯一扯。
只属于他和阿荏的小动作。
“如果我请你等我四年,四年后我大学毕业,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给你!阿荏,你不要这么轻易放弃好不好?”陈以航清澈好听的声音伴着雨声幽幽响起,比以往都要急切。阿荏并没有抬头望向他,只是脑海里还可以描绘他俊朗的样貌,他柔软又乌黑透亮的头发,干净漂亮的像个天使。
默了半晌,清越的女声答道:“四年?那时候你刚刚毕业,拿什么在社会上立足?我爸爸就是凉城数一数二的富商,你觉得你需要多少年才可以与他抗衡?人这一生又有多少个四年可以挥霍?爱情这个东西,玩一玩就够了,你该不会当真了吧。”
陈以航低头凝望着她素净的小脸,她的神情是从未有过的高傲冷艳。
“我要走了。”生怕再晚走一秒就要演不下去。
男生无助地像被抢了玩具的孩子,他委屈地想要拦住她,可又不敢。
阿荏又朝他笑一笑,“你不是那样纠缠不清的人,别让我看不起你。”他果然顿住了步子,她抬起头看见他柔软的头发遮住双眼,眼底透出的光芒格外痛苦。
她跑上了车,男生还怔怔立在原地,看着车越开越远溅起一路的水珠。
他白衬衫上的褶皱在雨帘里发出模糊的光。
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
一个转弯,阿荏就看不见了。
压得低低的抽泣声开始不受控制地变高,杨颂荏一脸痛苦地捂着脸,女孩子柔弱的哭泣声充满了整节车厢,杨秉文听得无比心烦,“不许再哭了!”
她抬起脸,一双眼睛通红通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爸,我不再爱您了。”女生颤抖的尾音逐渐分岔在薄暮微凉的空气中,让杨秉文也不由地跟着颤一颤。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她,胸腔深处忽然开始微微地发酸。
一回来,杨颂荏立刻就病来如山倒。回来当天阿荏就开始发高烧,温度直接烧上了四十度。又因为多日不曾好好饮食,她的胃部亦生了溃疡,就连呼吸道都有些感染发炎。
疼。
所以连眉心都一直紧紧蹙着,哪怕是陷入沉睡里,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事情一直迫在心头。
私人医生为她配了诸多瓶药水,短短数日,阿荏手背上已经满是针孔。风萍为此还同杨秉文吵了很多次,质问他为什么要把事情闹成这样,那个男孩子已经没有家了,他还抓着不放,现在累得自己女儿受这样的苦。她骂他不配做一个父亲。杨秉文只说他有自己的打算。可事已至此,风萍也没其他的法子,只能连日来都守在阿荏的床沿,寸步不离地伴着,一直一直哭。
夜深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