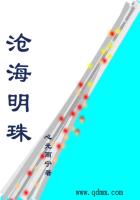“你竟然敢往本公主的衣服上丢泥巴!好大的胆子,你是谁?为什么往我的衣服上丢泥巴?”
牧察空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的小手,把泥巴都蹭到了自己的衣服上。
“我是牧察空,我……对不起。”
牧察朵仔细的审视着牧察空,确实是不认识,心下奇怪,一个她认识都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要弄脏她选中参加彩衣节的衣服呢!要是牧察樊,牧察澜她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平日里他们就经常相互捉弄。牧察朵想了又想,一拍天灵盖。
“噢!我知道了,牧察樊,是不是牧察樊让你这么做的,来人,给我把牧察樊抓过来。”
两个侍女应声把在门外偷听的牧察樊给提了过来。
“哈哈,那个,朵妹儿也在哈!这是在干嘛呢?”牧察樊生硬的打了声招呼,又一脸无辜且好奇的问。
“牧察樊是不是你让他往我衣服上丢泥巴的?”
“怎么……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这个样做。”牧察樊结结巴巴的说。
“不是你?!那你为什么在门外?”牧察朵问。
“我路过,路过。”牧察樊说斩钉截铁。
牧察朵狐疑的看看牧察樊,又看看牧察空。指着牧察空说:“那你说,是谁让你往衣服上丢泥巴的?”
“我,我只是……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能说。”牧察空紧张的说。
“你不说就算了,本公主不想知道了。不过你弄脏了我的衣服,总要赔我一件的。”
牧察樊被牧察朵的反应惊的目瞪口呆。
“就这么算了?”牧察樊问。
“阿樊哥,有什么话要说吗?”牧察朵故意提高了音调说。
“没有,没,没有。”牧察樊的头摇的像个拨浪鼓。
牧察朵不舍的看着那件彩绛云衣,玉手纤纤,就欲伸手去抚摸衣服的料子。
牧察空眼疾手快,及时拦住了她。牧察朵疑惑的看回牧察空,“你做什么?”
“别碰,脏了。”牧察空眼神坚定的说。
“泥巴而已……可惜了,这么好看的衣服……”
牧察朵收回被牧察空拦住的手,上下细细打量牧察空。心想这样一个人老实的家伙,为什么偏偏和牧察樊他们混在一起。看来以后要有的玩了,这次就放过你吧!看在你为人仗义,长的也还不错的份上。要是能收你当本公主的跟班就好了,那样我就再也不用担心闯祸被父皇母后教训了,是个背锅的好苗子。
牧察朵用很欣赏的眼神望着牧察空,牧察樊看她那两眼放光的样子,还以为她吃错药了。
“朵妹,你没事吧?不会是脑袋被门挤了吧?或者脑袋进水了?”牧察樊刻意把“进水了”咬的贼清楚。
“牧察樊,我看你是又想尝尝本公主独创的胡椒粉拌芥末蜂蜜糕了吧!”
牧察空像想到了无比恐怖的东西,脸都绿了,直犯恶心。
“喂!那个你,一天之内要把全朵牧最漂亮的衣服给我找来,后天的彩衣节我要穿。”牧察朵掐着不盈一握的腰肢说。
牧察空点点头,牧察樊也跟着紧点头。
牧察朵趁牧察空不注意伸手又要抚摸彩绛云衣,因为她听侍女说,这件衣服布料薄如蝉翼,还有冰冰凉凉的感觉,她还从没见识过这样的料子,自然要摸一下。
就在牧察朵的指尖还差0.1厘米就要触碰到衣服时,牧察空一手推倒衣架,一手推开牧察朵。
牧察朵不满的看着牧察空,心里愤愤不平。
牧察空的额头渗出冷汗,同时感觉到自己刚刚触碰到衣服的左手心,像火烧一样疼,皮肤上的掌纹都撕裂了一般,绽出血来。
牧察朵,牧察樊两个人满脸的震惊。牧察朵吓得都哭出来了,带着哭腔说:“快,快传太医,快叫太医来。”
牧察樊心里扑通扑通的直跳,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牧察澜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一进来就看到地上淌了一摊血水。花白头发的太医拿着银针往牧察空的身上扎。
“他怎么样了?”牧察朵哭着问。
“目前还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此毒奇诡,触则皮开肉绽,微臣还是第一次遇到。好在王子手上粘了些泥巴,中毒不深。只是这手怕是……日后会有些不便。”
牧察朵红肿的一双眼泪汪汪的眼,恐惧的瞄了眼倒在地上的衣服。身上顿起一片鸡皮疙瘩。如果刚刚是自己的手碰到了衣服,又或者是自己穿上了这件衣服,那此刻自己……皮开肉绽……牧察朵不敢再想下去,这是她这个年纪无法想象也不敢想的痛苦。
有人要谋害公主的消息,顷刻震惊了整个皇宫,牧察朵父皇母后火急火燎的来到牧察朵和牧察空他们待的偏殿。
皇宫的宫门都落了锁,任何人不得出宫。与彩衣大赛相关的一干人等,全部拘押候审。
皇后日夜守在牧察朵的身边,把她看的死死的,她的一切用品,都由专人负责试毒。
牧察空被留在宫中全力救治,牧察朵的父皇牧施游飞鸽传书通知淇河郡王牧察空受伤的消息。并且牧施游还日日亲自去看望牧察空。
牧察樊和牧察澜则躲在家里不出来了,一想到他们两个的恶作剧,无心的一句谎话,竟然一语成谶,不禁心惊肉跳,心有余悸。
牧察朵一直央求母后,想去看望牧察空,毕竟是因为她,牧察空才受伤的。牧察朵是第一次遇到除了她父皇母后外,对她真心实意的人。
宫人们对她都是敬而远之,牧察澜,牧察樊他们虽然会和她玩,却也做不到为了救她,而让自己受伤。
“母后,您就让我去看看牧察空吧!要不是他拦住了我,那此刻……”
牧察朵的母后赶忙掩住她童言无忌的嘴。
“快呸呸呸,胡说什么呢!凶手没抓住之前,母后哪也不许你去。万一你要有个什么好歹,你让母后还怎么活啊!母后就你一个女儿,好不容易把你养到像朵花似的年纪,母亲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牧察朵的母亲在牧察朵的寢殿住了六七日了,一刻也不和牧察朵分开,就连她出恭,她母后都等在一旁帮她揉手纸。
牧察朵都要被闷疯了,哪也不能去,什么也不能做。失去了自由,就像折翼的鸟儿。
牧察朵枯坐了一天,坐在琴案边,练习《潇湘水云》,她的手都酸了,眼睛也看花了。而且这曲目就跟催眠曲似的,听得她连打瞌睡。一打瞌睡,又立马被抓包,还要从头开始。
牧察朵的母后平日对她的琴棋书画的学习,还是很严苛的。因为她是皇室最尊贵的公主,更是整个朵牧最最尊贵的公主。她的品行处处都有人盯着,所以她的一切都代表了皇室的颜面。
那么在一些宴会上,节日上就免不了要她参与展示才艺。
她不仅要学琴还要学琵琶,萧,陶埙,编钟等。除了乐器还有焚香,制香,品茶,插花等。对于五谷,农耕,节气也要了解。
反正就是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技艺她都要学,还要样样学精。她为了能躲避这些课业,那是无所不用其极,也正是这样艰难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她古灵精怪的性格。
“母后我都练了一天的琴了,手都要破了,娘亲,好娘亲,我就歇一会,就一会儿。”牧察朵委屈巴巴的说。
“你呀!就会撒娇赖皮,这曲子是我半月前留给你练习的,到现在你都没学会,平日没人看着你,就偷懒了是吧!”
牧察朵摇着华服妇人的衣袖嘟着小嘴,带着小奶音,奶声奶气的唤道,“娘亲~娘亲~”
“好啦!就一柱香,一柱香之后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