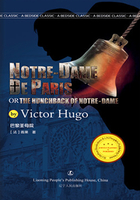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要想对中原作家群这样一个纯粹因为地域的因素而集结在一起的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进行具有学理性的概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干脆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在于,文学创作本身就是最讲究思想艺术原创性的一种事业,这种事业本身就要求每一个作家必须以个性化的面目出现,必须最大程度地保持非同于他者的个性化思想艺术品格。但我们在这里所要进行的工作,却偏偏就是要在这样一群以个性化追求为根本志业的作家中寻找出他们的共同点来,其难度自然可想而知。但既然来了,既然客观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中原作家群,那我也只能够勉为其难地试图在这一方面有所努力。
我想,我们其实应该在一种比较的意义层面上,寻找并谈论一下中原作家群的共同性特质。因为可比性的原因,这种比较将在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所谓中原四省,即陕西、山东、河南以及我自己所在的山西这四个省之间进行。从地缘文化的层面上,在我看来,这四个省份里,陕西与山东,均有着非常突出的文化保守主义特质。为什么是这两个省份具有浓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细细想来,恐怕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过程紧密相关。陕西,自打西周立国以来,一直到后来强盛的汉唐,可以说长期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而存在,是很多年的古代都城。其中王气之盛,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事实。因为如此一种历史文化渊源的缘故,在这个省份形成浓烈的文化保守主义特点,就是合乎情理的一个结果。这一点,在其中很多作家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山东,是古代齐国和鲁国的所在地,一向被称作齐鲁大地。在鲁地,最早出现了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这样一来,以孔孟为杰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最终形成,也就势在必然了。儒家文化,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传统。拥有了儒家文化,并以此来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底色,山东作家文化保守主义特质的形成,也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张炜、赵德发等山东作家作品中那样一种突出的道德化倾向,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与陕西、山东两个省份的状况有所不同,山西的情况,却是一种文体多元化倾向的形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西一共出现过三次创作高潮,一次是“十七年”期间的山药蛋派,另一次是1980年代的所谓“晋军崛起”。前两次创作高潮,山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一直体现在小说文体上。小说“一元独尊”的格局,到了当下开始发生明显的改观。尽管小说创作依然非常强势,但是,诸如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散文随笔等其他一些文体的异军崛起,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发展态势。纪实文学方面,赵瑜继续在全国报告文学领域保持着领军的地位,而且还有周宗奇、张石山、哲夫、鲁顺民、黄风、寓真等作家,也都积极地介入这一文体领域,取得了系列创作实绩。近年来,赵瑜佳作连连,相继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等。传记文学方面,陈为人、韩石山、周宗奇等作家都有非常抢眼的突出表现。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就是被看作“庾信文章老更成”的陈为人。他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不仅真切地透视表现了传主唐达成堪称复杂的精神世界,而且还进一步以唐达成为焦点,对于中国文坛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了真实的记述与犀利的剖析,在学界便赢得了口碑。此后,陈为人的主要精力就投入了一系列作家传记的写作过程之中,先后出版《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十张脸谱》等长篇传记作品。散文随笔的创作同样兴盛一时。值得注意的作家,首先是今年已届九十高龄的草书大家林鹏,我称之为思想者林鹏。还有张锐锋、闫文盛、毕星星、聂尔、指尖等,也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关键问题在于,山西文坛何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文体多元化的局面。我以为关键原因在于一种文化多元开放意识的具备与形成。置言之,是因为在山西,干脆就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比如林鹏,比如谢泳,比如丁东、邢小群夫妇,比如韩石山、周宗奇、毕星星等。
与陕西、山东以及山西的情况均有所不同,或许与更处于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区,或者说中国的核心地区有关,河南既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山西那样的文化多元开放意识,那样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也没有出现在河南。相对来说,河南的情形是既传统又现代,既保守又开放,具体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既现实主义,又现代主义、先锋派,具有突出不过的实验探索精神。即以我自己最为熟悉的小说创作这一块来说,一方面,出现了诸如李準、李佩甫、周大新、张宇、邵丽、田中禾这样可以说是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诸如阎连科、刘震云(且不说他的故乡三部曲——《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还有他的《一句顶一万句》,幽默、反讽)、李洱(他的《花腔》的现代主义特质自不必说,最近令人期盼的,是他的鸿篇巨制《应物兄》)、墨白(简直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现代主义写作,实力派的现代主义作家、先锋派作家),还有新近几年刚刚由学者批评家而转型成为非虚构写作的集大成者,两部“梁庄”以及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的作者梁鸿。真的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并存,保守兼开放齐行。
接下来,具体分析一下阎连科《受活》中既本土又现代(或曰先锋实验)的语言运用策略。谈到阎连科对于本土化叙事策略的成功运用,最突出者当然是在其小说文本中对于方言口语的一种堪称得心应手的运用。其实早在创作于数年之前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与《坚硬如水》中,阎连科就已经明显地显露出了对于方言口语的浓厚兴趣,就已经表露出了一种运用方言口语进行创作的突出迹象。只不过,只有到了《受活》之中,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才更加引人注目,而且作家在运用的方式上也更加具有了某种自觉性。我们注意到,在《受活》中,不仅有着对于方言口语的大量运用,诸如“受活”“热雪”“处地儿”“儒妮子”“圆全人”“死冷”“满全脸”“脚地”“顶儿”“地步”“头堂”“撒耍娇娇子”等,均是带有明显的河南耙耧地域色彩的方言词语,而且一种堪以凝重称之的方言精神,也正最大程度地渗透在了小说的整体叙述流程之中。比如这样一段随手摘出的小说中的叙事话语:
再看一下台下的百姓们,瞎子、瘸子、聋子和别的残着的人,不消秘书和断腿猴起手鼓掌提醒儿,那掌声就噼噼啪啪响个不停了,像阵雨一冷猛落在屋瓦上,把一个庄落都震着了,弥盖了,经经久久地不息着,连树上那些许的青叶子,都生冷冷地给震落下来了。县长望着台下满世界人的脸上汪着的红,自个脸上刚刚那一息阴沉也被荡得没有了,只剩下被那掌声鼓噪起来的足满和灿灿然然的笑。
应该说,在这段话语中,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大约只有“一冷猛”“庄落”以及“生冷冷”等不多的几个,然而,由于运用了“提醒儿”“不停了”“震着了”“弥盖了”“经经久久地不息着”“一息阴沉”“足满”以及“灿灿然然”,等等,带有强烈乡土气息的表达方式,那样一种渗透流贯于其中的方言精神也就昭然若揭了。然而,也还并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在《受活》中,方言口语还具备了另一种突出的结构功能,成为作家阎连科一种特别得心应手的结构手段。具体来说,就是阎连科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十分自然贴切地将方言口语穿插于自己充满乡土气息的叙述话语之中,然后又以注释的方式在“絮言”部分牵引出另外一个故事来。这样,借助于方言口语的运用以及对于方言口语的解释,小说文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虽然复杂但又格外清晰的多重复合结构。这样一种巧妙至极的结构方式,与阎连科排斥公元纪年而只是刻意地使用天干与地支这样一种中国独有的纪年方式相结合的结果,便是一种作家所一贯致力的小说本土化艺术追求的自然实现。
然而,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把握阎连科《受活》对于方言口语的运用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我们还有必要引入陈思和先生关于语言问题的一种精辟见解。在谈到鲁迅《狂人日记》的语言问题时,陈思和首先断定:“鲁迅的语言却在中国传统语言的生动性多义性的基础上,融会了西方语言的精确性,《狂人日记》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我们给它一个名称‘欧化语’。”然后结合文学史的事实指出:“我甚至以为,从鲁迅开始,中国的语言进入了一种现代语,而不是一般的口语写作,它才是现代语言。所谓的现代语言,就是尽最大的力量,来表达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表达现代人所能感受到的某一种思想感情。这是我对‘五四’新文化语言的一种理解。”如果说鲁迅的“欧化语”写作乃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可以表达“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现代人所能感受到的某一种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在我看来,阎连科在《受活》中对于本土化的方言口语的运用的意义和价值,也殊几可以作这样的一种理解。如果把这样的一种理解与刘旭关于小说写作对于底层命运的关注与表述不可能的命题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也就完全可以说,大概只有如阎连科《受活》所采用的这样一种以方言口语运用为主的本土化叙事策略,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去逼近底层社会的存在本相,并对这底层社会的存在本相做出一种艺术化的真切表述。在我看来,在1990年代以来这样一个“全球化”直逼眼下的时代,如阎连科《受活》这样的本土化小说写作,的确呈示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