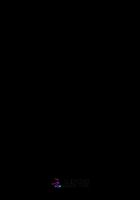首先,脑中想着土耳其和叔本华对印度的兴趣,他开始更广地考虑宗教,着重道德问题:“那么为什么这天启仅限于基督教堂?这天启与佛教、穆罕默德教(Mohammedan)有什么关系,他们也同样忏悔和行善啊?” (《安娜·卡列尼娜》,8章,18节,814页)此处的穆罕默德教与基督教的类比不实,说明列文对跨文化知识的欠缺;然而他追求广阔的世界范围的视野是一目了然的。后来在小说结尾处,他走得更远:“那么,犹太人,穆罕默德教徒,孔子信徒,佛教徒—又是谁呢?”(《安娜·卡列尼娜》,8章,19节,815页)他的直觉在身内外涌动,从近邻土耳其帝国的穆斯林转向有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俄国自身,而在另一个方向,又将亚洲多样化,在佛教上附加了中国的孔子。列文的思绪在这一点上中断了,但托尔斯泰眼中宗教与世界的连接是清楚的。此时,这两类的定义是无区别的区别—这不意味重视特性的托尔斯泰着意地希望化解世界多样性来取得全球统一。或许他曾想过这目标,可是他不会想象它的实现,无论是谈宗教或写小说。其结局是:他的主人公在精神探索时得到的非世界性信息结果却使他们去寻找与世界文化错综多样性一致的、广泛而含混的超国界观点。
6
我们再转来看普鲁斯特对世界性与世界文学的观点,这里不再有像《安娜》和歌德的直接联系。不过如弗斯罗夫斯基“迷人的格雷琴”所示,法国化的世界性眼光架构了他对浮士德的看法。哪一位法国世界性的编年者,分析家和法官能超越普鲁斯特,即便与他相等?【参照布鲁克斯,《世界性小说》(The Novel of Worldliness),285—286页。像亨利·詹姆斯一样,布鲁克斯认为普鲁斯特是法国世界性小说传统的终极成就的代表。】最突出的是《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头四卷中叙事者关于其外婆病和死的描写以及自己迟到的悲哀。和小说中详尽的社交场合相比,这些情节稍短,但其中的感情强度和真实性却打动了广大读者。随后它们又在第二部的《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 and Gomorrah)中达到了顶峰,其中第一章最后一节有一个标题,这在普鲁斯特并不常见。那标题叫“心的间歇”[《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 and Gomorrah),204页]。【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引言出自老牌/兰登书屋版(Vintage/Random House),它用经D.J.恩赖特(D.J.Enright)修改的蒙克里夫和基尔马丁(Moncrieff and Kilmartin)译本。以下的缩写用于指明所引的四卷:SW为《在斯万家那边》(Du c?té de chez Swann);WBG为《在少女花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GW为《盖儿芒特家那边》(Le C?té de Guermantes);SG为《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 and Gomorrah)。】当我们得知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Recherche)的最初三卷本版本用的就是这一标题时,这关于外婆情节的重要性才逐渐明了。【参照塔迪(Tadie),《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567页。】
以“贡布雷”(Combray)缩写名字部分为开端,外婆巴提尔德已不再接触社会。虽然并不似她那些以公开发表含蓄评论而闻名的姐妹们那么乖戾,她仍然是他的资产阶层教养严格维护者姨婆的笑柄。她那隐藏的残酷是叙述者自小就秘密而徒劳地蔑视的。[《在斯万家那边》(Du c?té de chez Swann),14页]尽管外婆并未像他想象的那样受到伤害。作为一个浪漫的大自然崇拜者,她的敏感远不在乎社会压力:她爱新鲜空气,甚至在雨中走,全然不顾沾泥的衣裾(《在斯万家那边》,12—13页)。她鄙夷正规的花园,她将植物与树桩分离,让它们显得更“自然”(《在斯万家那边》,16页)。对她来说,“别处的不为满足舒适与虚荣”(《在斯万家那边》,53页)的非世俗享受能产生艺术,她对这种艺术的爱也能达到同样的深度。
正因为外婆和叙述者的成长紧紧相连,这种非世俗性便与一种基本依附的无条件爱并存。事实上,她对他的健康和未来远比社会小事更挂心。作为《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第二母亲人物,她和叙述者的母亲同等重要。然而,以普鲁斯特典型的风格,表面是具有欺骗性的。小说早时有一个显著细节,外婆为孙子生日买书长途行走后疲累不堪(《在斯万家那边》,53页)。当时,她的疲劳似乎显示的是她的爱心,可是读者后来意识到这一定是她最后疾病的早期症兆。在普鲁斯特的情节和列文与他濒死兄弟经历的类比中,生死题材陡然闯入小说,可是此处它们为托尔斯泰孤儿主人公的缺乏父爱埋下了伏笔。
在《追忆似水年华》的下一卷中,是外婆而不是母亲陪伴他去巴尔贝克海边胜地,使叙述者少年时期不定的健康得以稳定。他们的房间相连,如遇紧急或不适应新房间,他可敲墙。尽管外婆如此保护他,叙述者却以外婆为耻,因为她和大旅店不相称,这旅店使列文在弗斯罗夫斯基身上意识到的“假日生活”态度字面化。不仅是少年期的不自然,这种尴尬也是叙述者进入世事时着迷的象征。之后,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全篇中,在托尔斯泰广泛展开的彼得堡三个上层圈子中,这种着迷将引导他在巴黎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徒劳地寻找个人专享的顶峰。
叙述者没有意识到即便外婆照看他的病情,她对自己的病却极力保密。此处照片一事至关重要。他外婆带着一顶华丽的宽边帽照相,她明显的虚荣使叙事者甚为吃惊—他将自己世俗的形象投向她:“我甚至在想我没把外婆放上太高耸的基座是不是真没误解她。”[《在少女花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500页]他并不公开拒绝,可是却补充了:“几句讥讽和伤人的话??其结果,假如我有义务看外婆高贵的帽子,至少我成功地在她脸上造出了那应该使我高兴的愉悦表情。”[《在少女花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501页]直到更晚以后,在第四卷才真相大白。当外婆过世后叙述者看着照片,女佣弗兰索瓦丝做了解释:“那天侯爵为她拍照,她拍得很糟糕,她得拍两次??然后她对我说,她说:‘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得有一张我的照片让他保存。’最后,她戴着那顶拉下的硕大帽子巧妙地站着,帽子竟连一点也看不见。”(《索多姆和戈摩尔》,237-238页)不是世俗的虚荣,而是怕孙子将来悲哀,这才是外婆心中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