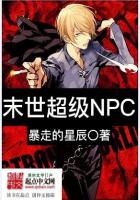二〇〇六年
黄凯睁开眼睛,眼前朦朦胧胧一片白色,还是这片白色,他已经住在这家疗养院四年了。
十年前所发生的那起恐怖事件,仍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却。这起事件曲折离奇,有时连黄凯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经历过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若不是亲身经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正是由于这点,他将事实真相讲述给别人听时,每个人都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主治医生认为这是黄凯精神错乱的病发症状。越是极力想说出真相,别人越是以为他疯了。为了在死去之前不留下任何遗憾,黄凯决定将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
十年前,在他和他口中那名来自地狱的男子之间,是否真的发生过常人难以想象的杀人案?
黄凯聘请了一位在调查事务所工作的人,来为他解开所有的谜团。这类人近似国外的私家侦探,干这行的人想法应该都很怪,对离奇的遭遇或许有独到的看法。曾经是一名侦探推理小说家的黄凯对这点深信不疑。
这所疗养院足足让黄凯疯狂了十年,十年来,他身边全是难以沟通的病人,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记忆中的恐怖经历会自动浮现在脑海中。
黄凯所在的疗养院,全称为“上海日辉精神康复治疗中心”,说穿了就是一所精神病患者的看护所,作为制度严格的疗养院中的一个病人,要会见外人是非常烦琐和困难的一件事。因此,黄凯必须有良好的表现,才有可能得到难能可贵的会面机会。只要不去触及那段会令他情绪失控的经历,黄凯与平常无异。假如并非真正的精神病人,要做到这点并不困难。
答应前来的侦探名叫左庶,黄凯从护士们的闲聊中,得知此人似乎小有名气。黄凯是经一位律师介绍才找到了这名侦探,左庶独自经营着一间调查社,不过对于调查社的具体性质、经营范围,黄凯一概不知,只知道他是有可能帮助自己离开这个疗养院的人。
约定见面的日期很快就来到了,黄凯的内心反倒有些忐忑不安。一位私家侦探接受一个精神病人的委托,会不会就是为了捞些油水?当然他并不是真正的疯子,所以,他的钱也不是这么容易骗的。
星期六的早晨,距离约定见面的九点还差十五分钟,黄凯提前到达了疗养院专供病人会见家属的接待大厅。接待大厅明亮宽敞,足有五十多个平方米,墙面仍是医院传统的白色,地面铺设了灰色调的大理石。整个接待室被磨砂玻璃隔板划分成了六个区域,每个相对私闭的空间内放置了两张桌子和几把红色靠背的折叠椅,一个区域可容纳两组家属同时探访病人。
他挑了个靠窗的座位,静静等候。
这家地处上海南郊靠近海边的疗养院,主体建筑是一座十二层高的白色楼房,从外形来看像是十二块从大到小的巨型积木堆砌起来,底楼的面积最大,每往上一层面积就逐渐变小,每层的渐变虽然不大,但对比顶楼和底层,差别就显而易见了。主楼外墙选用了光滑的材质,尽管白色容易弄脏发黑,不过每当雨过天晴之后,主楼则焕然一新,似乎在雨水中得到了重生。曾在疗养院居住过的一位文人,为主楼取了个贴切的昵称——“白塔”。白塔现代前卫的建筑风格,融入了中国古典的元素,活泼而不失典雅,严谨且不失变化,医院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止一次仰望这件富有创意的艺术品。
它的一楼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裙房,裙房两侧的尽头建有两个会堂,一侧是食堂,另一侧则是黄凯所在的接待大厅,它们由长长的走廊从内部和白塔相连。整个疗养院被包围在一片广阔的草坪之中。耐寒的绿草地上点缀着几只用于小憩的长椅。远处,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树木,透过茂密的枝叶依稀可见疗养院的“保护层”,两米多高的黑色铁栅栏。白塔正面由青石板铺出一条羊肠小道,石板路的另一边接壤着两扇精致镂空的黑色铁门,大门紧闭时,也将此地与世隔绝。门旁由纤维板搭建而成的简易值班室,住着尽忠职守的看门人。铁门外平坦的水泥马路旁,停放着几辆熟悉的汽车,每周的探访日它们都会在那里,百无聊赖的黄凯甚至能够熟练背下它们的车牌号码、车辆的主人,以及主人来探访的病人名字。
不知何时,黄凯的身旁坐下了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妇人,她不停向窗外张望,焦急等待着自己的探访者。每次有人走进会客大厅,她总会走出隔间看个明白,却总一次次失望地回来。
一位疗养院的护士来到老妇人身后,轻声对她说:“张阿婆,你的儿子打来电话。”
老人听到“电话”两个字,有些沮丧,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原本梳得服服帖帖的银丝,有几簇耷拉下来,感觉瞬间苍老了不少。任由护士搀扶着去接那通儿子打来的电话去了,不难猜出电话的内容是她儿子不来这僻远地方探望她的推脱借口。
老妇人急躁的情绪似乎影响到了黄凯,他低头看了眼手表,表盘上的两枚细针逐渐形成一个直角,他心里越发忧虑起来,会不会那个受委托人放弃了这笔业务?可能他在来的路上遇到意外或迷了路?当看门人推开铁门让进一个陌生男子,种种猜测都烟消云散,陌生男子彬彬有礼地与看门人交谈了几句,看门人随即伸出手指向接待大厅,男子微笑着摆手答谢,迈开轻松的步伐朝白塔走来。一路上他不安分地扭头左顾右盼,活似刚进城的农村人。
这名男子推门进来,不费力地找到了黄凯。
左庶看起来十分亲切,打扮得也较为随意休闲,耐克的黑色羽绒服配上条直筒裤管的牛仔裤,腰间束着根粗皮带,脚上踏着双蓝色帆布鞋,从微微发黑的白色鞋带以及磨破边的裤腿可以看出,左庶对衣着并不讲究。他虽然形象有些邋遢,但言谈举止间,仍闪现出睿智的光芒。
眼前这个头发蓬乱的男子,首先打起了招呼,“您就是黄先生吧!门卫告诉我,我要找的人严肃的就像国家领导人,我猜就是你了!”
“呵呵!”黄凯被逗得笑了起来。
“黄先生,你好!这是我的名片。”他随即递上了一张只印有名字和地址的名片。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庶啊!”腼腆的黄凯好不容易挤出一句坑坑巴巴的奉承话,一说完,就浑身不自在,黄凯虽然尽力装出健谈的样子,实质上,他是个脸皮很薄的人。
左庶笑了起来,可能因为听了夸奖双颊微微有些泛红,他和黄凯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搓着纤细的手指说:“不敢当,不敢当。如果可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主题吧!”
他的声音像具有魔力一般,让人心里感到踏实。黄凯调整了一下呼吸,鼓起勇气开始追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一九九六年
十年前,黄凯年仅二十四岁,居住在上海东区一个人口稀疏的小区内,整个小区是由九幢三层的老式合用公房构成,九幢房子每三幢一排,共三排,他就住在正当中的那幢房子的二楼。
随着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步伐的加快,上海的生活消费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上海人纷纷购置高档住宅,争先恐后搬出拥挤不堪的合用公房。黄凯所在的小区,绝大多数居民都是租房的房客,他也是这租房大军中的一员。
黄凯租下的房间约有十四个平方米,日常所需的简单家具一应俱全。这间房子拥有满意的条件,那就是宁静,这有利于一名推理小说家的创作。
因为整个事件发生在这幢房子里,所以有必要详细交代一下这房子的内部结构。走进小区你先会看到令人讨厌的绿化,绿色的植物被一层厚厚的灰尘所遮盖,它们的作用仅仅只是便于让人区分出这些一模一样的楼房来,每幢楼前栽种的都是不同品种的树木。走进楼道,先不去理睬一楼,沿着水泥阶梯向上走,可以看到楼梯上堆放的全是居民们用来抢占公用位置的杂物,破损残缺的家具、纸板箱、废木条,以及为了防止被盗而被主人扛到楼道上来的自行车。到达二楼首先看到的会是四只垂在墙上的破旧的电表,墙面污迹斑斑。向左转是一条狭长昏暗的走廊,走廊中弥漫着些许的臭味。走廊尽头的两侧是两间房间,靠左边是朝北的小房间,正是被黄凯租下来的那间。对面的房间约有二十个平方米,朝向正南,有充足的阳光,但价格比黄凯这间高出不少,这也是为什么黄凯选择阴冷北间的主要原因。走廊上装有一扇门,这里的居民通常称之为“总门”,总门内有厨房和卫生间,不过是由两个居室的居民共同使用的,这就是“合用公房”的基本解释。
由于是依靠写推理小说维持生计,所以收入并不稳定,可能某一段时间灵感降临,创作较为顺畅,稿费自然也丰厚,这段时间的日子自然会过得舒服一些。有高峰必然就有低谷,每当这个时候,房东先生就会无可奈何地对着他摇头。
事情的开始是在寒冷的冬季,黄凯正趴在陈旧的写字桌上冥思苦想着创作题材,他正陷入不幸的创作低谷。从窗外望出去,用来填充楼房间空档的植物都已经光秃秃的,这样的绿化起不到任何美化的作用。种植植物的潮湿的烂泥巴,反而会在夏季成为“四害”滋生的场所,周围的居民深受其害。房间和走廊里经常会有老鼠、蟑螂出没,大胆的老鼠甚至曾经咬烂过黄凯的手稿,因此他特意养了一只白色的小猫。
“咚咚咚!”有人在敲房门。那一定是房东先生,因为除了他没有人能够打开总门直接来敲黄凯的房门。
开门一看,果然是他。房东先生对黄凯说:“小黄啊!你准备一直在我这里白住下去吗?”
“再等一段时间吧!最近我手头紧。”黄凯十分不好意思,却实在拿不出房租来。其实平时在黄凯经济宽裕的时候,也不在乎多给一些额外的租金给房东先生,因此房东先生在支付租金的期限上也没有非常的苛刻。
房东无奈地笑了笑,逗起黄凯那只乖巧的小白猫来,看得出来房东先生十分喜欢它。
黄凯的房东先生姓房,所以常常有人取笑他天生就是收租的地主。房东先生在这个小区住了一辈子,因为舍不得这块故土,所以一直就住在黄凯所租房子的楼下。也有可能是他嗜赌成性,家中根本无力购买其他房产。再加上家里有个宝贝的小儿子要养,房东先生对儿子有求必应,自然不会有什么积蓄。
房东今次上楼来的主要目的,不是特意来催收租金,而是整理打扫对面那间闲置的屋子,听房东说有人已经租下了这间昂贵的房间。
“租房的人有些怪怪的,连房间都不用看,就先付了半年的房租。”
“是个什么样的人?”黄凯有些好奇。
“听他自己说,好像是一个画画的。我也只见过他一次,那个人不太爱说话,看起来不太好相处。小黄,你最好别去招惹他,因为我可不想同时失去两个房客啊!”
房东先生这么说的真正意图,无非是不想让房间空闲下来,以免造成他的损失。
房间空了一段时间,所以有不少的灰尘,不过新房客不需要太多的家具,所以房东先生让黄凯帮着把家具拆卸后搬去楼下他的房间。简单扫了扫地,清扫了显著位置的蜘蛛网,清洁工作就算完成了。
“小黄啊!这间屋子的门锁有些小毛病,你有空记得帮我修一修!”有些疲惫的房东先生交代完后就回了家。
第二天清晨,黄凯就被一阵喧闹声惊醒,走出房间一看,对面的房间已经摆放了不少的东西,这些物品昨天还没有看见,显然是房东所说的新邻居刚搬进来了。
“小心一点,别把大衣橱的镜子弄破了。”几名搬家公司的工人正设法将一个大衣橱抬进狭小的总门,一名瘦瘦高高的青年男子用命令的口气对工人们说道。
黄凯心想,应该先过去打个招呼,毕竟往后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合用一个厨房,共用一个浴缸。
“你是新搬来的吧!欢迎你,我就住在你对面,以后大家互相有个照应。”黄凯客气地说道。
这个男子却毫不理会,他的眼神中充满着蔑视和漠然。正如房东所说的那样,这个人的确不太好相处。
当工人们将全部的东西搬放妥当后,他才从昏暗的走廊走进了房间,男子约略长黄凯两三岁,身高一米八左右,比黄凯高出将近半个头,体形偏瘦,穿着一套合身的黑色西装,脚上的黑皮鞋锃光发亮。削长的脸型配上略微有些卷曲的长发,一双细长的眼睛流露出来的全部是冰冷的眼神。虽然听说他是画家,但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更像是一个杀手。
由此,这个人走进了黄凯单调枯燥的生活里,而他的一生也将永远改变,变得暗无天日。
作为推理小说家,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时常处于窘迫的境地。但黄凯并没有就此打算放弃,因为当自己的作品为他人所津津乐道时,这种快感实在让作者难以自拔。陷入灵感滞塞的他,需要通过接触其他事物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便灵感的产生。而一味坐在书稿前,只会令他走进创作上的死胡同。新搬进来的这位奇怪男子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因为是合用的住房,一天之中难免会在厨房或卫生间碰见几次,久而久之邻居的一些举动引起了黄凯强烈的好奇心。
“今天的天气真糟糕啊!下那么大的雨。”黄凯故意走进厨房,搭讪道。
奇怪,男子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继续煮他的方便面。
“你是画家吗?我认识的画家不多,除了达?芬奇之外就叫不出几个名字了,你叫什么名字?”黄凯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又问道。
“鲁坚!”奇怪男子突然回答了黄凯的问题。
“我叫黄凯!虽然我不懂绘画,但还是希望有机会能欣赏欣赏你的大作。”黄凯奉承道。
听完黄凯的话,鲁坚眼睛一亮,听到有人要欣赏他的作品似乎显得很得意,“现在就让你看吧!”他急忙关了火,也不管他的方便面了,径直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原以为很难接触的他,想不到这么快就搭上了话茬,黄凯紧随鲁坚走进了他的房间。
房间的窗帘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室内光线暗淡,只点了一盏橘红色的小台灯,感觉十分温馨。家具毫无秩序地靠墙排列着,墙壁上到处挂着破旧残缺的石膏像,地上全是油画颜料和画笔。木制画架摆放在房间的正中央,一幅还未完成的肖像油画搁在上面,近视眼的黄凯粗略地扫视了一遍这幅画,画面中是一位眉清目秀的美女,一头靓丽的长发,表情中有种难以名状的哀怨。为了仔细地查看一番画中的女人,黄凯不得不前倾身子凑近画板。
突然鲁坚拉开了厚厚的窗帘,光线一下子刺射进了眼睛,黄凯连忙用手遮挡强烈的阳光。一旁的鲁坚却躲在墙角边微翘着嘴唇,笑眯眯地盯着黄凯。
为何大白天要拉上窗帘?他就像吸血鬼一样惧怕阳光。这只是他身上众多谜团之一,更令黄凯感兴趣的是画板上的那个女子,这幅画显然还没有完成,但可以看出构图的角度十分别扭,作画的人像是趴在地上画的,为什么要选择如此的观察角度呢?这个女子正遭受着什么苦难,会有这般令人不安的神情。
不等黄凯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鲁坚便说道:“你的猫似乎饿了。”
外面果然传来小白猫的“喵喵”声。不知为什么,鲁坚刚才那股热情劲似乎已消失殆尽,自顾自地忙碌起来,就连黄凯离开都不加理睬。
专职作家的生活只能用无聊透顶来形容了,除了写作之外,唯一的消遣就来自于那只小白猫了。一个人终日与动物相伴,不得不承认是一种悲哀。即便如此,黄凯也不愿回到父母的身边,因为彼此之间亲情淡薄,只剩下了争吵。他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勉强挤在同一个屋檐下,为的只是得到“亲人”这个称呼。
黄凯很不喜欢住在对面的这个自大的家伙,他的傲慢令人厌恶,除非被人用枪顶住脑门,否则黄凯无论如何不想再去答理这位新邻居了。
但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如何违背意愿和鲁坚成为朋友的,更不知这不可思议的友谊是这个男人可怕计划的一部分。
一天清晨,恼人的敲门声伴着房东先生洪亮的嗓音,不时还有金属摩擦门板的刺耳声。
“什么事啊?”黄凯非常不情愿地起床开了门。
房东先生的脸上已经不见了昔日的亲切,转动着无名指上那只硕大无比的方戒,刚才的金属声正来自于它。
“你的房租已经拖欠三个月了……”虽然房东先生没有说出下半句话,但黄凯明白这是最后的通牒了。
黄凯只得摆出一张苦瓜脸,“请您再宽限几天……”
不等这句讨饶的话说完,房东就坚决地打断了他,生怕被打动似的。
这两个人的眉头一个比一个拧得紧,相对而视却都默默无言。一个是身无分文却想长住的房客,一个是依靠房租过活的房东。房东先生没有工作,他的经济来源就是他楼上的两间房间,以黄凯对房东先生的了解,不是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他不会如此逼债。虽然他态度强硬,摆出了六亲不认的架势,可还是稍稍让了步。
“三天之内,你要么交出欠我的房租,要么自己卷铺盖走人。”说完他掉头就走了。
房东先生就是这么个势利的中年人。在黄凯手头宽裕的时候,房东先生从来没有用这种态度对待过他。
也许房东先生是个好人,但不是善人。
创作素材和灵感的匮乏,对于目前的黄凯无疑是一个危机。
三天的时间无情地流逝着,很快到了最后期限。在这期间,房东先生为了表明他不可动摇的决定,甚至还带了一名租客来看了看仍属于黄凯的这间屋子,为此黄凯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黄凯眼下需要的是金钱而不是火气。
第三天,房东先生准时而至。他这次与平时不同,连门都没有敲就直接闯了进来,态度的转变几乎不加掩饰,无疑这是驱赶寒酸房客的必要“素质”。
“现在你马上离开我的房间。”房东冷酷地命令道。
黄凯明白恳求是浪费口舌,只得提着行李走了出去,小白猫也很有骨气地跟了出来,它没有理会房东先生。
“把你的东西全都带走。”房东先生对着门外挥挥手,表情显得很凶狠。
“这些东西或许可以能挽回一些你的损失。”黄凯留下了自己随身物品中最值钱的几样东西,一支笔头镀金的钢笔,一个随身听还有他仅剩的几十元钱。这些虽然不够偿还拖欠的房租,但至少可以为黄凯保留一个作家的尊严。
房东先生很坚持,他侧身站到门旁,潜台词就是要黄凯回去把那几样东西都带走。他还加了一句,“这些破烂玩意还得我浪费时间去丢掉,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黄凯愤怒地收拾好那些东西,小白猫却被黄凯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耳朵直直地竖起着,显得很警觉。
房东先生走到它面前,蹲下发福的身躯,伸出右手安抚着小白猫,小猫也温顺地摩挲着他粗糙的手。
小白猫的小小背叛,让黄凯不禁有些气恼。他抱起猫放入包中,无情地粉碎了他们之间的友情。
房东先生递来张百元大钞,“给猫买点吃的,看它瘦的。”
“不需要你的施舍。”
“又不是给你的,这是给我朋友的,拿着!”他把钱塞进了黄凯的口袋,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冷酷,仍然让人憎恶。然而,黄凯感觉到一股甜甜酸酸、说不明道不清的液体在心中涌动。不可否认,房东先生的这一举动融化了先前他插到胸口里的那把无情的刀。不过为了面子,黄凯坚决不接受。
就在两个人争执推让之时,鲁坚的房门打开了。他显然对正发生的事情已十分了解,一身正装的他走到两人当中,狭窄的过道顿时拥挤不堪。鲁坚掏出了一叠百元大钞,交到房东的手里,淡淡地说了句,“我先替他付了。”随后,他又重新回到他的暗室中,关上了房门。
从鲁坚开门到关门,黄凯和房东先生自始至终都注视着他,就像在看他主演的舞台剧。片刻寂静之后,我开始怀疑刚才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梦境。不过那叠钞票实实在在地装在了房东先生的口袋里。
这场风波就此平息,房东先生又变回了以前那样的和蔼可亲,鲁坚所付的这笔钱使得黄凯和房东先生和好如初,金钱的力量的确惊人。其他一切与往常无异,只是黄凯的债主变成了隔壁的画家。
黄凯并非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但除了自己的小说之外,家里也确实没有可以作为礼物的东西。于是他捧着一套自己的小说,敲开了鲁坚的门。
黄凯有些手足无措,支吾了好一会儿,始终不好意思开口说出感谢的话。而鲁坚似乎刻意刁难,他一言不发,眼神流露出对言谢的渴望。
“这是我的小说,送给你。”看着他的眼睛,不知为何,黄凯刚才对他的感激之情就荡然无存了。黄凯忽然非常不愿意让他明白这笔钱对于自己是多么及时的一场甘露。
他接过书,同时冷淡地说了句,“请进。”
尽管讨厌这个人,但黄凯并不讨厌他的画。
那画中的女人到底是谁?黄凯一直想弄个明白。在角落里坐下来,他抬头望着墙上的那些画,惊讶地跳了起来,因为房间里所有画的都是同一个女人,同一个仰视角度,几乎可以说每幅画都是一模一样。
“我有一个不错的故事,你看看能否写成小说。”鲁坚冷不防地说道。
黄凯把目光从画布移到了鲁坚那张严峻的脸上。
作为一名作家,收集必要的写作题材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不知道他的故事是否能写成侦探小说,但还是很乐意听一听。如果这位债主的故事难以入耳,就权当是付给他的利息吧!
有了一位忠实的听众,虽然只是看上去很忠实,鲁坚显得很高兴,语气温和地表达着感激,他撩了撩裤腿,一屁股坐在了脏兮兮的地板上,不时拉几下耳垂,摸几下鼻翼,待故事在胸中酝酿成熟之后,鲁坚开始叙述起他的故事来。
鲁坚是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为了方便读者朋友们的阅读,之后黄凯以第三人称叙述此故事,并稍做修改,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语句。
在两年以前,鲁坚被丘比特之箭射中,他爱上了一名女子,并且展开了疯狂的追求,那位纯真的姑娘很快投入了他温柔的怀抱。两人如胶似漆,如同蜜蜂寻找到一株花蜜充硕的鲜花,彼此享受着爱情带来的喜悦和甜蜜。有过热恋经验的人都体会过触碰爱情时身心的无比欢畅,此种感觉美妙而难以形容,此种感觉流淌进每条经脉中,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他们俩在迷人的外滩夜景下情意绵绵,情人节你侬我侬互赠礼品,做的只是一些普通情侣都做的事情,看似无奇的行为引发的却是两颗炙热心灵的碰撞。不觉乏味地诉说着讲了千百遍的山盟海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它能让一个理智的人变得疯狂,能让懦弱的人成为勇士,能让人死去活来,能让人如入天堂,能让人肝肠寸断,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不过对被爱情抛弃的人来说,它无疑又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
故事以鲁坚独有的节奏缓慢发展着,黄凯有些不耐烦了,鲁坚不停重复那个女人对他说过的话,每说一句,就越陶醉其中。这类似老太婆发牢骚般的故事丝毫提不起别人的兴致,而且故事也并不好听,他爱重复自己的话,这更让故事变得乏闷冗长,爱情虽然是个永恒的话题,可它不能为黄凯的小说赚到一毛钱。鲁坚掩饰住了对听众的不满表情,可能对他来说拥有一位听众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可惜,黄凯对爱情一无所知,他所说这些,就好比向六岁的孩子解释什么是哲学一样。
“抱歉,我只会写侦探小说,你的故事……”一时黄凯想不出能够婉拒他的词语,只是不断重复着“你的故事”四个字。
鲁坚突然停了下来,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黄凯身后的某样东西,表情如此愤怒,以至于吓了黄凯一大跳。
门口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引发这个男人的不满?黄凯回头一看,小白猫正在他的门板上勤奋地练着爪子,破旧的门板“啪啪”作响。
“看来它是找我来了!”黄凯温柔地抱起猫,为它的行为解释道。
鲁坚皱着眉头从地上起来,用冷冰冰的口气说道:“我整理整理思路,再讲给你听。”说完,就拍拍他全棉的西裤,直至黄凯出门也没抬头看一眼。
小白猫的及时出现为黄凯解了围,黄凯将仅剩的一根火腿肠丢进它的餐盘作为了奖赏。
很难想象这个冷酷的男人热恋时的笑脸,他的嘴是甜言蜜语的禁地,黄凯对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听别人杜撰出来的故事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这次淡薄的交流,让黄凯和鲁坚都初步熟悉了对方,在彼此心目中,双方都没有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朋友,尤其是黄凯对鲁坚的性格极其反感,可又对他的神秘抱有几分好奇。相信鲁坚也一样,一边讨厌着寒酸多嘴的邻居,一边又期望拥有这样一名听众。这种微妙的依赖关系的存在,才得以让两个互不顺眼的人和睦地生活在一条走廊内。
就这样,黄凯又重归到自己单调的生活中,写着被读者公认的三流侦探小说,与小猫为伴,虽然穷困却暂时不必为房租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