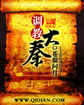漓裳怔怔地望着予澈。
从容轻浅的声调,淡定怡然的神色,说到紧要处,如墨的眸底不时有璀璨的光亮流转盘旋……
命悬一线,生死未卜,仿佛都是别人的故事,与他一点瓜葛也没有。
“阿漓,你知道吗?我真希望我的阿漓永远不要长大!永远像现在这样蜷缩在我的怀里!永远不要看见人性里最丑陋、最贪婪的一面!可我的阿漓已经长大了,长大了,就必须明白一些道理。”予澈修长的手指摩挲着她的下巴,郑重地道:“阿漓,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看一件事情,是不能只从表面的现象来判断或决定的。勤俭廉,真善美未必是觉悟的表现。用心去倾听,也未必能辨别的出其中真伪。所以你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所谓‘事实’都未必是真的!永远不要轻易相信它们!”
漓裳的心头顿时一紧,“王爷说的是……”她的眸光掠过起伏的帐幔,屏息静听了片刻,确信外面没有动静,方才压低了声音问:“……皇上吗?”
予澈的目光落在了不知名的所在,迷离而恍惚,“是,也不是。”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贪婪和趋吉避凶一样,都是人的本性!就像那土包子为了钱财偶施善心,一旦发现有危险,立刻又向我举起了刀。可我依然感谢他!没有他的偶施善心,我此刻已和九弟一样,早成了冢中的一堆枯骨了……”
漓裳听出了他在避重就轻,对于予涵那样的伤害,他面上虽然一如往昔地淡然无波,心下终是难以释怀的吧。
“予澈不会死的!予澈会长命百岁,一辈子陪在阿漓身边的!你刚刚才说过的,再不会丢下我了!”她纤弱的食指压上他蠕动的唇片,不忍心再去触摸他心底痛彻心扉的伤疤,“王爷,我们走吧,好不好!?”
室内的气氛忽然变得寒冷肃杀起来,连窗外的几竿翠竹仿佛都受到了感染,竹叶青青,正是生机勃勃的时候,却已纷纷挑落枝头。
予澈摩挲着她肩膀的手指明显颤抖了一下,眉心猝然凝集,低涩的声调压制她的耳边,几近耳语道:“阿漓,我们……我们怕是走不了了……予涵,不会放过我的……不会……”
“阿漓,你知道吗?我并不舍得六弟死!从不舍得!可我知道,六弟的心大着呢。胸藏百万兵,收发自如。南齐的山峦丘壑,万里疆土都深埋在他心底最隐蔽的角落里。即便父皇在世时对他层层打压,众兄弟亦不怎么待见他,他一样锋芒毕露,掩过我们所有人的光芒!”
予涵说着话时,激昂的语调里透了说不清的痛惜,嫉妒,憎恨……
他说,有予澈在,他的梦想永无施展的空间!
他说,帝位与他是志在必得!
他还说,他不知道,如果失去了梦想,还有什么可以支持他活下去!
……
她信!她信予涵一定做得出来!
“予澈,我们怎么办?”漓裳死命点头,孩子一样地在予澈的怀里嘤嘤哭了起来,“我不要你死!不要你离开我……予澈……”
予澈勾唇一笑,俯身吻了吻她的唇瓣,“傻丫头!我已经回来了,就不会死了!我去鬼门关上溜了一圈,阎王不肯要我!他老人家还让我带话回来呢?”
漓裳见他有了开玩笑的意趣,心下稍稍放松,抬起头问他,“什么话?”
予澈端起床头几案上早已凉透了茶水,微微抿了一口,似笑非笑地道:“阎王他老人家说,虽说予涵政务繁忙,但他还是希望予涵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看看他!”
漓裳震惊地说不出话来,耳边萦萦绕绕,充斥着的尽是予涵的冷笑声。
你以为你很了解六弟!?
你以为你很了解男人?!
……
她忽然发现,她与他抵足交缠,相融相合,却远不如予涵了解他。
怔愣了很久,漓裳恍恍惚惚地开口,“予澈,你想做皇上吗?”她问的直截了当。
予澈的回答亦是不假思索,“想!做梦都想!”
一语成谶啊。
终究还是男人比较了解男人!
璀璨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纱窗透漏在光可鉴人的地砖上,流光在房梁上流转荡漾,晃荡的眼前一阵迷茫。
予澈捧起了她温婉秀丽的小脸,目光如曜,射的她几乎睁不开眼睛。
“阿漓,我要你!也想要这大齐的万里江山!”他坚定的目光透过重帘翠幕,探向南齐的锦绣山河,“阿漓,经历了生死,我才明白,儒雅俊逸,淡漠明智,兄友弟恭,亲情友情……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假的!只有权势才是真的!没有大齐的万里江山做依托,我连心底最后的一丝温暖都呵护不住!”
予澈的话--
句句在理!
句句属实!
予澈和予涵……
他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死去的话——她只能选予涵了!
尽管如此,漓裳的眸中依旧抑制不住地悲戚绽放,“那我呢?我也是假的吗?”
“傻丫头,你就是我心头的最后一丝温暖啊?!”予澈忽然仰起头,自嘲地笑了,“其实,我也只是说说,皇位更迭,权利交割,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予涵施政灵活,颇得民心,政权日益巩固,再动起干戈来,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啊!?”
“也许,我的英雄梦,永远都只是一个梦想。”他叹息,“谈什么英雄?谈什么梦想?今晚睡下了,还能不能见到明早的太阳,全在予涵的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