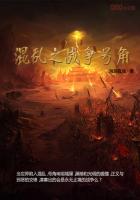红军是所大学,八路军也是一所大学,投奔八路军、延安的青年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革命的大学来了。毛泽东曾说过:“延安就像所革命大学。”《新民报》主撰赵超构1944 年延安一行后,也得出了“整个延安城都是在那里学习”的观感。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涌来的人们,一进入这所特殊的“大学”,就会感受到浓浓的学习氛围。
干部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干部的素质,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对于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当时,共产党的干部大量出身于农民和工人,文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文盲,这一教育背景严重制约了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时事政策的掌握与运用,很难适应抗日民族民主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要求。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十分重视,将干部教育工作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写作最丰富的时期。他在百忙中集中精力系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十余种著作,《鲁迅全集》,蔡东藩的《中国历史演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还有许多古书、诗词。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大量有名的著作。
据统计,《毛泽东选集》(1 ~ 4 卷)所收的158 篇文章,有112 篇是这一时期写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收集的372 篇,有142 篇是这一时期写的。他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有关学者一起,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同时,毛泽东还提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夸夸其谈、瞎子摸鱼、粗枝大叶的学习,并号召进行全党的学习竞赛。这样,延安的所有新老干部,都懂得了自身的价值和所肩负的繁重革命任务,掀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学习热潮。
一部分干部脱产进入干部学校专职学习。干部学校主要集中在延安,有中央党校、
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
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党也创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较著名的有抗大分校、华北联合大学、苏中公学等。各校配备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如在培养干部的“重工业”抗日军政大学,就有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何长工、王智涛、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知名人士任教。
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领导人也经常到各校做报告。大量投奔延安的有志青年也多数进入各个学校学习,接受这个革命大熔炉的锤炼,被培养成干部队伍的后备军。大家都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当时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的陈辛火这样深情地回忆:“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上、在树阴下的空地上上课。就是在1938 年11 月20 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一个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图书也不多,每月发的一点有限的津贴费差不多全用来买了书。只要新华书店到了新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那时夜间照明条件很差,可是大家读书认真。晚上一般用空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有时还用老麻籽油点灯。光线虽然不够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那时我们的背包很简单,几件衣服,一条薄被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却鼓鼓囊囊地装着好些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行起军来,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就是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也舍不得1938 年,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在户外上课。
丢掉一本。”
进入学校专职学习的干部毕竟有限,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其岗位上,边工作,边学习。文化低的乡级干部,主要是提高文化水平,以消灭文盲为主;文化程度较高的高中级干部,要学习理论。有的地方还制定了细致的学习制度和学习内容。如陕甘宁边区,各县在乡一级成立在职干部学习小组,由乡长任组长。依文化程度(不论职位)分为初、中、高三级:文盲或半文盲的在职干部为初级,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为中级,初中毕业以上程度为高级。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种学习以文化学习为主,其余为辅。业务学习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进行;时事学习,以自己阅读报纸为主,并请人讲解;理论学习,以调查研究入手。在学习制度上,坚持每日2 小时;半日校、夜校或补习班,每周至少上3 次,每次2 小时;实行成绩考核,分为日常考、临时试验、学期考试、毕业考试等,确立优劣,给以奖惩。在职干部学习的热情很高,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显著提升。
一些民众也在积极学习文化。共产党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成人文盲和失学儿童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好条件。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首要的工作便是开办针对成人文盲和失学儿童的成人小学和儿童小学,并力图培养受教育充分的教师来广泛地、迅速地传播一切有益的知识,而中国低层民众十分渴望接受哪怕最起码的教育,因此,共产党大得人心。
识字组、夜校、半日校、民众教育馆和黑板报是人们日常的学习形式。识字组以当地识字的人为中心组成,既识字,又学时事政治,还可以进行生产和日常知识的学习。晋察冀边区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佳话:唐县某村婆媳两个都是该村妇女识字班的学生,可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总需要留下一个人看家,烧饭洗衣,拾掇缝补。于是媳妇让婆婆去上课,要自己留在家里干活,婆婆说年纪轻的该读书识字,年纪老的要留在家里做事。最后还是媳妇挠不过婆婆的好意,于是就拿起课本抱起孩子去上课了。
“妈,等我回来,再教给你!”就是这样,婆媳两个都识了字。民教馆类似现在的图书馆,备有书报,发行刊物,组织演讲,举办各种文化展览等。群众还创造了冬学这种突击性的学习运动。冬学就是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文化教育活动,重点是扫盲。在各根据地,没有堂皇的教室,随便一间房子,一座树林,一片河滩,或是山坡,或是山顶,所有的工作场合,随处都是人民的课堂。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也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抗战,而且还认识了他们自己,了解了自己的力量。
到1939 年底,晋察冀边区冬学增至5379 个,入冬学人数由上年的18 万人上升到39 万余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冬学运动总结摘要》,《新中华报》1940年6 月11 日)。据1941 年晋绥边区神池等19 个县的统计,共开办冬学3116 处,学员达17 万余人,其中妇女约占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还普遍推行一种“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是指一些识字较多的小学生,特别是完小的高年级生,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教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识字,为家人读报,在自己家的附近或本村,组织识字组,教识字组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延安是“红色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学习风气最浓厚的地方。在那里,谁要是有一本好书,得到一支钢笔,就会成为周围同志十分羡慕的事。延安许多生活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抗战时期到过延安的德国友人王安娜这样说:“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的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尼姆· 韦尔斯则看到,“在延安,夜校随处可见。一天辛劳之后,泥水匠和学徒工、商人的儿子和贫苦的农民,都认认真真地坐在桌前学习读书写字。中国现在新旧两种文字都有,可老百姓大多愿意他们的孩子学习旧文字。”干部、战士、学生、民众一起,汇成火热激情的学习潮流。而坚定的理想信仰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理论文化的兴趣,是他们学习的不竭动力。
公司能否也像一所学校?当然,今天已不同延安时期,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专门抗大学员在认真阅读政治课本。
院校,负责培养各行各类专业人才,但不同的企业、团体,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提倡每个员工不断学习并形成风气,这还是需要的。
事实上,提倡学习就是弘扬正气,把员工的思想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一个人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是有限的,必须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进行再学习,许多劳动模范、技术能力都是在工作中努力学习的结果。公司、企业组织必要的学习,将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一定的投入必然带来一定的回报,那种“榨油式”的用人方式,把每个员工严格固定在工作机器上而始终不给“充电”,显然是一种短视,最终导致企业缺乏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