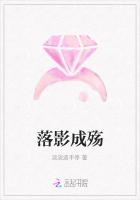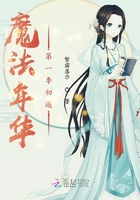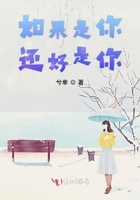本书作者张维舟先生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这个希望出自渗透历史感的情义,我是无从推却的。因为我和本书主人公芦甸,不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诗友,在中国野生自由诗的荒原上一起歌唱过、奔跑过的同龄人,而且还是接着50年代的难友,建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桩涉及成百上千文化人的冤假错案的同案人。
关于芦甸的一生,他当年如何离开舒适的成都,投奔艰苦的中原解放区,又转战晋冀鲁豫,如何在建国以后来到京津从事文化工作,并为新中国热情歌唱,不久即陷入意想不到的灾难……关于这一切,读者将会在本书中找到翔实的叙述和持平的评议。这里我只能就上述我和他的两层友谊,表示一下我对他的怀念。
作为诗友,我首先想说,当年我们都很年轻,对诗都有着年轻人才有的爱好与追求,尤其是芦甸,他为人真诚,这种真诚并在诗中得到了清澈如水的反映。在20人集《白色花》中,他的《沉默的竖琴》是他1943年走向战斗前对亲爱者的临别赠言,“愿花朵属于你,荆棘属于我”;《大海中的一滴水》是他在1949年全国解放的忘我的兴奋中,以“人们只看见天际的碧蓝,看不见我”而自豪的见证;《我活得像棵树了》写于1952年灾难隐约袭来之际,他觉得自己没有被“外来的风暴吹折”,没有被“冰雪压倒”,却被“一些被虫蛀空了的树”“重重地击伤”,以致当他努力“弹起全身去反拨”时,竟意外地“听见身边也有轰然倒地的声音”。……这些情感、情韵和情操,在历史老人的眼里,虽然显得有些天真,但由同龄人们看来,却鲜明地反映了他和他的诗友们当年所共有的对人生、对时代、对历史的真诚。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些诗,想必也不会在作者和自己之间感到什么隔膜吧。
另一方面,作为难友,我又不免要说,这种对人对己的真诚,虽然在诗中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拿到实际的复杂的生活中来,可就难免惹出怎么也躲不脱的灾祸。本书将会写到,芦甸正是胡风先生当年身边少数几个“热心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友人之一。50年代,他由于肯定胡风的文艺观点,同情他的被边缘化的处境,并明确认为,胡风问题的关键在于少数人的“宗派主义”,最终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党中央,他才日益接近胡风,直至最后参加了“三十万言”的草拟过程。他一再说过,“胡风问题的合理解决,不但符合胡风本人的期望,对党、对人民的文学事业更是有益的。”这些主观思想情况,当年在审讯员面前,作为“交代”讲出来,自是不老实的“狡辩”,是绝对通不过的。我作为同案人却可以证明(尽管当时也被认为“不老实”),那些思想情况是真实的,是符合芦甸的性格实际的。
1965年(10年以后),我和芦甸曾经见过一面,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我问他,今后还写诗吗?他说:“当然还写。不过,更想多读几本马列,看看自己过去究竟怎么错了。”话不多,却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当时的精神面貌。诗在他是怎么也不能放弃的,这可谓“本性难移”;至于他自己(也就是我们)所犯“错误”的原因,看来他虽已不再坚持上述1955年以前的一些认识,但对那些“批判”、“声讨”、“材料”、“编者按”之类,私下显然也并不以为然。
芦甸和他的难友们原来对于胡风事件的前因后果的认识,与事后多年发现的真正的历史实际相比较,充其量只能说是皮相之谈;至于上世纪50年代那些家喻户晓的定案依据,其远离真实而不能说明问题,就更是自郐以下了。胡风事件为什么会产生呢?只有经过几十年类似事件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归结,即缺乏社会主义法制所不可缺乏的言论自由这个基本公民权。可叹的是,这点今天看来不过是常识的认识,不但当年法庭上的公诉人不认识或不得已而“不认识”,连被起诉的“莫须有”的受害人们也都莫名其妙,有如被催眠一般,被困在公诉人的思维逻辑之网里,即令少数几个例外者的清醒的声音,也无不被压灭在铜墙铁壁之内。这就是说,当年或可避免胡风事件发生的唯一良方,只能被发现、被认识于几十年后的今天,却不是当年促成胡风事件的社会进化条件所能提供的:一系列悲剧之所以不可避免,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芦甸逝世于1972年。他是从1955年起被监禁10年以后,又被送到一个继续改造的环境,自觉自愿地从事超体力劳动,以致脑溢血而亡。他不但在毕生钟情的诗歌领域没有实现基于自己的潜力的志愿,也没有熬到1980年代初期的“平反”,更谈不上到新历史时期才能有的自我证明的机会:这是令他的在世的难友们扼腕叹息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几十年之后,人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严重的胡风案件毕竟平反了,加在芦甸及其难友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毕竟取消了,整个人文环境也比当年宽松多了,精神劳动的成功几率也更有保证了———芦甸九泉之下有知,当会深感欣慰吧。
本书作者为了写这本评传,多方搜集资料,反复修改原稿,终于将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一位诚挚的诗人和一位不知疲倦的真理探求者的面貌,重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这是值得感谢的。我庆幸有机会写这篇小文,同时也为亡友作为评传的主人公感到高兴。
2003年2月5日
本书指《芦甸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