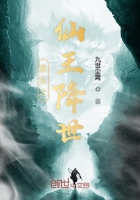我一路在摆渡人的船上不禁还是有些疑虑,白泽巡视忘川,守护封印,六首蛟再出现,自然该他出手料理。可这六首蛟怎么会突然出现?莫非是当年的漏网之鱼?这倒也不无可能。又或者真的是封印出现了问题?还有白泽这小子,往日见了我虽也是这张面瘫脸,不过似今日这般无礼倒是少见。他似乎很不想我从六首蛟嘴里问出些什么。这小子莫不是怕我问出什么,笑话他守护不力在更染面前失了颜面?
“大人在想什么?”摆渡人问我。
“没什么,小心你的船篙,戳到水里的鷒鱼了。”我提醒他。
“鷒鱼肉质鲜美,无论蒸食或是熬汤都极好,要不我网上来两条,给大人拿回望乡台享用?”
“多谢宋公子,着实不用。”
“大人,您唤我什么?”
“你不是姓宋吗?我唤你宋公子,有何不妥?”他沉默片刻,道了声:“多谢大人。”道谢后还是说:“我这便下网,到了望乡台定能网上几条。”
我叹气:“想来你是不知道我的手艺,不过是糟蹋了你的鱼。不然我也不能回回嘴馋都得到处蹭饭。”说起来我也并非没有在这上面花过心思,早些年给一个厨娘烧过茶,看到了她在彼岸的一世,别的尚且不论,她那一手厨艺着实让我眼馋,便托了摆渡人网上来几十条肥鱼,凭着惊人的悟性和逆天的记忆力煎蒸煮炸样样齐全。可无奈味道着实不济,偏偏我那时候又是个死心眼儿的性子,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味道不济可到底是我一番心血,可我着实对自己狠不下心,下不了口,但对旁人便无此顾虑,于是悉数赏了我的坐骑。
那时候我的坐骑还不是现在的毕方,而是方才出手的玄衣青年白泽。他原是鹿吴山的一只蛊雕,因长相威风我追了他六七十年这才成了我的坐骑。说来着实丢人,在此岸要有自己的坐骑,非得有几分本事降得住他不可。我自知是个没本事的,又实在想耍这个威风,于是使出诸多手段,软磨硬泡这才得逞。
他倒颇为尽责,个性虽冷漠些,却是但我所命,无有不应。如此过了三万年,却硬生生被我的厨艺逼得离了望乡台。他把给我网鱼的摆渡人打了一顿,再逼着他们喝光了我的鱼汤,最后自个儿也走了。临了只让三青鸟给我留了句话:
于人安康于己安康,还请大人别再下厨了。
我痛失坐骑,得了教训,自此后便真的没再下过厨。不料白泽离了望乡台不久,便成了更染的坐骑,更染是我姐姐,亦是三生石的主人。他大爷的白泽,老娘养你三万年,离开我没俩月你就另寻它主了,还勾搭上我姐,这让我好没颜面。如此气不过,便打上门去了。那时我还是个草包,见惯了平日在望乡台冷心冷脸的白泽,陡然看到他低眉顺眼,正在更染的院子里给为她架秋千,一时愣神,略略有些泄气。
“喂,你为什么弃了我而随了更染?”我问他。
“你做鱼太难吃了。”他面无表情。
“难吃你跟我说啊。”我苦口婆心。
“说过很多次。”他继续面无表情,“我说煲汤难喝,你便蒸了吃,我说蒸了也难吃,你便红烧,最后不得已切了鱼片儿生吃,生吃倒也罢了,你那五味杂陈五颜六色的蘸料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
“呵呵……”往事果然不堪回首,我尴尬了一下。却见一旁的更染一边喝茶一边瞧她的三生簿子,半点搭理我们的意思都没有,转而道:
“那更染有什么了不起,她顶天了也就只会做个面饼子。”
“她做的面饼子挺好,而且,她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就挺好。”好你大爷,我在心里骂。“哦,对了,我记得你那里还有好些竦斯蛋和精卫鸟蛋,与其留着给你糟蹋,不如拿些过来,摊了可以卷在面饼子里,或许你可以尝一尝……”你他奶奶的当真是噎死人不偿命啊。欸……自己口才不济,本事更不济,跑了半天讨了个没趣儿。
“你原来那头坐骑呢?”我自顾自倒了一杯茶喝,问更染。
“哦,你说那头小孰湖啊,被白泽打了一顿回崦嵫山了。”她不在意地说。
“哼,好一头霸道的蛊雕,欺负弱小,算什么本事!早晚我给他个三刀四剑,完了炖汤。”我愤愤。
“他若知道死了会给你炖汤那是决然不肯死的,即便死了也得诈尸,再者说了,你当年不就是看他一身威武,能帮你耍威风才死皮赖脸求来的吗?”
“你……”你大爷的,我又被呛了。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来,这是蕴慈送来的肉脯,尝尝。”
我试了,不愧是蕴慈的手艺,有了这口吃的,方才那点子气瞬间消了。我拿了她的三生簿子来看,正看到又是一个多情女子薄情郎的故事,那女子我倒知道,她在望乡台的茶还是我亲手烹的,当然,那时候白泽已经走了,我也只得亲手烹。她的前生我在望乡台已然尽数知晓,不过是个多情女子薄情郎的烂糟故事,无甚稀罕。不过这丫头来世倒是传奇。说她出身在一个家境富裕的商贾人家,不善女工也不爱经商,却是一把读书的好手。十七岁那年成了当朝唯一的女状元,进了中枢入了内阁。而那穷书生,读书倒也不差,却成了她是属下,偏她为官板正,立身处世颇难琢磨,那薄情书生一生瞧她脸色,如履薄冰。
“这倒是个奇女子!”我感叹,其实我有些羡慕更染的本事,她是三生石的主人,能念动三生诀,知晓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并拓印下来,成了一本本三生簿子。我和她最常做的事儿便是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把这些簿子当戏本子读,彼岸之人的生死怨怪,爱恨嗔痴,于我们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罢了。
“我该做饭了,你留在这里用饭吧,我看你倒是喜欢这肉脯,可以给你卷些在面饼子里。”我咬碎一口银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省了吧,只管好好把你那只蛊雕喂肥了,我早晚炖了他。”说完我愤然离身,完了想想,毅然决然又回来把那一大盘肉脯悉数倒进了自己的口袋。没了坐骑,我只得自己招了朵云慢腾腾回了望乡台,我那二两修为,光是驾个云便要喘上两口大气。
我记得回去的时候,寒川正在等我。他收拾了我那一地的狼藉,重新帮我垒起塌了的烧火炉灶,上面正烧着热水。还有被我烧了大半的亭子都帮我收拾稳妥了。看到他我突然觉得委屈极了,抽抽搭搭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诉说我的委屈,我是如何不容易才让白泽答应当我的坐骑,三万年来我是如何善待他,他又是如何狼心狗肺抛弃了我,更染又是如何不理解我等等……
他倒了热水,拧了块帕子,一边细心地为我擦脸一边耐心地听我唠叨。等我哭累了也讲累了,他才说话:“饿了吧,给你带了莲叶粥,吃点吧。”他把带的粥倒出来,又轻轻吹了几口,才递给我道,“慢点吃。”
我委委屈屈喝了几口,喝着喝着又委委屈屈吧嗒吧嗒流眼泪。
“这又是怎么了?”他叹了口气。
我一边抽噎一边可怜巴巴道:“没有肉!”说完我觉得自己更委屈了。
“那给你煎两个竦斯蛋可好?”
“两个不够。”我眼巴巴望着他。
“那煎四个?”
“嗯,别煎太熟,我喜欢蛋黄有点溏心的。”
“好。”他摸摸我的头,转身认命地给我煎蛋去了。等我喝完他带的粥,吃完他煎的蛋。他又很自觉地去洗碗收拾,我斜靠在亭子旁,跟他说:
“我不想在望乡台了,老想起那只没良心的蛊雕。”
“那跟我回旸谷,我那里青莲正开得好看。”
“可我修为不够,驾不了那么远的云。”
“我驾云带你便是。”
“我的坐骑跑了。”
“帮你重新猎一只。”
“可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废了他然后剁了炖汤。”
“我打不过他。”
“我帮你打。”
“那么大一只蛊雕,得炖多大一锅汤啊,而且我炖汤很难喝的。”
“我帮你喝。”
“我炖了更染的坐骑,她不会放过我的。”
“如此……便也分她一碗汤好了。”
……
我彻底被他逗乐了,他也笑了。我跑过去抱住他的胳膊,撒娇道:
“师父,你怎么这么好啊!”
“不好怎么当你师父啊。”他拍拍我的头。
这就是寒川,此岸之主,大母大父的独子,也是我和剪殇、更染、蕴慈、栢东临还有慕弦离的师父。一路又当爹又当娘把我们拉扯大。用他的话说,费了他姥姥的劲儿了。我们皆是以他之骨血化就,一滴血一根骨,再使出结茧化人术,待破茧而出便能长成如他一般的人形,睁眼在此岸见的第一人便是他,自然视他为唯一的倚靠。此后便听他教养,跟他修炼玩耍混日子。因了寒川的照拂,我们几个方能和乐安康地长大。可他却是个极不靠谱的师父,他对我们的教养,俩字儿便能一言以蔽之:随意。
寒川此人极为护短,对我们几个更是宠溺宽宥到了极致,从无半分苛责。但好在他的弟子都很成器,各自有了一身本事,在此岸有了一席安身立命之所。不过我却是个不大不小的例外,我是他的弟子里最小的。我出生的时候更染和慕弦离已经小有本事,连蕴慈和栢东临也算半个大人了。大我一岁的剪殇自己破茧而出嘤嘤呀呀哭起来。而我结茧两千年,到了时辰却硬是半分动静也无,寒川怕我闷死在茧里便又耗损修为从外部帮我破茧,这才保我一条小命。很多年后,更染跟我说,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惊呆了,因为刚出生的我实在太丑了,皱皱巴巴蔫儿瘪瘪。更染说,他们破茧而出时个个白胖可爱惹人疼,到了我这儿不知出了什么差错,跟白胖可爱挨不着半点边。可她这番说辞着实不能说服我,因为我尚且不记得自己破茧时皱皱巴巴,她又如何记得自己白胖可爱呢?奈何她长我一些年岁,又是老大姐,我不敢驳她。不过她也说了,当寒川抱出皱皱巴巴又丑不拉几的我时,发生了一点他们意料之外的事儿——我笑了,对着寒川,我那张皱皱巴巴的丑脸笑得天花乱坠。
因了那一笑,我逆天改命了。
“你对师父笑了,他也笑了”更染跟我说,“那时候我们突然都觉得你没那么丑了。”
“后来呢?”我一边嚼着更染摊的面饼子,一边问她。
“后来我们就把你养活这么大了呀。”她捏捏我的肥脸笑道,“养活大了,也变好看了。”她很是欣慰,似乎是她把我养漂亮的,我有点不服气,因为我本来就能长这么好看,以后还会越来越好看的。
船靠岸了,我回过神来,很多年不曾想起这些前尘往事了,为何今日偏偏记起来了,还记得这般清楚。果然是年纪大了,便喜欢追忆往昔了吗。还是去了一趟彼岸,心境真的变了?又或者,是那六首蛟龙令我想起了痛楚的过往?
罢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