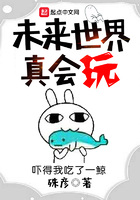清泉因刚刚从食盒端出粥时,烫到了手,现在还热辣辣的疼痛,见韩冰一动不动地仍端着热粥,忙唤了声:“韩先生。”
床上的胡云山又大声叫了声‘小妹’,清泉回身摸了摸茶壶,壶身冰凉,见韩冰已放下碗,拿了一个倭脚瓶的杯子,要过来倒水,清泉忙拎起水壶道:“我去给胡少爷打些开水。”边说边拎着茶壶出去了。
韩冰把杯放到桌子上,翻过手心,见已被热粥烫得通红。
其实韩冰并非拈酸吃醋之人,她之所以有些魂不守舍,皆因为昨夜胡云山向她表明心曲,她方知他的一颗心原是在她心上,数日来滞留心头的阴霭一扫而空,而又加上清泉说何靖华品行端正,她心里想胡云山即与何靖华是莫逆之交,也必是志趣相同。
一旦发现并非如此,就联想他混沌状态所吐之言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原已芳心暗许,顿如浇上一瓢冷水般,直寒到心里。
韩冰在对待与胡云山的感情上,一直秉承着,你用几分心对我,我就用几分心还你,你先爱我,我才敢爱你,你若不爱我,我即使真爱你,也要看似不爱你,否则让你捷足登了先,我将处处受制于掣肘,又如何独善其身?
窗外传来喜鹊的叫声,她走到窗前,看着几只花喜鹊上下欢快地在枝头上跳跃着,心情也跟着渐渐放松。
胡云山睡觉时本不喜欢挂帐子,嫌像用被蒙住头一样,感到压抑,又因掀了半天铃没人应,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扯下帐子,拖着虚弱的身子,自己过来倒水,走到桌边,找了一圈没看到水壶,见一杯里剩了半杯水,随手端起来一饮而尽,喝过水觉得头脑渐清醒些,环视四周,倒像走进谁的洞房一样。
一转头见窗边立着一个青年,傲然挺拔的背影,似有些相识的感觉,又因刚才鲁莽扯坏帐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忙弯腰道歉道:“昨晚头昏脑沉,竟误入公子的洞房,真是对不住!一会儿我叫人另买一领帐子送过来。”
韩冰回过头来,见他虽有些憔悴,仍不失俊朗,温文尔雅地笑了一下道:“你起来了?二少爷正派人去给你请大夫。”
胡云山见她明颜皓齿,虽静静一笑,直像一缕和煦的阳光洒向他的心头,吹散开缠绕于心头的阴云,他竟怔住了。又听她说‘二少爷’,忍不住问道:“莫非这是靖华的洞房?昨儿还见到他,怎么今儿倒成了亲?”
“谁成了亲?醒了,云山。”何靖华从匆匆屋外走进来,韩冰看着他额头上浅浅的汗珠,心里暗笑,何靖华真被胡云山支使迷糊了,出来进去,都带着小跑,真是人生有如此一知己足矣。
何靖华走到桌子边,看到一桌子的菜动都没动一下,抬起眼睛问韩冰:“菜都要凉了,怎么还不吃?”转回头对云山道:“刚刚叫蓝喜去找大夫的功夫,你猜我看到谁了?”他脱下外面的西服,随手扔到靠墙边椅子上,里面穿着一件宝蓝色的衬衫,外面套着灰色的坎肩。
胡云山刚刚兴起的一点儿兴致,见何靖华只平常一身西装,并不像是新郎一样,顿时无精打采地说道:“除非见到韩玉露,否则都与我无关。”
何靖华啼笑皆非地坐到桌前,见只放了一双碗筷,正巧清泉提着热水进来,忙从食盒里又抽出两副碗筷放到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