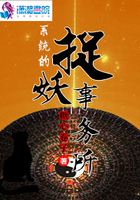这两日,沈云燕与许婆子亦都上门找了楚娇娘,问了合伙拾柴炭的事儿。
楚娇娘本想推了,但想家中的蚕现而也无用多管,手上亦没多少活儿碍着,正反在家中闲着也是闲着,就应下了。顺势也拉上李芽儿一起,也都还是去年那几伙人。
于是几人择好日子,不日,便去山里寻了起来。最先打头的地儿,也就在龙山村的后山。
迎着足金灿灿的阳光,女人们背着背篓,男人们拉着板车,去往山里。路边有野桂的香味,依附微风暗暗迤逦扑鼻,时淡时浓,教人沁爽甜静。
上去山中后,黄叶遍布的林间,日光斑驳,景色阴凉渐爽朗。楚娇娘脚踩松脆干枝,嘴里哼着小调儿,带着身边的沈云燕与李芽儿两人,也都跟着哼哼唱唱起来。整个林间回荡着欢声笑语,气氛不尽轻松欢快。
但此山中早已有拾柴之人赶在他们前头,将林中好些粗枝干柴已清捡走。是以几人便往林中深处走了去。
龙山村后山地大物博不是人瞎说的,除了拾干柴外,几人均捡了不少野菜野果子,且都是药用极高的好物种药材,这若是处理好,那也是能卖钱的。
一日下来,几人收获颇为丰富。
岑阿穆的车已然是装不下了,但好在今年沈父拉了一车,许婆子也叫她的老头也拉了一车,拢共三车。这三车下来,少说也有个十担了。
回去的路上,几人的脸上全是你看看我笑,我看看你笑,嘴里道着闲话,面容是满载而归的喜悦兴奋。
然在快下完山时,靠近清水沟的一条路上,楚娇娘脚下踩上一粒小碎石头子儿,毫无预兆的扭崴了脚,直从旁边满是荆棘的坡上滑下来,险些落到沟里。
一声惊叫,一时间说笑的话语被截断。
沈云燕许婆子等人见着楚娇娘身子倒滑下去,未能来得及反应,皆是一吓,不约而同叫喊一声“娇娘!”慌忙追下来。
李芽儿反应最快,忙下去将楚娇娘扶了扶,“娇娘姐,你没事吧?”
沈云燕与许婆子随后过来,紧着岑阿穆,许老头,沈父等人亦忙将车拉到平缓的地方放下,过来问了情况:有事无事,有无伤着哪儿?
楚娇娘坐在地上木了片刻,浑身突然缓过劲的疼痛起来,盼倩秀眉拧得极难受。这才发现手肘手掌的肌肤皆被荆棘划出不少的痕迹,鲜红的血迹透出来,看着就让人隐忍疼痛。
沈云燕见她模样,跟着把眉头一皱,替她感到疼:“你这……多吓人。没事儿吧!有没有伤着骨头?”
“应,应该没事儿。”楚娇娘借着沈云燕与李芽儿给的力起了身,动了动手腕手肘,脚下也扭了一扭,“没伤着骨头,没事儿。”
“这还能没事儿呢!都破皮出血了!”许婆子一面担心一面埋怨,帮她掸了掸衣裳的木叶渣子,道:“这路又不是不好走,你怎个这般不小心?差一点就掉进去了!”
楚娇娘也不知怎的,说崴脚也就崴脚了,直打了趣儿:“可能是许久未摔跤,是该要摔一次了。”
许婆子直给了个斜眼:“你倒是看得开,竟还能有这个理由。”
楚娇娘清爽一笑:“那不然呢?”
“行了行了,别耽搁时间,赶紧回去把伤口包扎一下。”许老头插了一句嘴。
沈云燕看了看她的伤口,跟着又庆幸一句:“好在是没伤着脸,这若是破相了,你男人回来,我们还不好交代了。”
一句话,又惹了楚娇娘一个笑出来。
收整好,楚娇娘那一篓子野菜甚的,是不能要了,篓子也摔了个稀巴烂,索性就扔了。然后在几人搀扶下下了山。
柴炭由沈云燕许婆子他们拉去了岑家,李芽儿则扶着楚娇娘先回了家。
才到家,魏老头与刘氏一见她如此狼狈的模样,也是狠狠吓了一跳。
二老一人一张惊恐慌张的脸拢过来,周身上下将她好一阵看,亦是问寒问暖,不甚担心关心:这是出了甚事儿!
楚娇娘面容姿态均给得轻松,嘴里道了无事儿,就是拾柴时不小心给摔了。丝毫不教人担心。
魏老头直骂她怎那不小心!
刘氏也跟着附和,让她赶紧去包扎。但末尾刘氏说的话同沈云燕一样,就怕她伤严重了,魏轩回来怪到她头上来。
楚娇娘嫣嫣嘻笑,竟觉得这样的担心关怀,让她心儿可乐了。
之后,在刘氏的帮忙下,楚娇娘解下身上的襻膊,去了谢圣手的家做了包扎处理。
酉时初刻,楚娇娘回来,老远就见家中烟囱里头飘了白浓浓的烟,映在鱼鳞般彩霞密布的苍穹上,画出一道游龙形态。
看罢,楚娇娘嘴角再次泛起浅浅温暖的笑容。有些事儿,不言而喻。
刘氏也不是没眼力见,儿媳妇手掌手臂全都受伤能,还能让她做饭不成?归刘氏劳作的时候,刘氏也不懈怠。吃饭时,见楚娇娘手不方便,刘氏也不肖谁提醒,吃上两口,便往她碗中夹了菜。
瞧这家中的气氛,刘氏的转变,楚娇娘煞然像个老成的婆子一样,心里熨帖得厉害,欣慰呀!嘴里道着:谢谢娘。
入夜,楚娇娘打算梳洗,但看看裹起来的手,不能入水,亦不好让人帮忙,只好简单的擦拭作罢,便躺上床睡了。
今日入睡极快,许是累了,没一刻的功夫便入了梦乡,可……梦不怎么好。
日光斑驳的丛林里,脚踩松脆干枝“咔吱咔吱”作响。只一瞬间,周围满是荆棘环绕,那荆棘带着锯齿,一点点地朝她逼近,不断发出阵阵轰隆隆的声音,恐怖至极。
头顶日光逐渐变暗,混浊如一滩淤泥盖在苍穹之顶,一层一层朝她往下压来,叫人透不过气儿。
忽然身边有一个人,时而是魏轩,时而看不清他的容样,只晓的那人牵了她的手,牵得她钻心的疼。
“魏郎,你放开我……”楚娇娘挣扎。
“魏郎,放开我……疼……”
几声呓语,楚娇娘从噩梦中惊醒。浑身沁满汗液,心中不安。受伤的那只手也一阵一阵痛到她发抖不止,然另一只手竟然恍惚摸着身边空荡荡的床,还想着魏轩怎么不在……
一眼恍若隔世,待楚娇娘彻底清醒后,才想起魏轩本就是不在她身边的。
白月光透过窗间,将暗沉沉的屋中照亮,静谧,清冷,孤寂,落寞……不安和害怕……
楚娇娘睡不着,披上一件外衣起身,推了半扇窗,迎头看着月亮头,才子时过半。
算下来,魏轩超过两个月未曾来信了,楚娇娘忍不住忧心,想知道他怎么了?他可安好?为何还不来信?是不是……
有些东西一旦形成常有的习惯,忽然在有一天,这个习惯断了,便不由得容易让人多想。楚娇娘在收魏轩书信的习惯上,从未间断,这是第一次。所以,她不安。
大半个晚上,楚娇娘都坐在窗前,整个脑中心上除了魏轩,再无其他。便是后头困意来袭,回到床榻上,辗转之间,想得也是他。
早晨起来,楚娇娘对着窗边打开镜奁,再看着镜中之人,因彻夜无眠,眼眶凹陷有些明显,却毫无修饰整理之意。
一夜之间,她便没了昨日的欢敞心情。
吃饭时,刘氏与魏老头都瞧出了问题,不约而同都问了楚娇娘。
楚娇娘不好说自己在忧心魏轩,怕二老觉着她在多想,只说了自己伤口疼得紧,没甚心情吃东西。喝了两口粥,便回了房。
可一连三日下来,皆无法安顿闭眼休息,也无法完整的吃一顿。越往后,楚娇娘心越发慌得厉害,连噩梦的次数也开始多了。
立冬的一早,不等吃下早饭,楚娇娘跑去县里衙门找了扶卓仪,想问问魏轩有无消息递给她。
县衙后堂,扶卓仪正与原世海、韩夫子几人在聊话,听楚娇娘过来,扶卓仪大致猜到了她过来的目的,面容心下因此慌措不安些时。
早在半月前,扶卓仪就得知了魏轩的消息,内心一直在揪虑,想着这件事儿到底要不要告诉魏家?今日与原世海以及他们所谈论的事,说得也正是魏轩的事儿。
一身秋香色交领襦裙的女人仓促的等在门口,扶卓仪出来县衙门口,只见她脸色苍白发干,眼眶深陷昏暗,憔悴不少;又见两只手都还包扎着,心上吓了一个紧张。
“嫂嫂,你这是……怎么了?”
见扶卓仪出来,楚娇娘有些吃力的扬起不甚在意的浅笑:“我无事,我来是想问问你,魏郎他有两个月未写信回来,有无给你托话回来?”
楚娇娘话语清淡,但心中的着急早是浮在眼中。
意料之中的话让扶卓仪口齿微僵,颇有些难以张开,顿下一会儿才道:“……嫂嫂,你……你一大早的过来,我见你面色差,先去里头坐着歇一会儿吧。”
楚娇娘立了少时,不知怎的,笑容在脸上已是不自在,“……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