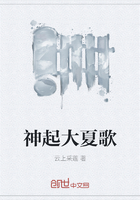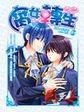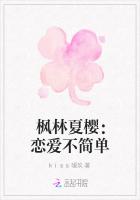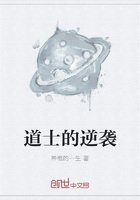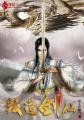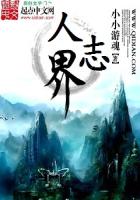离开寿州后,容止主仆三人向北而行,八月十三至应天。中秋将至,容止一行人便留在应天,打算在应天度过中秋,于十六一早离开。
到了应天,容止一行人找了个依水而立,杨柳依依的客栈。
应天位于淮水下游最大的应水河流沿岸的冲积平原,为了更好的发展河运,勤劳聪慧的应天人,扩大和加深河道,在城市建立各个船舶口岸,沟通东西南北。南运河与南大湖相连,水深港宽,水运交通便利,形成了一个人烟稠密、商铺林立的繁华的应天首府。
而应天王家就是靠运河发家,发展到现在应天所有的运河尽握在王家之手。
容止让三儿带着自己的名贴去应天府要了一些近期的邸报后,阿四在客栈收拾房间。
三儿带了邸报回来,容止给了阿四一百文铜钱*,又吩咐三儿带着阿四四处转转。待他们走后,容止一个人窝在房间的软榻上看报。
报上有三条消息让容止惊心不已,一是寿州水灾。这是容止亲眼经历的,虽然他在天一放晴就离开了,但一想到那一半个月的大水,又想想城外那广阔的大湖,容止便知水灾是逃不掉的。虽然他已经给郑家写了详细的救灾之策,随后又写了大篇治水之策,但世家大族,连皇帝的命令都可能会不听,有何况是一个小小的过客。
容止只寄期望于郑家是贤德太后本家,其他家族不同。
随后容止看见,邸报上有一大块版面都写的是襄州大旱,“唉~”容止叹息,他就知道大旱大涝从不单一出现,有大旱必有大涝,有大涝必有大旱,是天道。容止没治理过旱灾,不得其法,只想着可否把治理水涝的方法稍作更改用在治旱上。
第三条是户部侍郎曹寅曹大人因被朝臣参贪污腐败,现在被革职在家,接受调查。
容止没见过曹寅,但他在江都府那几个月,走街串巷,田间树下,不乏有人赞美曹大人大公无私,公正廉洁。称赞其在江都府任职的那些年,大修学堂,兴办教育,支持农商,发展经济,造福江都百姓。
在江都,无人不称赞他,无人不念他的好。这样的人,又栽培了陆丰泽陆大人那般的人,绝对不会是贪污之人。
容止看着邸报越看越皱眉,接下来几天的邸报,陛下不知用了什么方式竟压制住了一部分对曹寅大人的弹劾,又几天后,有人开始为曹寅大人正名,也正因为这样,朝廷分成了两派,一派竭力请旨皇帝严惩贪污,一部分力保曹大人,于是这事被闹得沸沸扬扬,阖宫内外,朝堂上下,人尽皆知。
容止心中为曹寅大人担心。
约莫到了亥时一刻,三儿和阿四回来了,阿四买了一些当地特色的吃食和小玩意儿给容止。
容止笑着收下了,又让阿四去休息,三儿留下。
三儿条理清晰的说了他在逛街时听到的关于王家和朝廷的一些消息,又说了一些民间趣闻和民间对近日襄州大旱寿州大水以及曹大人之事的看法。
容止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三儿退下了。
三儿退下时,在门口犹豫地说道:“听说明日晚到十六都会有灯会,一个大富商出了两个灯谜,许了百贯给答中之人。”
容止挑眉,放下手中的邸报,疑惑的问道:“富商?”
三儿见容止感兴趣,又急忙跑到容止身边,献宝似的答道:“对,听说可富了。每次出行都有七八个丫鬟跟着,十多个侍卫护着,那派头到像个皇子皇孙一般。”
“何处来的?”
“不知,百姓只知是一个富商。”
良久,容止才淡淡的“嗯”了一声。
八月十五,团圆时节,应天张灯结彩,整夜灯火通明,伎乐声闻数里,人声鼎沸。
容止带三儿阿四在一家极具特色的酒楼里吃完饭,站在包间的雕花窗栏前,看着漂满河灯,如同闪烁的星空一般的运河,容止让三儿去租一艘小画舫,夜游应天。
坐在画舫里,看着岸边店铺林立,灯火辉煌,河上花灯盏盏顺水而流,容止让三儿和阿四自行玩乐。
随着也越来越深,运河里的画舫越来越多,容止靠在船边,欣赏着应天的夜景和漂流而去的花灯。
顺着精致的花灯,容止看见一艘漂亮的大型的雕花画舫,白色的维幔随风而起,一位白衣少年坐在轮椅缓缓地到了船板上,一位灰白衣侍女手捧着一朵金色的荷花花灯,按着少年的指示,用细竹竿慢慢的放进了满河的花灯中。
少年见花灯入水,又自己控制着轮椅,回到了画舫。
随后画舫响起了铮铮的琵琶声,一曲《琵琶行》伴着荷花河灯缓缓的流进了容止的耳朵。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看着那飘到自己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的荷花河灯,容止好奇的将其捡了上来,打开荷花,看见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纸条。
纸条上的字体豪放洒脱。
西出阳关无故人。
是谁写的呢?坐在轮椅上的少年?还是画舫里面的人?
容止陷入了沉思,再看向那画舫,只见一个红衣公子一只手拉着一位白衣公子,另一只手上提了一盏火红色的花灯,喜笑颜开地和那白衣公子说话。随后那红衣公子看向船内,似乎在叫某人出来,片刻船舱中出来一个灰白衣裙手上拿了一个兔子灯的侍女。
再随后,那船就使得越来越远了,容止收回目光,突然发现沿河风景越来越熟悉,是自己下榻的客栈所在的那条河。
容止让船夫停船,自己拿着花灯下了船,中秋佳节,他让三儿和阿四自己去好好过节,不用服侍。
第二天一大早,阿四就打了洗漱水进来,叫醒了他,三儿在外面点餐。
容止在吃饭时,阿四和三儿又在收拾行李。一切收拾妥当,一行人就离开了应天。
出了应天,他们转而向西。
在路上,容止突然问道,谁赢了那百贯?
三儿说,一位坐轮椅的公子和另一个面若寒霜的白衣公子赢了百贯钱。
阿四补充道:一个气质出尘的姑娘笑着替两位公子收下的。
容止喃喃的问道,出尘?什么样的出尘?
阿四低头思索该如何组织语言回答这个问题,如何描述那姑娘的出尘。
三儿倒是直白地说道,就是那种原来女子还可以这样的出尘。
容止低头,陷入沉思…
随后的路程中,容止都很少说话,到是三儿和阿四常常聊起应天的繁华。
六日后,容止一行人到了陈留,他们稍作休息后立即就出发了。
离开陈留大约三四个时辰,在一个名叫老屲山的地方突然狂风大作,天空乌云密布。容止挑开窗帘,见草木萧萧,鸟兽凄凄,暴雨即将来临,恐遇山洪,便让三儿找个农家投宿。
三儿四处张望,见山沟处冒着寥寥被狂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白烟,心中窃喜,便驾着马车向那白烟赶去。
山路崎岖蜿蜒,路上全是各种各样的小花小草。紫的、白的、粉的夏枯草夹杂着开着紫色小花的如同麦穗一样的车前草,在风中摇曳。
山路的左边是一个从山上蔓延而下的沟渠,沟渠里长满了绿绿的长条形的小草,有些中间还夹杂着几朵盛开的夏枯草。在地势平缓的地方,沟渠中满是清澈见底的积水,如同一个小池塘一般。草儿随着水流而动,浅蓝色的小蝴蝶随着风儿飞舞。
而在另一边,则是荒草萋萋的荒地。里面茅草萋萋,黄荆丛生,桑树枝枝交相辉映。
三儿见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中逐渐弥漫着尘土的味道,他沿着越来越窄的小路艰难前行。
见小路旁的树荫里隐逸着很多现已被藤蔓植物占领的坍塌的房子,手心不禁泛起了冷汗。
三儿对容止说道:“公子看看右侧的树林里。”
容止闻言挑开窗看向右侧的树林,看见很多破败的房屋。
容止皱眉,压下心中的疑惑,道:“赶紧前行吧,雨马上就要下了。”
三儿依言加快了马车的速度。
又过了一刻钟,容止一行人终于到了那个烟火人家。
三儿停下马车,阿四立马弓身走出车厢,下了车。
三儿看着院子的大门,试探性的推了推,没想到门一推就开,就轻车熟路般牵着马儿,将马车停在了院子里。
雨声已至,阿四让容止在马车中等候,容止笑了笑,拒绝了阿四的好意,也跟着下车了。
到了屋舍门前,阿四轻轻地敲了敲门,道:“农家,我们由江都而来,去往开封,偶遇大雨,望农家收留我们三人一晚。”
屋中静悄悄的,阿四又敲了敲,恳切地说道:“求农家收留我们一晚。”
大雨已至,打在外面的荒草萋萋的庭院里,淋淋漓漓。屋内传出微弱的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一个白头发,满面皱纹的老婆婆从门后探出了脑袋。
在陈留的这个破旧的小山村里,容止在一个瘸了右腿的老婆婆家住了一宿。山村里的年轻人都搬走了,只有老婆婆一个人守着一只大黄狗,守着那片土地。那天晚上,三儿帮着老婆婆劈了很多柴火,阿四又帮助眼睛不好的婆婆缝衣服补鞋袜缝被子,反倒是容止这个手不能提见不能抗的读书人只能干看着。
老婆婆说,她的女儿也是读书人,还是个受人尊重的女先生,只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后来她的老伴也离开了,现在就剩她和家里的大黄了。
婆婆说,所有的人都埋葬在这片土地里,而活着的人也即将埋在这土里。
到了未时,雨慢慢停了,太阳从乌云中探出了脑袋,金色的阳光传过厚重的云层,洒在这个宁静偏远的小村庄。
金色的阳光缠绕着朦胧的雾气。容止看着这破败的房屋,陷入沉思。
夜晚,月明星稀,容止站在窗前,看着坐在柚子树下,乘凉的老人,突感凄凉。
月光下,老黄狗枕在老人的脚上,老人垂着头,低声唱到:“道一句青山,山外有山;道一声绿树,树高墙上,高高的瓦檐,树荫森森;转头的…柚子树,花开满树,山间的水月,狗吠鸟鸣,远处的人家……炊烟缕缕;都说那,远山外,城墙四起,…但我却深爱这,寂静之地;…都说那山水,青青绿绿,都说那人家…汲汲营营;…都说那山水,芳草萋萋,你可见,远山孤坟恸恸……”
歌声伴着夜间的虫鸣鸟叫,断断续续,杂乱无章,似唱似说,似哭似诉。声音嘶哑沧桑,他看不见她的面庞,但他感受到了她浓郁的悲伤,孤独,永远的孤独。
离开老婆婆家,三日后,容止一行人抵达京城。
(注:1两白银=1贯铜钱=1000文铜钱
不要太纠结于钱银换算,因为真的太难了,看了很多文件,大家说得得很冠冕堂皇,但实际用处不大。于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宋朝的物价,发现宋初物价不算很高,于是就估摸着现在的物价来假设。
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宋人维持简单的生活生产,人均每天需要生活费100文钱”。
宋初太祖时期货币税收都是有定制的,后来乱套了,这个真的太难,请不要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