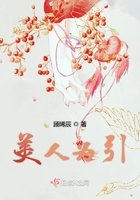夏日天亮的格外早,曙光如同水波四散,金灿灿的朝晖伴随冉冉上升的红日,将东方的天际侵染成红彤彤的色彩,似一片橘红的汪洋大海呈现在荥阳城外连绵山脉的主峰上。有疏落的风吹过,带来夏日里难得的清澈的凉意,夏侯山庄大门之外的木芙蓉随风摇曳,虽还未到开花季节也尽显婀娜多姿。
随着时间点点滴滴的迫近,及笄嘉礼是否能够如约顺利举行尚且待定,然而这已经不是夏侯宁波夫妇最为关心的一点,揪出投井下毒的幕后黑手,顺利救出夏侯梓阳确保平安归来,才是忧心如焚的心事,也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匆忙用完了早膳,夏侯宁波便亲自审讯因为携带有毒之物和兵器被捕的几名嫌疑人,凌峰和楚雄率山庄的侍卫队加大了对荥阳城的搜索,寻觅蛛丝马迹。
凌峰知道夏侯梓阳没有落在白浪等人的手上,自然也就明白夏侯梓阳没有被贼人挟持,他虽想不通为什么会在动手之前走漏消息,但从内心而言正如白浪所说,竟替夏侯山庄躲过一场无妄之灾怀有怀揣一丝窃喜之情。夏侯梓阳应该是赌气暂时离家出走了,和那个叫毛豆的市井小子混在一起,想到此,凌峰眉心微微一动,他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心头却不由自主地涌上一股酸楚的味道,像是炎热夏日里被柠檬汁或苹果醋浸过一般。
安若曦和潘罗姐妹等人也表示愿意出一份绵薄之力,发动自身人脉关系寻找蛛丝马迹,自己也打算奔走于街头巷尾或闹市一隅探听消息。
萨日娜和随从无暇多管夏侯山庄的闲外之事,无论它是七零八碎的琐事,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她爽然地挥了一挥衣袖,声音高傲中透出一缕清冷,朗声道:”中原高门大户的地方看了,茶喝了,饭吃了,除了学到了一些借刀杀人、张机设阱的本事外,就不过如此了!也算长见识了!”
山庄的侍卫对此不屑之言怒气冲冲,脸色发青,显然就要作色,却忽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声音,回头一望,原来是蓬面人见毛豆久去不回产生坐立不安的情绪,变得焦虑烦躁起来,一不顺心便摔了茶杯,推了方角桌,见有人上前大声斥责,便莫名其妙地口中咆哮道:“庸奴!你还能再作恶乎?“这摸不着头脑的话让山庄的侍卫大为冒火,欲要冲过来把他摁在地上好好地教训一顿,却不料还未近身就被他快如电闪的掌风直接拍到了地上,顿时感到、全身一震,手臂酸软,不由发出一声哀叫。
见此情况,原本站岗伫立在蓬面人身后距离几尺的两名侍卫,立马挺玄铁钢刀昂首直入,刀刃明晃晃地抖动,发出了嗡嗡之声。眼见刀锋就要削到后颈,蓬面人脚步微动,提气窜出,向右踏出两步,直接凭借耳力反背徒手挡刀,只听铛铛一响,钢刀被拦腰折断而落地,这空手劈白刃的手速堪比追风逐电般,让现场侍卫目不暇接,也让准备跨出山庄门槛的安若曦等人微有诧异之色。幸亏他还不欲伤人性命,手上并未下了狠手。
朱一彤连忙上前劝阻,笑意似弱柳扶枝,盈盈道:“大家都是担忧夏侯家大小姐的安危,只是一场误会罢了。”说着,拉了拉蓬面人的衣袖,耳畔悄声道:“莫要躁怒,毛豆未必有什么事,咱们在这里有吃有喝的,不吃亏。”
蓬面人本来有怒气在胸中徘徊,按捺不住发作的性情,无意之中与朱一彤相视一眼,登时怔住,兴许是被少女微启红唇的柔声所打动,他的眉头松了一松,浓翳的阴郁微微散退。安若曦抬起眼皮,凝睇一眼,见夏侯山庄的侍卫对蓬面人已经产生了敢怒而不敢言的不悦之色,心想他武功高强却貌似有些神志不清,若是再独自让他留在山庄,弄不好又会因为一言不合就与侍卫发生争执动起手来而不好收场,便含了一缕浅笑,对蓬面人道:“这位客人,你也不像是本地人,对荥阳城想必也有不少想逛的地方,不妨和我们一同出去走走看看,兴许一不小心就碰到了你那位小兄弟。”
蓬面人心思一转,点了点头,环视一周,喃喃道:“这山庄横梁压顶,运势受阻,必有晦气。“对此,山庄的侍卫“呸”了一声,一嗤恨意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蓬面人呵呵一笑,不以为然道:“狗嘴若能吐出象牙来,不就成妖怪了?”一番反怂竟让侍卫一时语塞,支吾着说不上来。
走出夏侯山庄,安若曦和潘罗姐妹俩选择分道扬镳各行其道办事,蓬面人跟着安若曦一行人向城中心的闹市行进,朱一彤仿佛是因为介怀自己身份上的卑微差距并不打算跟着几位各有身份地位的女主一道上路,而是选择了留在山庄静候消息,顺便有个落脚的地方供吃供喝,自己何乐不为?
安若曦一行人不疾不徐地向西城走去,这是荥阳城最热闹繁华的地方,人头攒动,街贩沿街叫卖的声音不绝于耳,让初到中原的她们开拓了对于市井之地的眼界,左顾右盼,兴致盎然。美景离不开美食,安若曦让人购置了灌汤包并分给了蓬面人一些,细白如瓷的外皮包着咸香鲜美的肉馅,汤味儿浓厚,很有嚼感,让她对中原的名小吃顿时增添了几分好感,再一凝眸,便瞧见蓬面人并未吃包子,只是用油纸将灌汤包小心地包裹起来,揣进衣兜里。她以为蓬面人舍不得吃,便淡然而笑道:“灌汤包要趁热吃,不然包子皮容易粘在油纸上,造成包子皮破损,这样汤汁就流走了。”
蓬面人扬一扬眉,微一沉吟道:“我那个小兄弟就喜欢吃包子,不知道他现在饿着了没?”
安若曦好奇地问道:“他叫你‘花大哥’,你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他也不晓得姓氏名谁,你们还真是一对难兄难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感情好像蛮深的。”
蓬面人沉一沉声道:“人与人相识,不在于长久,而在于赤城。有的人,认识了半辈子,还是一副蛇蝎心肠,如同披着羊皮的狼。”
安若曦含了一缕端庄笑意,心想此人若是正常起来说话倒是言之有理,有条不紊,想必之前受了道貌岸然奸人的坑害,才落得一个神志时不时犯迷糊的下场。
正想到此,随从女护卫一个走路不留神,撞到了迎面走来步履匆匆来人的胳膊,来人随即脸色一沉,嗔怪地睇她一眼,满是奚落之色,怒斥道:“蛮夷娘们,你走路不长眼睛呀!”
女侍卫不甘心被骂,气咻咻道:“你走路长眼睛,这么着急走,是赶着回去奔丧吗?”
来人神色傲然,眸中凝起一缕寒光,挥动手中钉头向前极为锋利的狼牙锤,精光四射,直接向脑门拍了过来。蓬面人右掌翻起,从旁一把抓过狼牙锤,狠狠地甩出,丝毫不顾前部末端若干破甲能力出类拔萃的狼牙状寸长铁钉,来人脚步踉跄,握紧的狼牙锤来不及脱手,直接被软索羁绊在半空转悠了一圈,仰翻摔倒在地,后脑勺受伤渗出鲜血来在地板上作一朵艳丽的血红花朵,也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来人神色傲然,眸中凝起一缕寒光,挥动手中钉头向前极为锋利的狼牙锤,精光四射,直接向脑门拍了过来。蓬面人右掌翻起,从旁一把抓过狼牙锤,狠狠地甩出,丝毫不顾前部末端若干破甲能力出类拔萃的狼牙状寸长铁钉,来人脚步踉跄,握紧的狼牙锤来不及脱手,直接被软索羁绊在半空转悠了一圈,仰翻摔倒在地,后脑勺受伤渗出鲜血来在地板上作一朵艳丽的血红花朵,也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当来人看清了蓬面人的身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只道:“又是你这杂碎多管闲事——”。原来此人正是皇城司诸司使陆琪,话音未落,两道强劲的掌力闪到了他的耳边,续而啪啪打在了脸上,留下清清脆的声响和斑斑的血痕,煞是醒目。
只见安若曦摇一摇手中刚刚在街边买的白兰花轻罗小扇,眼波宛转,目光冷厉道:“我这一招‘犀牛望月’的破冰掌,送给你两下,一是惩你对我苗人不敬,二是罚你对我客人不尊。”
皇城司诸司使陆琪等于当众被一个女人扇了耳光,这让他恚恨难当,眼下处于下风,只好不能动怒发作,低声下气的地道:“我知错了,请各位姑奶奶高抬贵手。”
随行女护卫见安若曦使了一个神色,便横了陆琪一眼,上前一步,代为奚落道:“知错就要悔改,若是再出言不逊,我们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陆琪脸上无光,虽然不服,口中依旧忙答应道:“是、是、是,小的一定铭记姑奶奶的教诲。”
原本此事就此作罢。不料想,陆琪是一个睚眦必报之人,当他与皇城司的同伴汇合之后,心中亦是忿忿不平。相比之下,同伴似乎更在乎眼下没能如期找到罪臣之女的下落,能否顺利向上司交差的问题,便催促道:“你已经晚到了一盏茶的时间,让荆王殿下等候了,口里还在叨叨念念地啰嗦什么?”
陆琪面有不悦之色,带着几分惴惴不安,疾步走进了东风客栈的一间上房,拱手端行,行拜手稽首礼,恭敬道:“荆王殿下立而望之,下官却因事耽搁姗姗来迟,实在罪该万死。”
此人正是宋仁宗之子荆王赵曦,他头戴通天冠,身穿蟒龙袍,原本负手而立,见帘子被有人掀开,便端然坐下,身体微斜,面容在冠上垂落的白玉珠的映照下,显得颇有威仪,徐徐拨着怀里刻有龙纹的玉串饰,似笑非笑地道:“既然知道自己是罪该万死,就选一种死法,自行了断吧!”
陆琪心下骇然,连忙抱屈道:“下官该死。本应一切顺利赶到,不料途中遇见了有犯上作乱之嫌的蛮夷,才特意留神了一会儿,所以耽搁了时辰。”
荆王赵曦不以为然,微微一哂,呵呵道:“让你们找一个女人,你们几个大老爷们连续多日所谓的奔波劳累都不见有任何音讯,亏还是皇城司的人!这会儿倒有闲情逸致管蛮夷的事,真是一派胡言!”说着,他紧握手指,目光凌厉如箭道:“荥阳城毗邻京师汴梁,也算是地处半个天子脚下,有蛮夷犯上作乱?是讥讽我大宋二十万卫戍禁军是一群酒囊饭袋之辈?”
陆琪神色一僵,声音有些颤抖,仍然勉力地道:“请荆王殿下息怒,下官只是如实相告。虽说荥阳城距离汴梁不远,但是近日来借夏侯山庄大办及笄之礼,城里的确混进了不少蛮夷细作之人,来历不明,实属可疑。”
“你们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人,现在却给我闲扯这些我漠不关心的事情,以为渎职之罪就这样可以蒙混过关了?”来人慢慢摩挲着光洁的玉面,语气看似波澜不惊却渗透阵阵凉意道。
陆琪哑然片刻,郑重跪下,叩首道:“荆王殿下请明察,那女贼人冒充被抄家流放的罪臣之女,轻而易举地混入了教坊司,趁着入宫侍奉公宴佐酒的机会,悄然潜入了杨淑妃娘娘的慈元殿,盗走了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的明月珠,卫戍禁军虽然在第一时间封锁了京师城门加大排查力度,但还是让她给开溜了,可见心机之缜密,计划之周详。下官和兄弟们奉皇命一路从汴梁追到荥阳,也是尽心尽力,片刻不敢稍作耽搁,情况都及时飞鸽传书反馈给了大庆殿--渎职之罪,下官实属担当不起!”
荆王赵曦兀自浮起一个幽绝的笑意,慢慢摩挲着光洁的玉面,轻轻侧首道:“我母妃的心爱之物丢了,你们几个追查办事不力,还敢来父皇来压我,真是涨本事了!”
陆琪目光一缩道:“属下冤枉!淑妃娘娘的宝物丢了,皇上尤为牵挂,特派荆王殿下从昭文馆繁忙的事务中抽身出来追查,属下自然不敢有半点松懈怠慢。”说着,他故意顿了顿道:“皇上近日身体抱恙,接连招了几位皇子回宫,如果荆王殿下能够从中有所表现,崭露头角,加之皇上素日里对杨淑妃的宠爱,殿下的前程不可估量!”
荆王赵曦闻言一怔,心头微微一颤,似是入神思索了片刻,他知道所谓昭文馆繁忙的事务不过是整理历朝历代的残破藏书,掌书籍修写校雠之事,是个被边缘化名副其实的闲职。他也明白自己的母妃虽然深得宋仁宗的喜欢,但是性格淡泊宁静,素来不争不抢,难以主动为自己争取什么名利,于是舒缓了神色,把弄着手中的玉串饰敲着桌沿道:“你倒说说看,本王应该怎么个有所表现?”
陆琪以狡黠的目光投向他的质问,满怀笑意,躬身道:“夏侯宁波将于翌日举办千金的及笄嘉礼,邀请了不少江湖名流和宫廷雅士参加,还有一些南蛮北狄、西戎东夷赴宴,想必场景十分热闹。”
“哪有如何?有什么话就直接了当地说,不要欲盖弥彰。”荆王赵曦神色肃了一肃,手指笃笃敲在桌上道。
“自古讲究‘驱蛮夷而定四方’,咱们若是能够发现夏侯山庄有勾结蛮夷串通一气的蛛丝马迹,岂不是立了大功?让皇上另眼相看。”陆琪附耳低语道。
荆王赵曦双眉暗蹙,不屑回眸睇他一眼道:“那夏侯山庄又不是任人宰割的无能之辈,凭借捕风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就能招认这谋危社稷理当满门抄斩的大逆大罪?”
陆琪亦笑,极力压低声音道:“殿下应该有所耳闻,那夏侯山庄与凤阳阁有过往恩怨,多年来让长公主一直耿耿于怀。蛛丝马迹在咱们的手上自然不能成为铁证,可是若到了长公主那里,您知道凭借她‘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难保不会添油加醋把捕风捉影之事酿成实事--到时候,荆王殿下您就坐等皇上的加封吧。”
荆王赵曦点头会意,双眸微睐,颇有几分感慨道:“难怪堂堂的皇城司也会有办事不力的地方,原本是把心思和伎俩用在了尔虞我诈、满心算计上。很好,为本王分忧,本王日后一定不会亏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