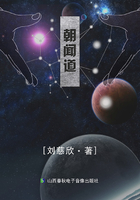《非常爱》 文\艾玛
选自《青岛文学》2012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艾玛:女,原名杨群芳,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澧县人。曾做过军校教员、兼职律师等。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小说多篇,我刊曾多次选发其作品。
1
文仲良看着美和,双眉微蹙,陷入沉思。
美和低着头,把菜一样样摆上桌。鸡皮笋汤,南瓜羹,葱花拌豆腐。两碗白米饭上点缀了几粒黑芝麻。
美和不敢看文仲良,文仲良的样子与其说是在沉思,不如说是在悲伤。文仲良自己察觉不到而已。
美和觉得人的衰老是从行动变慢开始的。美和知道此刻的文仲良比自己还要失望,他试图找到一种合适的语气和表情来抚慰美和,可是他找不着。他看上去简直有些可怜。
美和在文仲良对面坐下来,用汤匙舀出一小碗笋汤递给他。美和遇到文仲良后才开始跟着他吃素,一晃就是七八年。笋汤里有薄如蝉翼的笋衣,是美和这次远行唯一的收获。
“没有想到笋衣这么好吃。”美和用轻松的语气说。
美和的家乡梅家桥也有大片的竹林,但美和的家乡人只吃竹笋不吃笋衣。这次她到了安徽,发现笋衣卖得比竹笋还贵。尝过之后,才知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文仲良把一匙汤举到嘴边,停了片刻,又慢慢放了下来。
“那么,又是白跑了一趟啊。”文仲良忍不住叹气。
美和这一次去安徽,信息还是文仲良以前开律师事务所时的朋友老张提供的。文仲良抱着极大的希望,以为可以找到美和的儿子佳佳。最初美和追着一条条的线索来到这个原本陌生的城市,后来线索在这里断了,她失去目标,就在这座城市“漂”了下来。
找到佳佳已经成为了文仲良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他遇到美和的时候,美和已经找了十年的孩子,三十七岁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岁那么老。
那时的文仲良刚刑满释放。
在监狱里待了十年的他,由得意尽欢的不惑之年,平稳地进入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拎了个小行李箱回到空荡荡的公寓,他的妻子林一雯早已搬到了她自己购买的一套新居里。
她当然不会过来见他。
连一双儿女,文章与文馨,也是过了好几周他打电话过去,一雯才肯送他们在一个周末过来稍坐了坐。
文仲良知道这不能责怪他们。他盛年时的那些荒唐事,连他自己回想起来也觉难堪。
司机在楼下的汽车里等。孩子们穿着一所贵族中学的漂亮校服,端坐在他们儿时坐过的旧沙发上,仪容秀美,应答自如,好得超出了文仲良的期望——文仲良知道林一雯再次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蔑视——她到死都没有原谅他。林一雯去世前的一段日子,文仲良天天都要到她住的那所医院去,他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等着她答应让他去见她。他常常等到夜露把长椅和人都浸得湿湿的,最后总是文章出来劝他回家:“您要再病倒了,我可怎么办?”听到儿子满是无奈的话,他像个孩子,又悲伤又羞愧地转身离去。
现在孩子们都有很好的事业与生活。文章继承了林一雯的咖啡馆,文馨去了加拿大。林一雯走了,留在这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她让他感受到了失败,在他无力重来的晚年。有那么一段时间,文仲良觉得自己的余生简直就是在服另外的一个刑期。
但时间也是这人世间的魔法师。
曾几何时,文仲良以为自己很快也会死掉。可是,就像一架老破车,看上去随时随地要散架的样子,转过头来,却又吱吱嘎嘎跑了好些年。
两个人吃过饭,美和把桌子收拾干净了,沏了一壶茶。茶是美和从安徽当地买的。她还给文章和老张各买了一袋。“今年的春茶,看着炒好装袋的,炒的时候,香得差点让人哭出来。”美和说。
“哦。”文仲良看着美和,平常她很少使用这样夸张的语气。
“我已经和那边说过了,以后不用给我打钱了。”
文仲良一时没有明白美和在说什么。
美和手拿一块纸巾,埋头来来回回擦拭着桌面上的水渍。美和说:“……佳佳的爸爸还有别的孩子要养。”
文仲良明白过来。
美和的前夫每年都会给美和一笔钱,作为寻找佳佳的一部分费用。美和告诉前夫不用给她钱了,难道是说她不打算再找了吗?实际上如果美和愿意,自己也是可以给她一些钱的。但文仲良隐约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他们在一起后的这些年,只要有比较确切的消息,文仲良就会给美和买好来回的车票。美和也出去找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去安徽,倘若不是认为有比较大的把握,文仲良决不会忍心让她跑这一趟。没想到依然是无功而返、徒增悲伤。
美和把额前的头发往后一推,露出一片雪白的发际。她抬起头看着文仲良,泪流满面。
美和说:“佳佳今年二十三岁,是个大人了,从现在开始,就让他来找我吧。”
2
四月末天就热了起来。也不知是天气的缘故还是失望劳累所致,美和病了几天。文章得知后,打电话叫文仲良过去住,文仲良谢绝了。文章的媳妇叫爱更,是个娇滴滴的韩国姑娘,动不动就“欧巴,欧巴”地跟文章撒娇,文仲良到了这年纪,光是目睹这样的场面就已觉难堪。
况且,他和孩子们之间,是客气多于亲热的。对这个儿子,他心里甚至是有些憷的,儿子再怎么不好,也没有把自己弄得身陷牢狱、妻离子散。
不过,在电话里对文章说不过去了,放下电话的一瞬间,文仲良似乎听到了文章的轻笑。
文章这样年纪的男人,正是处在对男女之情豁达而又轻慢的年纪,他们有的是恣意妄为的资本……他该如何猜想自己与美和呢?
文仲良放下电话,因为羞恼脸不禁有些发烧。电话旁边的一面小圆镜子清晰地映出了他的表情,面颊上几小块老年斑的颜色也因此加深了,感觉像一块块污迹。窗外的一株双樱却开得正好,花朵累累垂垂,有果实的质感。
林一雯很喜欢樱花。记得附近一所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棵双樱,树高两层,开起花来,一棵树就撑起了一个盛大的场面,垂委及地的红花像瀑布一样,让人叹为观止。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年到樱花盛开的季节,他都会抽空陪着林一雯去市内各个景点看樱花。他们也去过那所大学。文馨都上幼儿园了,两个人还手拉着手,面对着一树樱花在校园的一张长椅上一坐半天。
到了后来,更能触动他的却是单樱。单瓣樱花开得比双樱早,花期短,在薄寒的春色里匆匆,像个凄美的吻……颜色是雪也似的白,远看是轻的,比云彩还轻薄的质感,风可以吹走的那种。刚和一雯分开的时候,有一个雨天,他孤身一人走到路上,路旁有几株单樱正值花期,只见满眼清澈的白,湿淋淋的白和无声的轻柔坠落……
窗台边的书桌上有一张多年前的全家福。照片里的他和林一雯十指紧扣,很幸福的样子。文馨刚会走路,与文章一起偎依在他们身边。
美和每次擦拭书桌,都会拿起照片端详,说:“多好看的一家人。”
好看得不像是真的。文仲良时常觉得照片里的美好与幸福不过是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梦。尤其是到了现在的年纪,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照片里的文章,还像个小女孩似的,天真烂漫,眉目清秀。现在的文章,已年过而立,额头的发际线,不知不觉往上走了些许。
出门散步,文仲良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走到文章的咖啡馆去,隔着一条马路站在那,远远地看上一眼就好。咖啡馆总是很安静,坐在里面的那些人,也很安静。文仲良很放心。作为一个父亲,文仲良知道自己永远错失了将儿子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机会。文章考大学、就业,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候,他倒是恢复了自由身,可那时候,他不像是刑满释放回来的,倒像是来自外星球,什么也不会,什么都看不懂,而且,还怕。在监狱里包装了十年牙签后,除了见到牙签不怕,看见什么都怕得要命。怕出门,怕跟人说话,怕过马路,怕孩子说错话,怕孩子过马路……好在后来遇到美和,与其说是他帮着她找孩子,不如说是她帮着他找自己。
这世上的每个父亲应该都有些可以与儿女分享的人生经验。文仲良时常问自己:你啊,有什么可以与孩子们分享的呢?
3
美和挣扎着起床料理家务,文仲良连忙制止了她。他打电话到爱心家政社叫了个钟点工。美和的样子让他觉得心酸,因为生病她显得非常内疚,好像她犯了个大错。站在她的处境想一想,就会觉得她非常可怜——连病也不敢生。
钟点工逄姐和美和差不多大的年纪,但性情与命运都相差了很多。逄姐的丈夫是公交公司的司机,儿子在日本留学。逄姐的嘴里少不得老公儿子。
逄姐把一盆子衣服端到美和的床边,一边洗衣服一边跟美和说话。
“……交了班,不管多晚,人家什么也不管,先到小红莓喝一杯,多晚我也等啊,年轻的时候啊,傻。现在可好,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怕儿子知道呕我了……怎么,你要喝点水的么?”
见美和挣扎着坐起来,逄姐连忙站起来,提着两手的肥皂泡走到床边去。
美和听到人说儿子,眼睛里有了异样的光亮。
文仲良简直不忍心看下去。
他走到书房,给老张挂了个电话。下午老张正好有两个小时的空当,文仲良便约他到附近的莲花阁喝茶。老张名叫张敬堂,满世界的人,大约只有文仲良叫他老张,别人都是叫他张老的。
老张步履矫健,染黑了头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六十多岁的人。
他们是同一年从大学毕业的,老张是工农兵学员,比文仲良年长两岁,至今仍活跃在律师界。老张身上有着名目繁多的头衔,除了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以及各类公司与组织的法律顾问,他还担任着市律师协会理事长、省书法协会理事等职。当然,他已经很少亲自出庭办案子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有老张的意义,好比一个国家有了核武器,哪里能三天两头拿它打东打西?不过是镇镇宅,充充底气罢了。
看着老张步履轻快地向自己走来,文仲良想狱中的十年可真不是白过的啊。
文仲良与老张寒暄起来。老张忙,与文仲良有一阵没见面了,文仲良现在过着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晚年,除了通报各自的身体状况,老张能跟他说什么呢?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今非昔比啊,现在律师这行是越来越难做了。”老张敲着桌子,感叹道:“我这一生,最难忘的还是与你共事的那些年。”老张说。
文仲良笑而不语。
两人合作过的最为成功的案件是那宗轰动一时的枪下留人案。那是二十多年前,他们一起承接了一宗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被告方的委托,在一二审都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两人没有放弃,直奔最高法院申请复核。最高法院刑庭在审核了他们对一二审一份关键证据的质疑后,紧急签发了暂停执行死刑的通知。两人一案成名。也正是通过这个案子,他们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友谊……后来的文仲良时常觉得自己的一生,事业也好爱情也好,开头都太顺利了一些。
文仲良拿出美和为老张买的茶叶,说:“比不上你常喝的,也还算不错。美和的一片心意。”
老张沉默了一会,说:“美和还好吧?要她别灰心,慢慢找。”文仲良点点头。多年的职业习惯使然,像他们这样的人,即使是被逼到了悬崖上,明知死路一条,但也绝不会把话说死的。
4
从茶馆到家里,步行也就是半小时的路程。文仲良顺着海滨步行道,竟慢慢走了一个多小时。
海边有很多垂钓的老人,他们衣着简朴、面色黧黑,安静地搁在膝盖上的双手骨节突出、多皱而厚大。大多是一辈子以海为生的人。
市内各区规模不小的老年大学与他们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文仲良走两步,就会停下来看看钓鱼者身边的小水桶。那些老人一坐半天,所得不过是三五条半拃左右的小黄花、小黑头。
时光往后溯十来年,退潮的时候在海边的礁石滩上,随便哪个小水坑里都能摸到比这还要大点的鱼。很难想象大海已变得如此贫瘠。
不过钓鱼的老人们似乎并不感到沮丧,他们个个面色坦然,向着平静的大海默然而坐,相互之间相隔丈许,鲜有交谈。
隔着一片并不开阔的草地,老人们背后的马路上车如流水人如织。有风吹过,路旁的樱花树就如惊扰了群群粉蝶,翩翩不绝、活色生香。
文仲良觉得这些沉默的垂钓老人更像是自己的先导,指引着他要把无与伦比的鲜活世界彻底置于身后。他们与众不同。
除了佳佳这件事,自己也许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文仲良想。而老张呢,似乎有些冬行春令。
不过人各有命,老张这一辈子也许就是一支从强弩上射出的快箭,注定是要带着一声巨响,“嘭”的一下直射到终点的。
而他们原来是如此相像。文仲良想不起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变得不一样了的。也不能说就是在狱中。
5
晚餐的时候美和起来吃了一点小米粥。在灯光下她看上去瘦了不少。
“我跟逄姐说,做完这一周就可以了,正好前栋孙家也需要一位做白班的月嫂,他们已经谈妥了。”美和对文仲良说。
文仲良唯有点头。
安徽之行,美和并没有吐露多少。
即便如此,文仲良也能体察到美和的心情。
就像自己,最初和一雯分开的时候,也痛,因为还是幻想着有从头再来的一天,所以这痛,不过是痛。直到有一天,在狱中,他和一位也在服刑的前副市长下棋,下到一半,前副市长举棋不定,过了半晌,颓然将棋子一扔,叹道:“……覆水难收啊!”——说的何止是棋?
这一语也熄灭了文仲良心头的幻想,文仲良只觉得霎时间心如刀绞。
“从现在开始,就让他来找我吧!”
文仲良想起美和泪流满面说的这句话。
美和觉得自己是要放弃儿子了,所以才会落泪,放弃之痛,应该是比找而不得的失望来得更痛的吧。在她年近五十的时候,她要放下寻找儿子的念头,才能重拾过上正常生活的勇气,生活对她也未免太残忍了。
“……买他的那家人也穷,就上到初中,十五岁就开始在小煤窑打工了,现在差不多和佳佳的爸爸一样高。我带着他去县城,赶去合肥的最后一趟班车……他就在路边的小水沟里把脸上的煤灰洗了洗……很俊的,可惜亲子鉴定却不是。”美和曾在回家的当天一边整理带回来的东西,一边跟文仲良这样说。当时她的语气很平淡,但声音却一点点地低下去。
文仲良喝了一口海带汤,豆酱稍微放多了点,汤水从舌尖上滑过生出了一丝涩麻。人随着年纪渐长,所有的器官似乎都慢慢进入半休眠状态,唯有味蕾和脾气醒着。银行和酒店等一些服务场所时常能见到觉得受到怠慢而大动肝火的老人,而电视里美食栏目的专家也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就是这个缘故吧。
文仲良也是到了知天命之年,才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认识的。年轻的时候,旺盛的生命力需要丰富的食物来喂养,而且,什么东西吃下去这身体都如饮甘露。现在呢,过多的食物对身体与其说是营养,不如说是负担,它们只会让身体散发出浑浊的气味。身体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在不知不觉中减少着它的需求,而活在这身体内的灵魂也因此变得简单、宽容。食物似乎也会改变人的表情,文仲良每每不经意路过镜前,驻足端详,也会为自己脸上日益增加的安静从容打动。
老张曾传授保养秘诀,每天必食一只海参,一小杯张裕卡斯特干红。但在文仲良看来,这未免太过刻意而且奢侈。
一箪食、一瓢饮,足矣。
文仲良喝着汤,想起刚才在回家的路上遇到逄姐的情形。他走到楼下时,恰好逄姐从楼道内出来。逄姐手里拎着一袋垃圾,她往一边让了让,对文仲良说:“文先生,晚饭我做好了。”
逄姐停了停,又说:“……您快上去吧,她,好多了。”逄姐似乎在犹豫,该怎么在文仲良面前称呼美和。
逄姐最后用了一个“她”。就是这一个“她”,让文仲良再次想到他与美和的关系。
在他们生活的这个海滨城市,老年人再婚的比例很高。为了使双方的子女不至于在那个虽不可预见、但绝不遥远的将来因为财产对簿公堂,大部分再婚老人都放弃了法律上的名分,选择了同居的方式。更有一些有经济能力的老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更中意那些处于经济弱势的农妇和下岗女工,女人以保姆的名义与老人生活在一起,照顾老人的日常起居,他们付给这女人比保姆略高的薪水。金钱使老人与女人间的关系变得极其简单,一旦老人过世,老人的子女无须费甚口舌,就能轻易地将这女人扫地出门。
大约这类经济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不公事关颜面与体统,有地方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禁止保姆陪睡”。文仲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就觉得此举简直就像那些个操心不当、霸道有余且粗俗浮躁的家长所为,且不说这种规定隐含的对保姆这个行业的歧视,单就法的效率来说也是极其之低的。这种规定既不能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也不能对被侵害者给予保护,更无法起到禁止性规定所应起到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大概只会让本身处于弱势的一方倍添羞辱——根本就像是一句毫无道理的呵斥嘛。
也许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让美和也感受到了这种羞辱。文仲良不免这样想。
6
是谁说过,青春消逝后的人,需要时不时的小睡。文仲良发现自己常常就能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傍晚的时候,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文仲良。他听到美和急急地从厨房奔向客厅的声音。本来是在阳台上看《芥子园画谱》,不知怎么就睡着了,书掉到了地上。
美和对着电话听筒说:“等等啊……”她把听筒轻轻搁在桌子上,疾步走到阳台上替文仲良把书捡了起来。是从什么时候起,文仲良发现自己连弯腰这样的动作也做不来了。大半辈子都是弯着腰过来的,先是在法官面前、在委托人面前、甚至是在一雯面前,后来是在狱警面前、在儿女面前……老了老了,骨头倒真的硬了。
电话是老张打来的。两人寒暄了一阵,通报了各自的血压与睡眠情况。老张说:“……开着会呢,睡着了,到了晚上,倒躺在床上听了一夜风声。”老张的语气里平添了一丝凄凉,似乎萌生了退意。文仲良想,老张怎么也算得上是功成身就,一直河边走,未曾湿过鞋。干这一行的做到这个地步,又有这样好的结局,实在是不太多。文仲良想起海边的垂钓老人,想也许过不了多久,自己和老张就都可以加入到他们中间去,面向大海,比肩而坐,鲜有交谈,却知心知肺。
“你还记得,她吗?”老张的声音突然变得迟疑起来。
“谁?”
“听说,她,出家了,已经十多年了……”老张的声音低下来:“她那样的一个人,也会出家?”老张像是在问文仲良,又像是在问自己。
文仲良怔住了,握着听筒的手微微颤抖起来。
“你是说……江、江云?”
老张没有说话,一阵沉默过后,他轻轻挂掉了电话。
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嘟”的声音,文仲良的眼前出现了一双水蒙蒙的眼睛,这双眼睛眼梢上掠,宛若惊鸿,流光溢彩、却又似愁还悲。
7
文仲良时常想,最初,如果自己没有去律师事务所,而是一直待在司法局综合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会一辈子坐在一张松木办公桌后面,喝茶,看报,平安到老。
也许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也许会像别的男人那样,喝个小酒打个小牌,和办公室新分来的女大学生暧昧暧昧,但是就像水不管有多千奇百折,终归要流入大海一样,他一定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将婚姻这艘小船平稳地划向人生的终点。他和林一雯两个人,也许会在越来越平淡的日子里心平气和、毫无遗憾地老去。
可是,命运是不可以假设的。
他是在到律师事务所的第三年碰到江云的。那时候他和老张刚刚办完那桩枪下留人案,尽管最高法院经过复查,最后还是核准了他们委托人的死刑判决,但他和老张还是因为这起案件而声名大噪。自清末以枪决取代斩首以来,“刀下留人”的传奇有年头没上演过了,人们因此很是兴奋了一阵。那时他和老张都在睿智通达的中年,有着挺拔的身姿,如火如荼的事业。初战告捷后的他们,眉宇间不免有仗剑四顾、舍我其谁的熠熠神采。
文仲良还记得那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在办公室里看一个案子的卷宗,老张没有敲门,直接就推门进来了。身后跟着的就是江云。
他第一眼看见江云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了一种要窒息的感觉,她整个人,就像盛开的热带花朵,艳丽的色彩,火辣辣的气息,处处刺激人的神经。他简直有些呼吸不畅。他后来为她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因为她的引诱,不如说是出自他对她的讨好。一开始老张和他一样昏了头。他们以为自己是英雄,救得了落难美人。
老张是个聪明人,发现江云牵扯到七号别墅时,马上挥剑斩情丝,抽身而出。江云名下的七号别墅是栋历史悠久的老别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共两党的首脑人物都曾在这里小住过,推门出去就是一小片沙滩,风景美不胜收。江云提供的买卖合同漏洞百出,老张不愧是老张,一看合同已知是怎么回事,谁敢卖七号别墅呢?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到。江云跑来咨询买卖合同的问题,无非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做点暴风雨来临前的准备,好使自己对七号别墅的拥有合法化。换个人,早就要闻风丧胆了,可是江云,就有种在那图谋丢帅保车。这水不知道有多深!老张想明白过来,不禁大汗淋漓。
老张拉着文仲良去市京剧院看《四进士》。他们原本对京剧都不甚热乎,但却也都知道《四进士》,“一出四进士,半部大明律”。剧中宋世杰是个足智多谋的讼师,凭着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在知府杀气腾腾的公堂上救民妇杨素贞于水火。
“江云不是杨素贞!”老张意味深长地对文仲良说,“再说,几千年来,也就这么个成功的个案。”
文仲良很固执地认为,在与政府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个人总是处于弱势,无论如何,都值得一争。他以为至少可以像枪下留人案一样,在一成不变的旧习里撕开一道口子,好吹进些新鲜的风来。当然,除了这个正大磊落的原因外,他也不能否认,他的内心里也暗涌着一股英雄救美的豪情,那是每一个男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心内悄然滋长的豪情。
文仲良后来明白,律师不过就是有点辩才,挑动得了什么?可惜那时候他又能听得进什么呢!他太相信江云,也太相信自己,自以为两脚都踩在合法线内就可以了,可有时候那条线在哪里,谁又能说得清?最后的结果很讽刺,江云全身而退,交回别墅了事,进去四个人,一个副书记、一个副市长、一个国企老总,加文仲良一个小律师,果真是“四进士”。前三个人贪污受贿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七号别墅对他们来说只是无足轻重的一个细节,而他,一跟头全栽在这个细节上。
后来,文仲良也常常问自己,那阵子,他是因为不爱一雯了才陷入江云的温柔乡的吗?每一次,他都很肯定地回答自己:不是这样的,不是!他爱一雯,从来就不曾改变。只不过,江云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总能轻易把她周围的男人都点燃,他没能幸免。这是他不如老张的地方。曾有一阵,每每想到这件事,文仲良就不免又羞又愧。
不过,对于江云出家这件事,文仲良倒没有觉得多诧异,不像老张,感叹连连。
一团火,烧到最后,可不就是灰么!
8
夜晚来临,隔窗可以看见一轮明月,高悬在窗外的夜空中。文仲良无心睡眠。躺在另一张床上的美和悄没声息的,但文仲良知道她一定也没有睡着。
文仲良问道:“……你和佳佳的父亲,分开是因为佳佳这件事么?”
他几乎不曾问过美和关于佳佳以外的事,这个夜晚,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美和生命中的这个男人……他们一定也是相爱过的。有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却丢失了。美和到了这里,那么,那个男人呢?他有了新的家,过得好吗?文仲良突然很想了解这个男人,好像这个男人,是他的一个知己,他似乎感觉到这个男人,内心里一定有一种伤痛,就像他一样,正是这种伤痛,冥冥中会使他们彼此懂得。
美和沉默着。自从前两天文仲良提议去结婚登记以来,她很少说话。
文仲良侧过身去,看着洒落在窗台上的皎皎月光。不知过了多久,美和轻轻说:“上午你去书画院看画展的时候,爱更来过了。”
晚饭时有一碗泡菜豆腐汤,文仲良就猜测到了。爱更是个好儿媳,隔三差五地送自己做的泡菜和黄豆酱过来。这样的女子,会给公公送吃食的女子,在现在的中国似乎很难找到了。爱更的中文说得颠三倒四的,文仲良和这个韩国媳妇几乎没有什么交谈。不过他对她的印象很好,她非常善良,对美和很好。还有她约微有些扁平的圆脸,她对文章毫无戒备的孩子似的依恋,都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爱更的眼睛红红的,两个人,似乎是……”美和叹了一口气。
文仲良只觉得心头一沉。他和儿子之间,一直缺一场畅谈。他进去的时候,文章还很小,等他出来,文章又是在最忙碌的高中阶段,接着上大学,继承一雯的事业,很平稳地过来。文仲良觉得这后半辈子,他一直都在寻找一个机会,寻找一个能跟儿子说几句心里话的机会,关于过去,他欠着孩子们一个交代……他憧憬着他们可以像别的父子那样,默契,话不用太多,三言两语,彼此就心领神会。
“头一年是怎么过来的,我都忘了……”
一阵沉默过后,美和幽幽开口道。
“年底我们得到一条信息,说是佳佳有可能在山东郯城一个叫阳集的村庄里。好容易等到学校放假——那时梅家桥小学就我们两个老师,他教数学、体育、美术,我教语文和音乐——我们带上所有的钱还有干粮往山东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徐州,再从徐州坐七个小时汽车到郯城。进入山东境内天开始下大雪,我们辗转赶过去……并不是。大年三十那天的傍晚,我们返回到郯城县城,在一个小旅馆住下来……雪下得很大,不时有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他打了盆热水给我洗脸,然后他出去了。”美和拥着被子半坐起来,继续说,“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回来的时候,头上衣服上全是雪,他手里拿了包东西,他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倒了两杯开水,他打开那包东西,是包酱猪蹄。他笑着对我说,美和,过年了!”
两个寻子未得的人,在异乡,大雪纷飞的除夕夜,还有这包酱猪蹄,很可能还是费了不少劲才弄来的……这让文仲良感到酸楚。
“他说,美和,过年了!”美和停下来,问文仲良,“你猜我对他说了些什么?”
“你一定很伤心……”文仲良说。
美和沉默了一会,黑暗中她发出一声低笑,这笑声颤颤的,听上去让人心碎。
美和说:“你猜对一半,是的,我很伤心!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而我的佳佳,此时此刻,不知道在哪里,穿得暖不暖,吃饭了没有,有没有哭,所以当他说美和,过年了——”美和再次停下来,声音变得比风还轻,“我噌一下站起来,说你把孩子驮在三轮车上去镇上,驮出去的是孩子,驮回来的是袋土豆,你连孩子和土豆都分不清,你怎么还有心吃肉?有心过年?”美和的声音像被鞭打了一样哆嗦起来:“我把猪蹄和水杯都扫到地上去,对他喊道——你!为什么不去死啊?”
文仲良坐起来:“美和!”
“是的,我对他喊,你为什么不去死?”美和哽咽着,“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样子……你知道吗?后来我有多感谢他没有去死!感谢他回到梅家桥小学去给孩子们上课,感谢他后来又结了婚,还有了孩子!”
文仲良披衣起身,走到美和的床边坐下,他握着她的一只手,默然无语却满心酸楚。他和美和的经历不同,但某些方面却惊人地相似。他们婚姻的解体或许都是因为爱得太深,如果没有那么深的爱,也就不会有那么深的伤害。文仲良静静地握着美和的一只手,就像是她一个同病相怜的朋友。他想到了一雯……一雯推开门,站在门口,怔怔地看着他,一步步向后退去,满眼都是心碎。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看站在文仲良身后的江云一眼——这一幕是文仲良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他不免感叹婚姻就像饮水,这水的温度要刚刚好,太冷、太热都不能畅饮。和一雯分开后的一段时间,他也曾无数次幻想过,如果那时一雯爱他没有那么深,只爱他一点点,就一点点,该有多好!
他没有恨过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9
文仲良打电话约文章吃饭。
“就我们父子俩。”他对文章说。
文章在电话里有些迟疑地:“有什么事吗,爸?”
“见面说吧,老地方。”文仲良飞快说道。
“电话里不能说吗?”文章似乎很忙。
“如果你有空,还是见一面吧。”
“那好!”文章很快就答应了。
放下电话的一刻,文仲良想,好在一雯把孩子们都教得很好,他们都有很好的教养,能给一个失败的父亲恰到好处的尊重。
文仲良换了件半新不旧的风衣出门。美和送他到门口,她看了文仲良一眼,脸上生出一片淡淡的红晕。美和低着头说道:“请不要和文章谈结婚的事。”
“放心吧,不是这事,只是跟孩子聊聊罢了。”
前一晚的夜谈,敏感的美和似乎觉察到了文仲良会和儿子谈起他们的事情。美和不愿意和他结婚,是充分体谅到他的处境。在他这个年纪,他们之间的这种状态,对他来说并无什么不便。人生暮年,总是减法做起来更轻松。
文仲良下楼往附近那家茶馆走去。他打算立个遗嘱,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给美和。万一哪天他离开了,美和要住到哪里去?佳佳最后确切的线索,就是在这座城市,美和大约不会活着离开这里的了。跑得动的时候,她总是在寻找,现在跑不动了,她便开始了等待。梅家桥,没有佳佳,她是再也回不去的了。给美和一个可以安心等待儿子的地方,是文仲良能为美和做到的事情。但文仲良不知该怎么跟文章说。可是,迟早要跟他说的。他没有给过孩子们任何东西,这套房子,虽然不值什么钱,也还是一雯留给他的,当时她就是什么都不留给他,他又能说什么?
没想到文章倒是很爽快。
“您写个遗嘱,留给阿姨不就行了嘛,文馨也不会有意见的。”文章还带了包点心,“咖啡馆里刚换了个西点师,意大利人,做得很不错,爱更包好了让我带过来。”
文仲良喝了口茶,把杯子放下后,很郑重地对文章说:“对爱更,要好。”文章笑了:“她在阿姨面前哭了?哎呀,有什么,下次去她又该笑了。”
“你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有些错……”文仲良一下变得笨嘴拙舌起来,“你不知道,我和你妈妈……那时候你还小,我……”他用一只手在桌上摸来摸去,不知该从何谈起。
文章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看着文仲良。这还是文仲良头一次跟他说到那件事。
文仲良也看着儿子。文章的表情,似乎他也一直期待着这一刻。
文仲良满腹歉意,思绪万千,一时语塞。这个场景想象了很多次,结果却是这样。父子俩一时相对无语。过了一会,文章伸出一只手,握住了文仲良那只搁在桌子上的手。
“爸。”文章轻声叫道,“您不用说,我都知道。刚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害怕过。不过好在有妈妈。妈妈去世前,全都对我说了,我知道。”文章使劲将文仲良的手握了握:“这也是人生。”
儿子的手很大很有劲,文仲良的眼眶慢慢湿了。林一雯去世后,他得以进入她的病房去跟她告别。她表情安详地静静地躺在那。他看着她,心如刀割,痛得不能自已。那一刻,她的安详让他恨极了她。自始至终,她连个说声对不起、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给他!
“你妈妈,怎么跟你说的?”文仲良听到了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就好像再次站到了被告席上,等着聆听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宣判。
“妈妈说,”文章微微一笑,模仿着林一雯的语气说道,“现在想来,你们的爸爸,真糊涂啊!书生意气,心肠呢,又太软!”不光语气,说这句话时的文章,连表情竟都有些像一雯。
原来是这样!
就像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赦免,文仲良浑身哆嗦着,把多皱的窄窄的额头抵到了儿子宽厚的手背上。
原刊责编 高建刚 本刊责编 鲁太光
责编稿签:读完这篇小说,留给我的,只有一个意象,那就是樱花,飘荡的樱花,飘洒的樱花,飘扬的樱花······这飘飘荡荡、飘飘洒洒、飘飘扬扬的樱花,把一树树美丽飘荡成一树树哀愁,把一片片温暖飘洒成一片片萧瑟,把早春飘摇成清秋······因为,这在文本中飘零的何止是樱花啊,那就是主人公的的心花啊,是他们非常爱非常恨非常罪非常美的心花啊。在这漫天的樱花中,我们以为一切都落花流水春去也。幸运的是,作者在小说结尾用一段轻柔的细语拯救了主人公的心情,也拯救了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在这飘零的故事中又读出一些春的意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