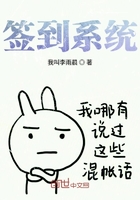正二月间城里赛龙灯,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还要算邻近各村上的女人,她们像一阵旋风,大大小小牵成一串从这街冲到那街,然而能够看得见三姑娘同三姑娘的妈妈吗?不,一回也没有看见!锣鼓喧天,惊不了她母女两个,正如惊不了栖在竹林的雀子。鸡上埘的时候,比这里更西也是住在坝下的堂嫂子们,顺便也邀请一声“三姐”,三姑娘总是微笑的推辞。妈妈则极力鼓励着一路去,三姑娘送客到坝上,也跟着出来,看到底攀缠着走了不;然而别人的渐渐走得远了,自己的不还是影子一般的依在身边吗?
三姑娘的拒绝,本是很自然的,妈妈的神情反而有点莫名其妙了!用询问的眼光朝妈妈脸上一?,——却也正在?过来,于是又掉头望着嫂子们走去的方向:
“有什么可看?成群打阵,好像是发了疯的!”
这话本来想使妈妈热闹起来,而妈妈依然是无精打采沉着面孔。河里没有水,平沙一片,现得这坝从远远看来是蜿蜒着一条蛇,站在上面的人,更小到同一颗黑子了。由这里望过去,半圆形的城门,也低斜得快要同地面合成了一起;木桥俨然是画中见过的,而往来蠕动都在沙滩;在坝上分明数得清楚,及至到了沙滩,一转眼就失了心目中的标记,只觉得一簇簇的仿佛是远山上的树林罢了。至于篎篎的喧声,却比站在近旁更能入耳,虽然听不着说的是什么,听者的心早被他牵引了去了。竹林里也同平常一样,雀子在奏他们的晚歌,然而对于听惯了的人只能够增加静寂。
打破这静寂的终于还是妈妈:
“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猫跳!你老这样守着我,到底……”
妈妈不作声,三姑娘抱歉似的不安,突然来了这埋怨,刚才的事倒好像给一阵风赶跑了,增长了一番力气娇恼着:
“到底!这也什么到底不到底!我不欢喜玩!”
三姑娘同妈妈间的争吵,其原因都出在自己的过于乖巧,比如每天清早起来,把房里的家具抹得干净,妈妈却说,“乡户人家呵,要这样?”偶然一出门做客,只对着镜子把散在额上的头毛梳理一梳理,妈妈却硬从盒子里拿出一枝花来。现在站在坝上,眶子里的眼泪快要迸出来了,妈妈才不作声。这时节难为的是妈妈了,皱着眉头不转眼的望,而三姑娘老不抬头!待到点燃了案上的灯,才知道已经走进了茅屋,这期间的时刻竟是在梦中过去了。
灯光下也立刻照见了三姑娘,拿一束稻草,一菜篮适才饭后同妈妈在园里割回的白菜,坐下板凳三棵捆成一把。
“妈妈,这比以前大得多了!两棵怕就有一斤。”
妈妈哪想到屋里还放着明天早晨要卖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妈妈的帮忙,妈妈终于不出声的叹一口气伴着三姑娘捆了。
三姑娘不上街看灯,然而当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过了多少次的,所以听了敲在城里响在城外的锣鼓,都能够在记忆中画出是怎样的情境来。“再是上东门,再是在衙门口领赏,……”忖着声音所来的地方自言自语的这样猜。妈妈正在做嫂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欢喜赶热闹,那情境也许比三姑娘更记得清白,然而对于三姑娘的仿佛亲临一般的高兴,只是无意的吐出来几声“是”,——这几乎要使得三姑娘稀奇得伸起腰来了:“刚才还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实在是站起来了,一二三四的点着把数,然后又一把把的摆在菜篮,以便于明天一大早挑上街去卖。
见了三姑娘活泼泼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为什么那样没出息,不在火烛之下现一现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的呢?不,——倘若奇怪,只有自己的妈妈。人一见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同三姑娘的菜,其余的什么也不记得,因为耽误了一刻,三姑娘的莱就买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这样好,隔夜没有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里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后留给我的印象,也就在卖菜这一件事。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旧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式,不过这也不能够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过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三姑娘在我们的眼睛里同我们的先生一样熟,所不同的,我们一望见先生就往里跑,望见三姑娘都不知不觉的站在那里笑。然而三姑娘是这样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闹便愈是消灭下去,等到我们从她的篮里拣起菜来,又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了铜子,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终是很习惯的,接下铜子又把菜篮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卖青椒。这时青椒出世还不久,我们大家商议买四两来煮鱼吃——鲜青椒煮鲜鱼,是再好吃没有的。三姑娘在用秤称,我们都高兴的了不得,有的说买鲫鱼,有的说鲫鱼还不及鳊鱼。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
我们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三姑娘是不吃我们的饭的,妈妈在家里等吃饭。我们没有什么谢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将来碰一个好姑爷。”
我这样说。然而三姑娘也就赶跑了。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雾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
那妇人的话也分明听到。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
1924年10月
【作者介绍】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废名是他的笔名。湖北省黄梅县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入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同年加入“语丝社”。192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抗日战争以前,废名在北京学习和工作了15年。其中有5年是在西山的一个村子里度过的。这时的创作除了写故乡黄梅城乡以外,还写了北京的城乡。这时期,废名创作了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散文《枣》、《北平通信》等等。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回乡教学以避难。在此期间,废名几乎停顿了他的文学事业,与文学界也断了联系,只写了几篇短文。抗战结束又重返北大,这时期写了总题为《父亲做小孩子的时候》的一组文章,还有《五祖寺》、《散文》、《教训》、《打锣的故事》、《放猖》诸篇文章。1953年,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教。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废名以特立独行而名世。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都有独特的眼光和思考,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奇特的风格。他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是在小说方面。就其本质来说,他是一个诗人,从其表现来说,他又是一位散文家,他有不少的小说与散文几乎无法分别。但实际上,废名的散文创作和小说创作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他的散文有其自己的特点、笔法和情调。
属于语丝派作家的废名,在小说的创作上给他直接影响的,要数与他同时期的语丝派的周氏兄弟。在鲁迅的影响下,废名的小说,也执意描写乡村社会中人们的不幸遭遇和苦难,在乡土风情中隐现哀怨忧郁的色彩。废名小说恬淡清新的诗意风格,则主要是受周作人平和恬淡的小品文的影响。在小说里,他着重描写乡村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往往抓住生活中的某一个角落、场景、镜头、片断进行精雕细刻,抒发含蓄、自然、朴实的情感,在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中捕捉美,流露出他对田园生活的眷恋。
废名的作品,尽管其选择的角度和处理与众不同,但他究竟还是在写人生,写对人生的思考。读了他的作品,就会从中深深地感悟到他所描写的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是那么的丰富多彩,那么的深刻和生动。小说《竹林的故事》是废名的成名之作。他还创作了《桥》、《柚子》、《菱荡》、《浣衣母》、《桃园》等小说;散文有《州》、《万寿官》、《沙滩》、《枣》、《碑》等。
【阅读提示】
废名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田园派小说家。《竹林的故事》发表于1925年2月《语丝》第14期,最能代表废名小说的风格,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初期最富有诗情和青春气息的作品之一。小说以平淡质朴之笔描写了具有浓郁情调的农村生活。
作者以凝练而有才情的笔写竹林,写茅舍,写菜,写少女,触笔之处皆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象。其中尤对竹林写得最有灵气。河边葱茏的竹林好像是专门为三姑娘生长的。三姑娘也好像是专门为这片竹林生长的。她们之间达到了一种诗情交融的境界。竹林下有三姑娘的幸福与哀愁,她在这里唱歌嬉戏,帮父亲捉鱼,帮母亲买盐,尤其是“三姑娘在水边,头毛低到眼边,才把脑壳一扬,不觉也就瞥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顿时兴奋起来,然而立刻不见了……突然一声,呵呀!这回是一尾大鱼!”,这里活脱脱地表现出那个天真活泼,带着青春气息的三姑娘形象。竹林里又蕴藏着三姑娘的青春和性格。三姑娘很能干,八岁就能替妈妈洗衣,她也很懂事,父亲死后,她不愿离开妈妈,乡亲们成群地到城里看赛龙灯,她淑静得宛若栖在竹枝的雀子,锣鼓喧天也惊动不了她,只像影子似的伴着妈妈,即使妈妈鼓励她去,她也以“我不喜欢玩”作理由而拒绝。这里,一个孝顺懂事而又不失纯真的葱茏竹林里的小姑娘形象跃然纸上。三姑娘还如竹一般“直”,使得人们拿铜子买菜也似乎觉得俗气。是呀,三姑娘已经十二三岁,就是穿着淡得同月色一般的旧衣服也是再得体、再标致不过了,“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看到她不觉想笑,她的淑静能将我们的热闹消灭,就如同竹林对人的陶冶。最妙不可言的是她的一句“吃先生们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说完抓起一把掷在原先称就了的堆里。一个俏皮聪明活泼的小姑娘形象栩栩如生。人物的语言、行为和心灵一起化作诗的韵律。废名的小说往往把自然景色灵化,把世间人物稚化,化作余音绕梁的山村牧笛。废名用绿竹来写现实世界,文题是写竹,文眼则在“水”。废名的小说几乎每篇离不开水,这里也是。竹因水而翠,水因竹而清。假如竹林旁边没有水,则少了灵性。正是这水,使得三姑娘充满灵秀之气,性格也如水一般清爽,容不得一点杂质。“竹林”“水”“三姑娘”至此融为一体,难分你我,互相映衬,互相突现。
读《竹林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作者对春的爱怜,对绿的敏感。废名笔下的自然景观,再加上平实流畅的语言,无不散发着田园诗式的意蕴。正如废名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小说“分明地受到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那样”,追求小说的情趣、意境、诗情、画意。他的小说大都比较短小,人物也只有寥寥数个。而这些人物的存在并非为了介入首尾完整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为了倾诉一种情愫,表现一种人生滋味,或作为点缀,为幽美静谧的田园风光增添一种人世的意味,就像舟子、椎夫、渔翁作为宋元山水画中的点缀一样。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性格塑造,将小说散文化、诗化,不仅表现在废名的短篇小说中,也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虽形式上为长篇小说,但每个章节几乎都可以当作独立的散文读。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就将《桥》中的几节作为散文选入该集。废名的这种诗化追求,影响了几代作家,他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田园小说的开拓者。
【思考与练习】
1这篇小说具有散文化和诗化的倾向。作品不借重故事情节,对人物形象也不作精雕细刻,而是再现了一个意境,饱含着一种情韵,用简练的文笔传达了一种情绪,从而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试对其散文化和诗化的倾向做具体分析。
2这篇小说,字里行间浓情四溢,却不见作者“抒情”的痕迹,而是寓情于诗的意境和挥洒自如的描写之中。这种写作手法有何艺术效果?
心香
叶文玲
老岩不是要在南方过年么?为什么提前回来了?
一推门,我就看到了一个奇迹:一把赭色的样式古朴的陶土瓦壶,在蜂窝炉上咝咝地冒着水汽。
我惊奇地望着瓦壶,又看看老岩。呵,他刮了胡子理了发,中式罩衫干干净净,蟹青色的围巾和蚌壳棉鞋都是新的。嘿,这哪是平时的老岩!
“你看我有些反常,是不是?”老岩解嘲地摸着光溜溜的下巴颏。
我惊讶的不光是老岩的焕然一新,炉子上这把陶土瓦壶,更教我像发现一件出土文物那样稀奇。
可不是我夸大其词,在我和老岩合住的房间中,用壶烧水,简直像“赤日炎炎水成冰,冷饭抽芽两三寸”一样不可思议。
在没有分配到这个学校前,我就崇拜过老岩。这不仅因他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更主要是由于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因一幅油画名噪一时,而我,那时还是一个流鼻涕的小学生。当时,他那幅大出风头的画和老师们谈论这幅画时给我的印象,使我在看着画上的署名——岩岱时,就像仰望天上的星星一样,觉得高不可攀。
生活,也真像浩瀚的星空教人莫测。现在,我竟成了老岩的同事,并且同校同室。可是,早已改行教英语的老岩,平常连谈论美术和绘画的兴致都没有了。他英语功底很深,教三个班的课也不费劲,家又在南方,空闲时他什么也不做,只躺在床上看原版本的外文小说。
无论是怎样了不得的名人,如果你一旦接近他,你便觉得:失去的是罩在他头上的神秘的光圈,得到的是明晰而真实的面目和形象。而当你和他相交相知,发现他和常人一样有着这样那样的喜怒哀乐,你就倍觉亲切,甚至连他的缺点也感到可爱。
我对老岩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现在,连他平日不爱说笑,一没事就直挺挺地躺着看书,不爱收拾,连袜子也总是换到没有可换时才从床垫下抓起一大把去洗的习惯,我也无一例外地看成是有才气的人的那种可爱的懒散。不管怎么说,老岩是个好人,我一向敬重他。
老岩唯一教我大惑不解的怪癖就是:他很讨厌水壶,而且讨厌到了近乎憎恶的地步。
在我刚任教并兼任初一的图画课时,我教学生作静物写生,就从总务处拿来了一套实物:铝壶、茶盘和茶杯。
老岩一见,皱着眉头说:“什么不好画,要画这?”没等我说话他劈手夺走了我手中的壶,又马上在抽屉里找出几只红艳艳的苹果放在盘子里。“呶,画画这多好!……多好!”他那眯缝着的眼睛发亮了。
我没有细辨其中原委,只好照办。
不久,因屋里没烧水的壶,喝水不方便,我随口说了句:“要领把壶来就好了……”
老岩双眉一挑:“壶?哦,我去领。”
第二天,我们的炉子上出现了一只铝锅。
我奇怪了:“怎么领这个?”
“不是领的,我是买的。”老岩回答时,连看也不看我。
“买的?买锅干吗?又不做饭,烧水总是壶好……”
老岩一反往常地没了好声气:“锅不能烧?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