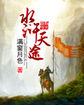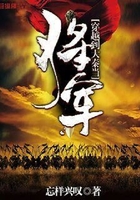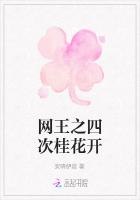汉朝分封诸王是前车之鉴,能看透儒家那一套的智者,都会明白,未来削藩是不可避免的。
人看到自己注定的前路,该怎么选择呢?
是俯首投降,还是奋起反抗?
前世历史说朱棣早就有了造反之心,并不是没道理,李清一番分析下来,李清都觉得朱棣应该是早有造反之意。
只是朱元璋控盘能力太强,再有心也是无力的。
也许没人想到,建文帝身边的猪队友们,会如此急不可耐及没用吧!
俯首投降不是朱棣的性格,既然注定要走这条路,那么就该想如何把路走通。
“墨家既然认定将来必定会削藩,又打算在此时入世,与儒家争锋,本王是墨家众多投注之一吗?”
朱棣的声音有点冷。
李清不慌不忙道:“王爷,家师在世时说过,六年前墨家上一届代表大会上表决过,若非异族再次戕害我华夏苗裔,墨家六十年内不会入世。”
“什么是代表大会?”朱棣倒是不耻下问。
李清忽悠道:“这是我墨家一千年前探索出的机构组织,一切权力归于代表大会。”
“每二十年,散布全世界的墨者都有权,在十个墨者的共同推荐下作为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所有重大事项,都需要在代表大会上表决决定,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所有墨者都必须遵守执行。”
“你作为钜子,也要遵守代表大会的决定?”朱棣惊讶道。
“钜子为作墨家领袖,每届钜子一生有三次一票否决权。钜子可由上代钜子指定承继,上代钜子无指定承继下,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先辈们意识到权力需要制衡,故进行了改革,也是这样的改革,让敝派传承延续至今。二千年前的百家争鸣,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除了借名方外的佛道,其他的学术门派几乎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
李清开始给朱棣灌输分权与权力制衡。
朱棣若有所思,想了一会,皱眉道:“敝派掌握如此多学问,为何这么长的时间不曾见传学?”
李清叹道:“王爷,一直以来,墨家不愿入世传学,不是墨家自私,敝帚自珍,而是二千年来,墨家以惨痛的教训明白,在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前,墨家传出的学问,只会沦为皇权及儒家的禁脔。”
“王爷,王莽就是敝派第二十三代钜子,是敝派的一次尝试。”
“什么?王莽竟然是你们墨家钜子?”
“资料记录是这样,当年之事,太过久远,很多资料已经遗失。小侄年幼时看到的,大多是后来先辈们总结论述,大概是当年支持王莽钜子时,很多学问不足,造成急功近利,最后不免失败,敝派也损失惨重。”
“也是那次之后,敝派也意识到儒家的强大及自己的不足,敝派决定退隐于世,或隐于各行,或远走海外,积累学问。”
朱棣叹息道:“难怪王莽篡汉时,很多施政措施都与历代格格不入。”
李清回忆了下知呼上调侃王莽为穿越者时,说的一些王莽的施政方案,沉声道:
“王爷,不是小侄为敝派先辈说好话,王莽钜子施行的一些政策,是比儒家那套要有效解决问题的,只是当时没把度掌握好。例如土地改革,历代朝政败坏的开始就是从土地兼并开始的。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和王爷慢慢探讨解决方案。”
明朝的藩王制度下,为供养宗室诸王,应该说是历代中,土地兼并最严重的王朝,最高峰时,有些州县的土地超过七成在宗室名下。
李清继续道:“王爷,儒家为何一千五百多年来能独尊朝纲?是因为儒家那一套天生就是为皇权服务的。儒家制定的伦理纲常,目的就是为了禁锢控制掠夺百姓,供养权力,他们儒家从中分一杯羹。”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何周朝以来,历代王朝国祚最长者不过三百余年,就是因为儒家那一套制造出的是绝对的权力,上层持权力权贵者,娇逸奢侈,日益腐化,视百姓如刍狗。”
“赵宋与士大夫共天下,短短不过几十年,即出现冗官、冗费、冗兵。”
“官员勋贵集团不事产生,五指不沾阳春水,一饭一食佳为民旨民膏,百姓再勤劳也不够越来越庞大的勋贵官员剥削掠夺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就是历朝百姓造反的根源。”
“有口饭吃的,谁愿意去冒险砍头造反?”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能供养权贵,即将饿死的百姓亦能造反覆灭权贵。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李清顿了顿,喝了口茶,继续道:“王爷,自敝派进行权力机构改革后,责任终身制,权力对敝派子弟来说,既是特权,也是责任,以至墨家子弟不爱权,如果有得选择,墨家子弟更愿意去探索天地至理。”
“先辈记录,极北之地有光为极光,美不胜收,仙景不过如是;南洋之滨,海面星罗棋布一个个如花环般的小岛,犹如天际抖落而下的一块块翠玉;非洲南之端有天涯海角,气象万变,景象奇妙……”
“这样的人间仙景,先辈们的记录传回,众子弟恨不得即时前往欣赏。”
“世界那么大,无主之地如此之多,为何我墨家子弟非要入世与儒家争锋来困守一隅?”
李清继续声色悲怆道:“小侄年少,身负钜子之职责,本应遵守代表大会之决定。”
“此次任性冲动违背大会决定,行一票否决之权,孑然一身入世,不是代表墨家入世,也不是墨家要入世与儒家争锋。”
“是因为此地为我华夏之根,桑梓之地,小侄同为华夏之苗裔,觉得自己力所能及之下,不忍百姓再受儒家禁锢,百年后再度陷入历朝之轮回,故表露身份是来与王爷做个约定。”
朱棣沉声问道:“什么约定?”
李清恳声道:“小侄以墨家所学全力助王爷戴上白帽子,登极之日,若王爷愿意用墨家之学,小侄愿助大明成为世界中心,成为中央之国,中国之旗,飘扬四方,照耀万世。”
“若王爷贪婪皇权,再起儒家,重回历朝那一套,只需王爷一声告之,小侄即时率领墨家子弟退出中国,界时王爷请赐小侄十万华夏子民,小侄率十万华夏子弟寻一无主之地,延续我华夏之威壮灿烂,约定永世与大明交好。”
朱棣皱眉道:“姑且不论本王能不能走到那步,你就这么肯定,我朝在儒家主政下也会如历朝那样最终社稷灭宗庙毁?”
李清郁闷道:“王爷,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您与陛下如此知兵,常不能解决北方之患,后世子孙从小在深宫儒家教育下长大,儒家早就把君子六艺的射、御、数丢了,教育出的皇帝及大臣怎么可能知兵及民间疾苦?”
真想告诉你,前世历史中,你才死几十年,你的子孙皇帝就创造了“土木之变”的惨败,连皇帝都被捉了。
“到时北患南下,如何抵御?溃败之局早就已注定,从此外有北方之敌,内有勋贵官员士大夫腐化,一旦有旱涝天灾,百娃揭竿而起是唯一选择。”
最悲催的是大明正处于小冰河上升期,旱涝之神交替出来施法折腾。
“儒家妄想靠着几本经书就治理天下,与何不食肉糜有何区别?汉晋唐宋,哪个跳得出此轮回,终社稷灭宗庙毁,王爷凭什么觉得大明可避免?”
作为历史学爱好者,他从前世五千年的历史里总结出一套规律,撇开藩王各自为政,蒙昧落后的周朝不提,没有一个朝代的国运,撑过三百年。
两宋两汉也是经过重组后的王朝。
恰恰历代王朝中,几乎都是儒家主政朝堂。
是巧合吗?不见得。
因素肯定很多,但李清个人认为儒家是要负一半以上的负责。
反正现在也没儒家之人来反驳,即使有儒家人反驳也不怕,就像前世网络段子。如来与玉皇争吵,如来只需来一句:你被猴子打了,你姐被凡人睡了,你女儿被凡人睡了,你孙女被凡人睡了。
朱棣不回答李清的反问,又沉默了一会,忽然道:“你之前说尊师隐居此地,是要找到克治北方的策略,是否有找到解决之法?”
李清微微一怔,不明白朱棣怎么就突然跳跃到这里,这就打算解决北方之患吗?
难道朱棣觉得解决北方了,朱家就可以万世无忧了?李清暗自吐槽。
问题还是要回答的,想了想,李清道:“小侄与家师多次推演,得到有一个策略,我们都认为可行性非常高。”
朱棣双眼一缩,真找到了解决之法?墨家这么厉害吗?
“能否说说?”朱棣试探道。
李清点头道:“让学问惠及华夏之民,这是敝派的宗旨。”
“此策略三个方面,三管齐下。首先是军事占领,这是必须的。”
朱棣幽怨般瞥了李清一眼。
李清也没在意,继续道:“军事占领后,一方面就是对牧区进行划片区而治,建立盟旗制度……第二方面,推行黄教……”
李清直接照搬了清时的盟旗制度及佛教策略后,继续道:
“第三方面,就是经济殖入。北方游牧南下侵我汉民族,除开少数是因权贵贪婪,说到底大多是部落出现灾害,牛羊死绝,无力生存,不得不冒险南下掠夺。”
“小侄已经研究出奶粉,一旦确定能长时间保存,可以从牧民手上收购羊牛奶,加工为奶粉,运回我中国内销售,对双方都大大有利。”
“牛羊奶是一个细水长流的收入,牧民有了钱,就能一定程度摆脱天灾的伤害,再加上前面的两方面压制,大部分年青人都念经去了,剩下一二个放羊能养活家庭,南下的心思就淡了。”
“墨家子弟,天纵之才也!”
朱棣深吸一口气,感叹道:“二千多年了,北方之患就如疥癣般,杀了一庄又一庄,代代南下叩关,祸害我华夏,无数人与财物被毁。此策略施行,北方再无祸患。”
李清不客气泼冷水道:“王爷,即使将大漠化为我华夏之地,蒙古族化为我华夏之民,瓦刺之西北,还有同样好扩张的俄罗斯呢!”
“王爷,世界如此之大,民族如此之多,都在求生存,中国一旦势弱,无数饿狼就会扑过来撕咬,听说现在连小小倭国都敢侵扰我中国沿海。”
朱棣也无语,好不容易看到解决北方祸患的机会,这小子立刻来一闷棍,但能感觉到,墨家似乎真的对这个世界有着更深的认知。
倭寇侵扰中国沿海,这事他也有所闻,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
只见李清指着地图大概秘鲁位置,说道:“王爷,据先辈记载,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可作主粮的农作物叫土豆,耐旱,至少亩产达十五石以上,全国可种,即使大漠里都能种活。”
李清决定再来一狠招,不信吸引不了朱棣当皇帝后,抢在葡萄牙西班牙人前让大明无敌船队插旗全球。
到时是要出海,要用我墨家所学呢,还是要用儒家的锦绣文章?
“什么?亩产十五石以上的主粮?”朱棣惊跳起来。
即使听到白帽子都没惊跳的他,听到这个消息竟然惊跳而起,足见土豆对他的吸引。
“那里还有一种农作物叫红薯,亦可勉强作主粮,同样能达十五石以上,不过耐旱性没土豆好。”李清再放一招
“主要找到了土豆和红薯,我中国不单不再受饥饿之威胁,善于耕种的汉民北上种土豆,到时整个北方都将成为我中国的粮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