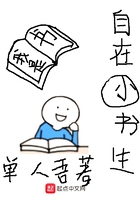用过晚饭后,香菱便引着公子进了内屋。她看得出,公子今晚心情不错,想必是跟那位甄公子喝酒尽了兴吧。不知怎的,香菱自己的心情也莫名好了起来,于是她决定要趁着好心情陪公子好好的聊一会天。
香菱小时候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好像小时候也是生在富贵人家?就像公子家里一般,似乎是不愁吃穿的。当时还有爹娘?面容已经完全记不得了。自己应该还有个名字?叫什么莲?不会是香莲吧,这名字还不如香菱好听呢。
之后,便是很长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香菱不愿去回忆那段日子,她恨不得把那段记忆埋藏在最深、最边缘的心底,永远不要想起。因此,那段记忆也慢慢变得模糊了。
直到十岁那年,被公子买回家。其实香菱并不知道她当时多少岁,只是公子说,她跟姑娘看起来差不多大。姑娘当时是十岁,于是她就说自己也是十岁。公子买她那天是九月初一,很好,她也有生日了,九月初一。
香菱的记忆,就从十岁生日那天开始清晰,到今天已经是三年零三个月了。公子打小就有四个小厮,琴童棋童书童画童,却一直没有一个丫环。据琴童说,公子不习惯被丫环服侍。直到那天,公子与几位朋友在街上游戏,不知怎的就看见了跪在街边的自己。公子盯着她,目光炯炯。随后公子叹了口气,就从人牙子手里将她买下。那天之后,公子有了一个丫环,但直到今天也只有这一个。
其实香菱知道的,公子那天盯着的不是她的眼睛,而是她眉心那颗米粒大小的胭脂痣。她想,公子一定是认出这颗痣来了。他也许是见过小时候的自己吧。更重要的是,公子可能会有她爹娘的消息。
可是,公子一直没有提,香菱也没有问。开始是不敢问,在敢问了之后,却又不想问了。爹娘将她丢进了最黑暗的深渊里,而公子却把她从深渊里捞了出来。如果公子想说,她当然愿意听。如果公子不想说,她也不会去问,就做一辈子公子的香菱。
香菱心里想着,动作上却丝毫不慢。她快步走进屋里,熟练地服侍公子换上便装,倒了两杯茶,陪公子在桌前坐下。
香菱有一样得意的本事,就是可以一眼看出公子的心情好坏。刚才她就发现,公子今天的心情是这一个月里最好的。难道那甄公子就如此得公子喜欢?香菱心里不禁有些泛酸。
她今年十三岁,在别人家里已经是可以试云雨情的年纪了。平日里,她也极注意梳妆打扮。与琴童几个闲聊时,他们都说自己的容貌比姑娘房里的莺儿、太太房里的玉箫小玉几人加起来还要俊得多。她也看得出,公子心里十分欢喜自己。但为何,公子还迟迟不肯给她一个名分呢?
有一次她装着什么都不懂,钻在公子的被窝里对着公子傻笑。公子却客气地把她请了出来,嘴里还念叨着什么“炼铜”这些难懂的话。估计是嫌我年纪小、没长开吧,香菱这样想。
公子喝了一口茶,舒服地出了一口气,嘴角带笑。香菱也低头笑了起来,正琢磨主动找点话头,却忽然发现公子看向了自己,欲言又止。
发生什么了?公子的心情怎么突然变坏了?为什么看我?我今天又没做什么,莫非外面有什么麻烦事?
“香菱啊,你到我们家有几年了?”公子开口问道。
“已是三年零三个月了。”香菱对这个一直记得很清楚。
公子似乎在组织语言:“是啊,这么久了……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
“公子请说。”果然是关于自己的事,香菱想道。
“是这样,我前些日子打听到了你的身世,你想听吗?”
前些日子打听到,这话香菱是不信的。当年那一眼,分明是认出了自己。但香菱还是呆呆地看着公子:“公子既然愿说,香菱自然是愿听的。”
“你本姓甄,名叫英莲。”
果然没记错,名字里有个莲字。
“是甄公子那个甄家吗?”香菱问道。
“不是,同姓各宗。”公子答道:“你父名为甄士隐,与你母封氏都是本府人。昨日管家来保找到了封家,那封氏说起她当年有一女,唤作甄英莲,三岁时走失。不久甄家又失了火,家财散尽,封氏回了娘家庄上,而那甄士隐,早就出家做道士,不知所踪了。那封氏说起英莲眉心有颗胭脂痣,你年岁又对得上,大约就是你了。”
还真是昨天才知道我的身世啊,香菱想道。不知为何,十年来第一次听到爹娘的消息,她居然没什么感觉,关注的重点却在公子何时知道这件事上。
“来保问我要不要告诉封氏你的消息,我觉得这事应该由你拿主意。”公子道。
香菱皱起眉头想了一想,问道:“公子是开春才上京吗?”
“是的。”
“那香菱希望公子赏个假,明日派人送我去见我娘亲。过完年后,开春我便回来,随公子上京,如何?”知道了本名是英莲后,香菱还是自称香菱。
“我自是没问题。只是你爹出家后,你娘多年无人相伴,虽然家境也算殷实,终不免有些寂寞。她怕是希望你能多陪陪她。”
香菱正色道:“香菱是公子花钱买到薛家的,自是薛家的人。公子愿意助我找回身世,又送我回去全几日母女之情,香菱已是感激不尽。只愿公子能容我,这辈子就在薛家服侍公子,以报公子之恩。”
公子愣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接。半晌,他打个哈哈,笑道:“只求你别怪我这么晚才帮你找回身世就好。那明天就让来保送你去吧,我出发前再派他接你。你快去收拾行李吧,我这里不用你服侍了。”
香菱却道:“我没有什么行李要收拾的,衣物什么的想必娘那里也不缺。这几年我攒了些银子,一发带回去罢了。香菱只想今晚再陪公子说会话,下次见面就是开春了。”
于是公子便说起了今日狮子楼里与甄宝玉他们的趣事。说到作咏雪诗时,香菱察觉到公子有些得意,便插话道:“公子,香菱也想学作诗。”
果然,公子一听就来了兴致:“听妹妹说起过你也是个爱诗之人,无事时寻过她写的诗看。依你说,我今天作的这两首咏雪诗,比我妹妹如何?”
差得远了,香菱想道。但她嘴上却说:“姑娘的诗总是看得我半懂不懂的,不如公子的诗清晰明了。”
公子哈哈大笑:“我是喜欢在外面吹牛,其实也知道妹妹的诗才强我百倍。不说别的,你这名字就是她取的呢。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唐朝李商隐的诗,她可是信手拈来。”
香菱一字一字地将这两句诗重复了一遍,又点头道:“虽然不甚明白,但我觉得这两句确是好诗。”
公子又笑道:“这两句里‘菱’与‘桂’对应,哪天我再去买个丫环,取名就叫金桂,与你做伴如何?”
香菱也开起了玩笑:“那诗里‘弱’与‘香’对应,公子若是再买个丫环,应当叫弱桂才是。”
“那多难听啊。”公子又笑了,“刚才是跟你开玩笑。我拿你的生辰八字去算过命,你命中什么都好,就单犯一个‘桂’字。今后若遇到名字里有‘桂’的人,可要躲远点,记住了吗?”
香菱含笑应是,心里却想公子又来唬我,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公子如何能知道呢?
静了片刻,她又开口道:“姑娘的诗虽好,但我是真心更爱公子的诗,求公子教我。”
公子似乎认真思考了一番,但说出的话却让香菱有些失望:“你明日就走了,我现在教你也来不及。你若真心要学诗,走之前就去找我妹妹要几本诗书回家研习。进了京城以后,咱们一起在我姨妈家住,那边有几个与你一般大的姑娘,你自可同她们交流诗词之道。”
香菱见公子执意不教,也没办法,又道:“我平日听琴童说,公子号称‘诗剑双绝’,一手薛家剑法打遍武林。既然公子不愿教我作诗,能否教我薛家剑法呢?琴童说薛家剑法就在这‘接化发’三字下,我听得颇觉有理,却又不能完全通晓其意。公子能否仔细与我讲讲这接化发之道呢?”
公子的表情一时非常精彩,香菱竟然少有的看不透他的心思。半晌,公子才开口:“这接化发确是薛家剑法的精要。但琴童有没有跟你说过,薛家剑法没有招数,只有内功?要是没有内功,就无法发挥薛家剑法真正的威力。”
香菱不依不饶:“我也听说过,公子曾花重金从武当山购来习练内功的方法。能否让香菱见识见识呢?”
公子笑道:“武当那帮道士敝帚自珍,本来简单的内功给他们写得那叫一个云山雾罩。还是我和妹妹一字一字地读那上万字的内功心法,剔除了九成九的神怪玄学之论,才得了现在简单明了的薛家内功。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就是这般了。”
香菱抓住了重点:“姑娘也会内功?”
“她不会。”公子答道,“练内功需要资质,百中得一,我妹妹就是那百中之九十九了。蝌兄弟也不成,倒是琴妹妹是有资质的,好久不见她,不知练得如何了。”
公子又道:“这薛家内功是我和妹妹总结归纳而来,已不是武当的练法,我也不需替他们守密。我现在教给你,你回家习练,若是三天之后还没有感觉,就是你没有这份资质,不用再练了。”
香菱这才露出了笑容,点头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