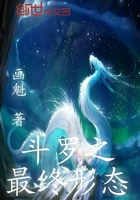孙枝梅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拉着我,用低的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说:
“义平,走,我们回去。”孙枝梅光着的小脚扛着孙枝梅虚弱的身子,拖家带口走着走着,似乎听到有人在喊:
“小梅,小梅!”
我们停下脚步,回过头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老叫花子似的的人站在了我们身后。孙枝梅稍微迟疑了一下,用力咳了两下,清了清嗓子,尽量使声音最大,紧张地问道:
“你是谁?想干什么?”
“小梅,是我,东文的父亲,罗世昌啊!”老人显得很兴奋的样子,说。
罗世昌,我的爷爷,我们家遭遇轰炸时,他带着姑姑到外面乞讨去了。
孙枝梅放大胆子走近几步,仔细一看,真的是罗世昌!孙枝梅确实吃惊不小,说:
“姑父,真的是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孙枝梅的眼泪情不自禁已经哗哗的在流。
她用手捋了捋罗世昌额前的乱发,露出一张布瞒皱纹的脸,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一张不知疲惫的脸,不知是被无情的岁月还是残酷的世道,刻蚀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孙枝梅有点站不稳了,动荡的乱世之中,远在异乡,还能见到亲人。满脸倦容的孙枝梅露出了微微的笑意,联想到自己刚刚被日本人的折磨和侮辱,孙枝梅豁然开朗,挺直胸膛叫着我,说:
“义平,扶爷爷回家!我们回家!”
罗世昌想起还有傻姑娘罗东瑶,忙说:
“等一下,还有一个人,你表妹瑶瑶也来了。”
我们一行来到罗东瑶藏身之处,一个废弃的瓦窑。罗世昌大声喊道:
“东瑶,东瑶!出来呀!我是父亲。”
从瓦窑里面出来一个蓬头垢面小男孩模样的人,孙枝梅也认为是个男孩子。是罗世昌有意把罗东瑶打扮成男孩,把头发剪的乱七八糟,像狗咬的一样。不知罗世昌从哪找来一件特大号的成年男子的大褂子,穿在罗东瑶身上,把整个人罩的除了褂子就只有头和脚了,脚上好赖还穿有露出脚指头的布鞋。估计布鞋上面的小洞,都是用脚踢狗时反被狗咬破的。
别看一件大褂子就把罗东瑶整个人都罩住了,其实我姑姑罗东瑶,已经二十几岁了,是个成年女子。只是不怎么会说话,行动也慢慢悠悠,不急不忙的,原先在老家时经常跟我一起玩,我经常把她当马骑,她也乐意让我骑在背上,她就在地上拼命的往前爬。
我们回到家里,孙枝梅累得实在是不行了,小脚应该血肉模糊了,就直接去房间睡觉了。爷爷罗世昌问我有没有什么吃的,我老实告诉他:
“什么吃的也没有,钱也被人抢走了。”
罗世昌在厨房里找了半天,把那胎盘拿了出来,问我:
“义平,这是什么?”我告诉他,这是跟妹妹一同从孙枝梅肚子里拉出来的,可以吃的。
罗世昌当然知道这是胎盘,而且目前来说孙枝梅是最需要营养的。罗世昌切了几片胎盘,洗了一把米,放在锅里煮上了粥。粥煮好了,罗世昌把那几片胎盘掂出来,叫我端给孙枝梅吃。然后又在锅了添了些水,继续煮,等水煮开了,我们也开始喝粥,我们都喝的很饱。
经过近两年的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磨难,罗世昌也醒悟了,为了儿媳和孙子、孙女,罗世昌决定该做点事了。于是,罗世昌每天早早的就出去,很晚才回来,回来时总是能给我们带回一点吃的。
同往常一样,罗世昌早早地出了们,来到一个离家较远的饭馆前。这么久的要饭经验,罗世昌知道什么地方能得到丰盛的残羹剩饭。他会在饭馆对面蹲守,注视着饭馆里面的动静,一旦看到二楼有人下楼,他就快速地冲进饭馆,上到二楼的雅间,把残羹剩饭全数倒入自己的衣服包着就跑。
当他跑出饭馆大门时,被从门前飞驰而过的小车撞个正着,飞出能有十几米远,当时就晕了过去。开车的人下车看了看,没有理睬,开着车一溜烟跑了。
等罗世昌自然醒来时,天正下着滂沱大雨,罗世昌坐起来想了想,我的丰盛晚餐呢?罗世昌快速的爬起来,满大街去找,一路找到刚刚的饭馆旁边,只看到自己那件破烂不堪的衣服。罗世昌没有放弃心里的念想,在老天的帮助下,罗世昌找回了三块骨头。他兴奋的揣起这三块骨头,把衣服往肩上一搭,哼着小曲踏上回家的路途。
尽管天上的雨越下越大,对罗世昌来说,早已习惯了这种冲涮,就当做接受这无根之水的洗礼。
罗世昌回到家时,我们都已经睡了。罗世昌把裤子脱下来,和衣服一起拧干了水放在炉子上烤,烤干了又穿上。然后切了几片胎盘,与刚才捡回来的三块骨头放在一起,装在碗里添些水盖好后,放在炉子上煲汤。
当罗世昌端着骨头汤来到房间时,孙枝梅已经醒来坐在床上。孙枝梅看了看罗世昌,接过汤碗,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是把不住眼睛里面的眼泪,唰唰的往下流,流落到汤碗里,没有发出一丝水滴的声音。孙枝梅把汤一饮而尽,又酸又咸的汤在孙枝梅的嘴里是那么的沁人心脾!
罗世昌看着孙枝梅把汤喝完,一种由内而发的高兴和满足添加在罗世昌不知疲倦的脸上的皱纹里。罗世昌接过孙枝梅递过来的碗,说:
“小梅,孩子啊,你接着睡吧。”
话还没说完,罗世昌突感体力不支,整个身子就往下坠,倒在了地上,昏了过去。
孙枝梅赶紧起身下床,坐在罗世昌身边,大声的喊着:
“姑父,姑父。。。”
嗓子喊哑了,罗世昌依然没有反应,泪流干了,罗世昌还是没有醒来。孙枝梅用手指试了试罗世昌的鼻子,感觉呼吸还是有,就找来一张竹席,摊平在罗世昌身边。自己在对面双手使劲推罗世昌,想把罗世昌推到竹席上去,就是不能够做到!
罗世昌再次醒来时,感觉身体有点不对劲。左手使不上劲,胳膊肘弯曲不能动,只能单靠右手的支撑身体坐了起来。左脚也不能使力,头部歪向右侧,口水直流不受控制。
孙枝梅心想,这下完了,罗世昌瘫痪了!这可怎么办哪?老天哪!
孙枝梅慢慢搀扶着罗世昌坐在椅子上,现在的罗世昌连说话都很费劲,吐字不清,还要不停的擦口水。
罗世昌的这种病,以前在娘家时,孙枝梅听父亲说过,但当时她没有用心去记。孙枝梅真是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跟父亲好好学呢?孙枝梅的父亲,不但爱好习武,还精通中医针灸,尤其擅长颈椎和妇科类疾病的针灸治疗。
孙枝梅一筹莫展,真是应了古语: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首先钱财被抢;接着自己刚刚生完小孩就被抓去严刑拷打,还被狗日本军官玷污了身子;得之不易的亲人相投,却惨得如此之重病!孙枝梅想着想着,万念俱灰!
“我饿了。”我使劲拽着摇着孙枝梅的手臂,说。
孙枝梅恍恍惚惚,霎时想起罗东文的交代:“小梅,一定要把义平抚养成人。”孙枝梅想起了罗东文,想起了她的天,心里有了力量的支撑!她坚信罗东文总是会回来的。
农历八月初一,孙枝梅怀抱妹妹,一手拉着我,说是要去庙里烧香。我拽着孙枝梅旗袍的下摆,跟在后面,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座寺庙。这座寺庙不大,屋顶上铺满了金碧辉煌的琉璃,屋脊上雕刻了许多人物,栩栩如生。这里,环境清幽,远远望去,寺庙就像天宫一样。
孙枝梅真是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么一块地方。孙枝梅走进寺庙,跨过门槛,在前面树立着一尊高大塑像。塑像傍边有几个和尚单手竖在胸前,嘴里叽里呱啦念着经。孙枝梅拉着我同她一起跪在塑像面前,叮嘱我不要吱声。
孙枝梅心想,世人痴心向佛,只因悟不透纷扰的世俗。我一心只祈求神灵保佑太平无事,祈求世间给我孙枝梅一条活路!
我们向塑像磕头完毕,从寺庙里出来,走在下去的台阶上,迎面看到那个日本女人正往上来。孙枝梅像见到救星一般,激动的急急忙忙就上前去打招呼,说:
“夫人,您好!”
还没等那个日本女人开口,两个军人随从已经上前挡在孙枝梅与日本女人之间,逼着孙枝梅离远一点。眼看着日本女人远去,孙枝梅岂能放过这个机会,于是加急两步追了上去,大声说:
“夫人,将军夫人,我去过贵府的。还是您搭救我的。”
日本女人依旧没有搭理孙枝梅,进去寺庙里面了。两个军人随从站立在门口,一边一个。孙枝梅坚信这次就是她改变人生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所以孙枝梅就同那两个军人随从一再解释,可这两个日本人根本听不懂中国话。孙枝梅只好拉着我到傍边等候日本女人出来。
日本女人出来了,孙枝梅急忙又迎了上去,说:
“夫人,您的丈夫,他的脖子我能医好。”这句话果然管用,引起了日本女人的注意。日本女人推开随从来到孙枝梅面前,仔细看了看孙枝梅,说:
“原来你是如此的美丽。你的小孩还好吗?”
日本女人终于搭理孙枝梅了,孙枝梅激动的有些结巴,说:
“谢,谢,谢谢夫人!”与其说孙枝梅是客气,倒不如说是低下卑微。
日本女人说:“你刚才说什么,我丈夫的脖子的事,你真的可以医治?”
孙枝梅说:“是的,夫人。我叫孙枝梅,是原先孔府的媳妇。上次我看见您丈夫脖子上的颈托,就估摸着您丈夫的脖子是不是有点问题。”
日本女人说:“是的。你有办法?”
“我从小跟随家父学习中医针灸之学,尤其擅长颈椎和妇科。”孙枝梅说。
日本女人说:“那感情好,改天我派人请你去一下我家。”
“夫人,不用您请,我自己去就行。只是现在我因多次搬迁碾转,针灸工具尽数失落。重新置办需要时日。”
“我明白,理解。”日本女人说完,跟身边的丫环嘀咕了几句。丫环过来给了孙枝梅一些钱,孙枝梅接过钞票,低头说:
“真是不好意思。一周之内,我一定去拜访,以表感谢!”这一次,我没有抢孙枝梅手里的钱。
我们回到家里,罗世昌已经拉得到处都是,满屋子臭气熏天。姑姑坐在门槛上只顾自己玩。孙枝梅今天虽然走的有点累,但心情特好,屋里再怎么臭也无所谓,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再说。
孙枝梅叫我帮手把罗世昌扶到凳子上坐稳,罗世昌腿上、屁股周边到处粘满了压得扁扁的屎块。孙枝梅要用手一块块地把屎块剥下来,然后再用湿毛巾擦洗,洗完了人身上,还要洗睡觉的床铺。洗床铺比较难一点,因为压干了的屎块粘在木板上劳劳的,很难剥掉,需要一边滴水一边擦洗,方能清洗干净。
这样的清洗工作,孙枝梅天天要做的,有时一天要洗几次。罗世昌不但屎尿不禁,而且说话也说不清楚,所以孙枝梅也就没敢给罗世昌穿衣服,只是在他身上盖了条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