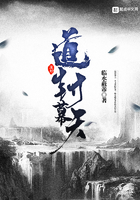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⑨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颇曰:‘恶用是轻轻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轻轻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注释】
①匡章:齐国名将,其言行见于《战国策·齐策、燕策》和《吕氏春秋·不屈、爱类》。
②陈仲子:齐国人,又称田仲、陈仲、於(yú)陵仲子等。
③放陵:地名,在今山东长山县南,距临淄约二百里。
④螬(cáo):即蛴螬,俗称“地蚕”、“大蚕”,是金龟子的幼虫。
⑤将:拿,取。
⑥巨擘(bò):大拇指,引申为在某一方面杰出的人或事物。
⑦盗跖:据说是春秋时有名的大盗,柳下惠的兄弟。
⑧辟垆(lú):绩麻练麻。绩麻为辟,练麻为垆。
⑨盖(gě):地名,是陈戴的封邑。
⑩频颇(pō):即颦蹙,不愉快的样子。
轻轻:鹅叫声。
哇:吐。
【评析】
以上这章可以当作讽刺文学来读。
陈仲子是齐国著名的“廉士”,可孟子认为他的作为并不能算是廉洁,尤其是不能提倡和推广他的这种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做得太过分了,是一种走极端的行为。孟子尖刻地讽刺说,要做到他那样,除非把人先变成蚯蚓,只吃泥土,喝地下水,这才能够做到彻底“廉洁”。而真正要用这种“廉”的标准来衡量,就是陈仲子本人也没能够做到。比如说,他住的房屋,还不知道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甚至强盗一样的人建筑起来的哩;他所吃的粮食,还不知道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甚至强盗一样的人种植出来的哩。何况,他离开母亲,不吃母亲的食物,但却还是要吃妻子的食物;他避开哥哥,不住哥哥的房屋,但却还是要在於陵这个地方来住房屋。这些行为,难道能够说是彻底“廉洁”吗?不是!说到头,只能算是一种沽名钓誉,一种酸腐,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假”,一种虚伪。但是,用朱熹引范氏的话来看,就更加严重:“仲子避兄离母,无亲戚、君臣、上下,是无人伦也,岂有无人伦而可以为廉哉?”(《孟子集注》)在“反腐倡廉”的今天,的确是有一个对廉洁的界定问题。廉洁并不是谈钱色变,拿得越少越好,也并不是生活越俭朴越好,人越清贫穷酸越好。其实,按照孔子、孟子的看法,廉洁就是“见得思义”(孔子),就是“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基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所谓“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廉洁做过了头,“当受不受”,比如说你的工资不要,该拿的奖金不拿,那就不是廉洁,而是酸腐,是“虚伪”,是沽名钓誉了。
因此,廉洁与酸腐的界限还是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经济问题时常引起人们困惑的时代。
最后回到讽刺的问题上来谈几句。除了以蚯蚓比喻辛辣讽刺外,孟子说:“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这里的讽刺更是不露声色,一箭双雕。一方面以“巨擘”讽刺陈仲子,另一方面却由于陈仲子之所以可以称为“巨擘”,是因为“于齐国之士”。也就是说,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已经算是齐国人中最好的了,那其他的齐国人真不知有多酸腐、多糟糕呢!另外,就是开始一段匡章之口对陈仲子的叙述,也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而关于陈仲子吃“轻轻之肉”一事的整个描写,就可以直接放进《儒林外史》的篇章里面去。
【原文】
彭更①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②于诸侯,不以泰③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④,以羡⑤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⑥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⑦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⑧,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注释】
①彭更:人名,孟子的学生。
②传食:指住在诸侯的驿舍(宾馆)里接受饮食。传:驿舍,相当于今天的③泰:同“太”,过分。
④通功易事:交流成果,交换物资。
⑤羡:余,多余。
⑥梓匠轮舆:梓人、匠人指木工;轮人、舆人指制造车轮和车厢的工人。
⑦待:同“持”,扶持。
⑧墁(màn):本义为粉刷墙壁的工具,这里指新粉刷过的墙壁。
【评析】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还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是正当的,再多也可以接受;如果不正当,再少也不应该接受。这就涉及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比如说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入问题,新闻媒介时有披露,其症结点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如果是“如其道”,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当然要按有关规定上税等等),如果是“非其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的界定是很清楚的。
问题在于,谁来界定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呢?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回到孟子的说法,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如利思义”(《论语·宪问》)或“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观点以及他自己“当辞则辞,当受则受”的实际做法(见《公孙丑下》4.3)都是一致的。说到底,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道”正是“如其道”,“无道”正是“非其道”。
本章牵涉的另一个方面是动与效果的关系问题。
在这观点上,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把论辩对手放到荒唐的处境,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在今天我们看来,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这个问一点也不复杂。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解决问题。孟子则是从实成绩,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解决问题。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不听大话、空话,只看工作业绩。
当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我们的观点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无论你是谁,做了错事,还是做好事的“动机不纯”,都是反对的。
只是,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二者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成绩,也就是“食功”而“非食志”了吧。
【原文】
孟子谓戴不胜①曰:“子欲子之王之②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齐人傅之,众楚人咻③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一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④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注释】
①戴不胜:人名,宋国大臣。
②之:动词,向,往,到。
③咻(xiū):喧哗干扰。
④庄岳:齐国的街里名。庄:街名;岳:里名。
【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