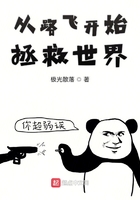玫瑰虽然有刺,但是仍旧美丽。
有人说,玫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渴望向世界展示它的艳丽。可碍于身上的尖刺,使得某一些人望而却步,只敢驻足于远处观赏,生怕戳伤自己的双手。
倘若玫瑰生长在牧野,同周遭的杂草作伴,那一定需要努力展示自身的颜色,要么长出更为坚硬的尖刺,以免去被牛羊当作口料,连根咬去的下场。即使开了花,吐了蕊,如果没人来采摘,最终只能与野花作伴,一起烂在泥土里。在茫茫牧野上,玫瑰要是能为识花者所发现,便是无比的幸事。往日拍打在花瓣上的风雨,都会成为真正绽放那一天的磨砺。
“接叶连枝千万绿,一花两色浅深红。”
夜钧寰躺在沙发上,随意翻看着手里的书,时不时会念出其中的句子。家里还能听见一把成年女性的说话声,不多时又增添了一把成年男性的说话声。两把声音,夜钧寰都再熟悉不过,他们是电视每天播送新闻节目里的两位主持人。
夜钧寰小心抚平书的页脚,随后“啪”地一下合上书,径直走向厨房,从米缸里舀起一杯半的米——这是他日常的饭量。淘洗两次过后,米连带一盆新接的水,被一股脑地倒入电饭煲。夜钧寰多次测量,直到水面离米恰好一个小指关节深浅,才满意地盖上盖子,让电饭煲进入工作状态。
客厅里突然响起“铃铃”的电话声,夜钧寰不得已甩干沾满洗米水的手。由于从小被教导“不能用湿手触摸电器”,夜钧寰将双手在裤腿上来回擦了三次,才急匆匆地拿起话筒。
“喂?”
“……”
电话里也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另一头是夜钧寰的母亲在说话。
“喂?你哑巴啊,接了不说话的?”
“干什么?”
“吃饭没有?”
“刚煮。”
“你爸爸呢?”
“我怎么知道。”
“嘟,嘟,嘟”,夜母那头挂断了电话。
夜父夜母在广州做了将近二十年的服装生意,站在广州本地人视角来看,夜钧寰属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一年前,夜家搬到现在所住的小区,房子据说是买的,而不是租的。夜钧寰还不太懂买房和租房的区别,只知道家里的墙要么贴了光滑的瓷砖,要么贴了好看的墙纸,哪样都比原来粗糙而单调的白粉墙好。
小学升初中时,夜钧寰填写了两所学校的报名表。一所是梅花学院,最好的区属中学;另一所是集才中学,比前者稍差一些。梅花学院从前是女子学校,近年面对社会上越来越大的生源压力,不得已而放开招生限制,吸纳男学生入学。但总的来说,梅花学院还是一所以女学生为主的中学。考虑到这点,再加上集才中学离家更近,夜母便替夜钧寰选择了集才中学。
明天是九月一日,众所周知的开学日,今天则是初中开学的前一晚。阳台上的新校服与新校裤,因为晚间的微风左右摆动,似乎在用它们独有的形式进行庆祝。电饭煲里的饭已经熟了,夜钧寰起锅烧油,快速完成一道西红柿鸡蛋,作为晚饭的配菜。陪同夜钧寰吃饭的,是电视里的两位主持人,每晚如此,很少有缺席的时候。
从明天起,夜钧寰便是一名初中生了。
————————
朋友。
朋友有什么用?
提起青春,常有人说,青春即是青涩。尚未成熟的水果是青涩的,硬而不甜。假使将一批青涩的水果摆放在一起,它们便会产生乙烯等物质,相互催熟,最终各个脱离青涩,进入成熟的状态。青春期的学生为何需要朋友,原因正是如此。
从还不会走路的岁数开始,夜钧寰就对文字特别着迷,文字在这里仅限于中国的汉字。对文字着迷,自然而然会喜欢看书,如果现代社会还流行抓周的传统,夜钧寰想必会在那时抓取一本书。
夜钧寰牙还没换完,读过的书肯定不算多,却自认为读过许多书,再后来发展成自认为很有才华。可惜这时节连笔尚且不能握得稳妥,更别说要他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夜钧寰只好委屈自己文曲星下凡的能力,暂时用于背诵古诗文上,间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
小学语文课的许多时候,语文老师刚讲完上句,夜钧寰也不举手,马上在座位上接出下句。那几个字像是从老师嘴里借来一般,着急还回去,这也被某些同学嫌弃为“不遵守课堂纪律”。事实上夜钧寰学艺不精,常有说错的时候,这又被某些同学评价为“未免装得太过”。
有才华的人早期多数不受人待见,夜钧寰对此观点深信不疑,对身边人的各式话语不上心。最后干脆减少与别人的交流,当然也不存在交友,往好听的说是为人内向,往难听的说是不屑于同人交流。人们的刻板印象里,安静的男生是奇怪的,安静的夜钧寰更是双奇临门,奇上加奇。
在家里没人说话,在外面无话可说,夜钧寰大脑里的语言功能分区,似乎真的就这么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