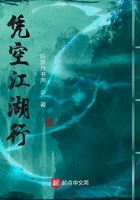(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三月底的天气,往年已是春意融融,早樱露了头,其余的差不多也有个小骨朵。今年特别冷,总是灰蒙蒙的天幕,衬着岚山上光秃秃的枫树枝,有鸟落下的时候,树下的人抬头就能看到考究的山水画。
天龙寺的住持就在树下看画。
住持叫元真,五十多岁,是个和尚。这天龙寺是他家祖传的产业,寺里面除了他还有负责收田租的管账,做饭的厨子,以及剩下的十几个普通的和尚。
元真看了半天树。他每天都要在树下看树,也不知道是真看树还是假借参禅之名躲着不去念经。反正这寺里他是老大。有一次,负责监督弟子念经拜佛的监堂估计也是看住持天天看花看鸟逍遥到让人一肚皮火,大着胆子请教了一波住持再干啥。
元真说,虽然佛曰不可说,不过我说了你也不懂。不过看你身为监堂,尚有闲心在背经书的时候看别人如何,想来道行也是很浅,明日就下山去吧。
然后来了个专心监督和尚们背经书的新监堂。从此和尚们再没有一句嘟囔。
和尚们早上有早经,早经完了吃早饭,早饭完了做法事,法事完了吃午饭,午饭完了到将军足利家轮值守卫。不轮值的可以选择打杂或者打坐。每个月有一天时间拿着领到的饷银回家买米。现在是乱世,对于天龙寺这一口好干简单收益高还没生命危险的事情乡民们自然是趋之若鹜。更何况如果到足利将军家,说不准干点闲差打打下手还能捞着点儿赏赐。好好挣钱不好么,为什么要挑住持的茬儿?更何况住持平时就是个闷葫芦,干活儿拿钱不加班没批评,多好。
所以元真在干啥呢?
他真的是在看树。
作为方圆百里内最出色的武士,元真从小跟着上一任住持修习拔刀术。天龙寺历来和足利将军府交好,每代住持都是足利将军手下第一武将,随将军征战四方。虽然征战规模不大,但是是实打实的血腥搏杀。元真少年时刀法已有小成,三十余年过去了大大小小战斗无数,如今周边暂且太平无事,所以才安心回天龙寺诵经念佛。
元真只是觉得无聊。佛经他早看过许多,动不动就“照见五蕴皆空”,只是足利大人们来的时候捐钱尚且钱包不空,出门抢劫粮钱女人那岂止是不空,晚上享乐的时候五蕴溢出还差不多。佛经从来只是马后炮,人没了,或者杀人的人事后来忏悔。武术又是很无趣,寺里有百亩佃田钱粮不缺。游山逛水又很懒,索性在树下看看树,内心很平静。不然记忆力不是练功就是杀人,真的是非常不美好。
偷懒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正常人应该干的事,不过元真那次酒后说了,我有钱有地位有本事,我不是正常人。
元真一眼就看出来八角是个杀手。
俩人在半夜在佛堂对了一手。空气里绵密的刀径把天窗里照进来的月光铺满了佛堂,最后两把长刀的刀尖相互抵着眉心方才罢手。
“你是中土人?”元真问道。
八角不说话。
“不用藏身份,你那两把刀我见过,那是我祖上托人打的,一共两对四把。”元真翻出了他手中的刀铭,“秋霜”“冬霖”。
八角还是不说话。
“放心,我不是问你讨刀,我只是好奇,这两把刀早就随遣使远赴中土做贡品,怎么会到你手上。我们是刀客,可以说一说刀的事。”元真指着八角的刀,那原本是陈皮的。
八角似乎终于被说动了,他张了张嘴——
“大爷,我听不懂啊。”
忘了他是中土人,不会本地语,元真扶额。
八角是要饭的时候被庙里的和尚带回来的。他做的大船遇了台风,船老大被浪卷走祭了海,一干人等七零八落,八角醒来的时候人在岸上,身上除了衣服和怀里抱着的陈皮的刀啥也没剩下。本打算凭借一身厨艺混口饭吃,结果抬抬眼发现这地方山峰延绵,根本看不到城在哪里,更别提啥有招聘需求的馆子。沙滩上画图连比划带猜大概知道了城的方向,一路上要饭抓鱼打野味吃野菜混到了城里。结果瞅一眼发现人家吃的还是生食。得,接着要饭吧。
去哪儿要饭呢?当然本地最大的寺庙天龙寺。
和尚们平时天天打杂也是无趣,看到一个不会说话的要饭的当然是戏弄一番。戏弄过头了,八角觉得本地的帮会道貌岸然却不讲礼数,于是出手打了一架。无奈腹中饥饿拳头绵软无力,被众人拿下,正准备丢河里恰巧被看树看的眼酸的元真看到。元真瞥了一眼虎口硬茧,“留下!”
八角就这么留下来,还被剃了光头,每日跟着和尚们念经打坐学土著语,时不时被元真拉过去切磋刀法。几个月下来土著语学的差不多,佛经因为天天坐最后排打盹一句不会。不过也有个好处,老香油教给他的内功心法,其实也就是呼吸吐纳,倒是精进不少。监堂大和尚要训斥时,呜呜呜呜假装听不懂。几次三番,又见他与住持交往甚密,大和尚也就不再多管。
八角还把拔刀术学会了,跟老香油教给他的切树刀法差不多,只不过拔刀术有刀鞘加速,有一个小小的蓄力过程,会更快一些。
于是八角被天龙寺推举为代表,参加足利将军府下个月十五举办的刀术赛。
(么的办法,总得有个过程,ghs等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