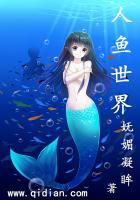亲爱的,你说你想来上海。想来上海看看从前的弄堂。你来吧,你来吧!不过从前弄堂里那些老人、女人还有快乐的孩子都已各奔东西。你还记得我那缺心少肺的表姐姗姗吧?今天我就要与她重逢了。此刻,我正一步一步走向上海的深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长长地吸一口气,吐出,再吸,再吐。胸膛里有两只手穿破我的头颅举向天空高喊:“你好,上海。”
我曾经住在上海弄堂里。我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个小女孩。弄堂里女孩子们的故事,我一直记着。如果没有她们,没有她们演绎的故事,那么上海的弄堂就没有那么灿烂夺目了。弄堂也许不叫弄堂,叫小巷或者别的什么。我这样说,你也许不高兴。你会质疑,难道弄堂里的男孩子,构不成风景?是啊,你也有道理。只是女孩如花,花朵总是比绿叶艳丽。
如今上海弄堂,一条条少下去。即使仍住在弄堂里的女孩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会聚在一起跳绳、跳橡皮筋了。她们被越来越沉重的书包,压得喘不过气来。若是寒暑假,她们也不会三五成群地聚在弄堂里。她们的目光老早越过弄堂,投到更远、更广袤的世界。
我定居杭州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当来到上海,我总忘不了去童年生活过的弄堂看看。弄堂虽然没有了从前的喧闹,却是历史的见证。这里曾经生活着我的祖父、祖母,一个家族的人。这里有我童年的梦幻和希冀,也有我与表姐姗姗朝夕相处的时光。那时光姗姗经常带我到外滩看轮船,到百货公司看花布。她总是让我帮她挑选花布。但往往我选准的,她又不买。好几次我都不想跟她出去,但她一叫,我又去了。
现在,天气凉爽了下来。八月下旬的午后坐在出租车上,已不用开空调了。我与姗姗约好在“美美百货”,宁静的咖啡吧里见面。这里出没的大多是外国使馆的先生小姐,或者是上海的奥菲斯先生小姐。这里的服装首饰,即使在减价期间,价位依旧令人咋舌。因此,这里永远是宁静和优雅的。
我到达“美美百货”时,距我们约定的时间尚早,便沿着淮海中路一直往前走。这是我熟悉的街道。虽然留学美国几年,却是一回来就先回到了这里。这里过一个十字路口,左拐弯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弄堂了。都说西区长大的女孩子,被充满殖民地气息的异域风情,培育出了优雅的气质。我想想也是有道理的。
八月里的天,也像小孩儿的脸。刚刚还晴空万里,忽然一个劈雷就下起雨来。雨下大时,我正好回到了童年的故居。只是这里的住家,已全部是陌生人。我站在屋檐下躲雨,望着已经苍老斑驳的房子,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回到上海了。
那个我与姗姗曾经住过的屋子,传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那是一个小女孩坐在琴凳上,弹着枯燥的车尔尼599练习曲。她让我把时光倒流到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没有钢琴弹,也没有玩具玩,偶尔有零食吃就高兴极了。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大米、面粉、猪肉、豆制品、油、糖等等,都要凭票供应。那时候祖父已经去世。我的父母与姗姗的父母,也早已离开上海去了别的城市和农村。我们祖孙三人,相依为命。
祖母是旧时代的上海淑女,经过日积月累的思想改造,收敛了很多旧习气。但浸透在骨子里的贵族气,仍然会掩盖不住地流露出来。比如教养、比如雅致、比如文静、比如讲究。尽管那时候再讲究,我们的生活也是清贫的。但接受了祖母的影响,我们懂得生活是重要的。所以一旦父母寄钱来,祖母给我们零花钱后,我们就会去逛马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祖母则会在厨房里,烧一块越缩越小的红烩牛肉。她的老脸上,总有着深深的绝望和温情。因为祖父遗留下来的钱,被银行冻结。家里的钢琴、红木家具和金银首饰,统统被“造反派”抄家拿走了。
我们弄堂的东口,有一个小酒馆,门面很简陋。玻璃橱窗内,卖酒、白宰鸡、猪头肉、皮蛋、花生米,早上还卖肉包子和刀切馒头。到了夏天也兼卖棒冰和汽水。祖母对汽水不屑一顾。她常说,这哪里比得上她年轻时候喝的可口可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从没有喝过可口可乐。弄堂的西口,有一个水果摊。苹果、香蕉、枇杷、桃、李子、西瓜都是按季上市的水果,但买的人并不多。小孩子通常买最便宜的李子。红心李子吃起来酸酸的,也很爽口。有一次姗姗买回来十个红心李子,我一下午就吃掉了七个,剩下三个给她吃。她从不计较我多吃。她的谦让,让我觉得是应该的。谁让她是我的表姐呢!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多吃的,像李子多吃了就让我肚子痛。祖母说桃子起病,李子送命。姗姗便幸灾乐祸地说:“看你还要不要做馋猫了?”
姗姗的幸灾乐祸并无恶意。可是我总想着要报复她一下,心里才痛快。那天邻居王家姆妈,送来两张《英雄儿女》的电影票。王家姆妈是因为祖母常送给她自己用铁勺子做的蛋饺,才把慰问军属的两张电影票送给了我们。我们当时正在吃午饭,祖母说 她是老眼昏花看不来电影了。祖母催我们快吃饭。祖母要我们姐妹俩,结伴去看电影才放心。她说电影院门口,有票贩子和小流氓。
姗姗吃饭很慢,祖母就不断地催。我到天井里逛一圈回来,见她还没吃好,也煞有介事地催她。然后恶作剧地将鸡毛掸子上的鸡毛,拔几根下来插在她的小辫上。由于我催得紧,姗姗来不及吃完碗里的饭,就和我去看电影了。这时离放电影只有七八分钟,我们一路小跑着去电影院。我跑在她后边,看着她小辫上的鸡毛跑起来一颤一颤的,便暗暗地偷着乐。她一点儿不知道我的恶作剧,而我竟然觉得很好玩,直到走出电影院也没有把它摘下来。当然走出电影院时,我已经被《英雄儿女》中王芳唱的“风烟滚滚唱英雄……”感动极了,压根儿没再注意她小辫上的鸡毛。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只要想起她,她小辫上的鸡毛,就会一颤一颤地在我眼前浮动。我有时想向她忏悔,不想再被这鸡毛折磨自己了。可是如果我真向她这样做了,她准会哈哈大笑,说我酸透了。
我就这样站在童年故居的屋檐下,一边听着小女孩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一边想着姗姗。雨还在继续下着,我正犹豫着是否冒雨前行,小女孩忽然从窗子上探出头来对我说:“阿姨吃糖。”
小女孩大约七八岁,她的模样很像小时候的姗姗。圆圆的脸蛋,眼睛很大,睫毛也很长。这是又一代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子。我接过她的糖,那是一粒瑞士糖。如今的女孩子吃进口糖,已是很平常的事。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就十分稀罕。记得有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天气变得很糟糕,雨淅淅沥沥地下得没日没夜,梧桐树全淋透了,变黑了。街上的积水全是黑色的,店堂里的地也全都是黑黑的湿脚印子。我在食品店糖果柜前,看到有进口糖。进口糖贵极了。进口糖的糖纸也漂亮极了。于是斗胆把祖母叫我到南货店买黑木耳、金针菜的钱,统统买了进口糖。回家自然是挨祖母的骂,不过总算第一次吃到了进口糖。
现在我吃完小女孩给的一粒瑞士糖后,雨渐渐停了。我也就此向已回到琴凳上的小女孩挥挥手,到“美美百货”去。我在“美美百货”,宁静的咖啡吧里等姗姗。姗姗还没有来,她总是慢腾腾的习惯,一辈子也改不掉。我只好自己先坐在临窗的咖啡座上,要一份“卡普奇诺”,然后一边喝,一边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我沉思着,想着姗姗的过去和现在。
姗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已经是个初中生了。那时候她长得白白胖胖很丰满,两只日益长大的乳房,由于不用胸罩,跑起步来一颤一颤的,让她羞愧。所以她最讨厌上体育课,讨厌那些男生注视她的目光。那时候女生都不用胸罩,仿佛胸罩是成熟女人的专利。女生们最尴尬的日子,就是夏天。夏天女生们穿着薄薄的衬衣,风一吹衣服便贴到胸脯上了。这时候女生们都会弯一下腰,尽量不让乳房显现出来。姗姗特别羡慕班里乳房不大的女生,她觉得她们不用像她这样弓着腰、驼着背走路是一种幸福。
祖母曾给姗姗买过两个白布胸罩。祖母说你戴上这个,把背挺起来。姗姗心里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但还是听话地戴了起来。然而到了学校,男女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冲着她的背部,让她感到十分羞涩。她的脸一阵阵地泛着红晕。她想那胸罩一定被白衬衣映照得清晰无比,她恨不得马上回家脱掉那东西。
姗姗后来在初中时期,再没有戴过胸罩。但男生们依然给她取了“白吊带”的绰号。这绰号让姗姗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有一次她放学回家冲祖母道:“都是你!都是你要我戴那该死的胸罩,现在班里同学背后都叫我‘白吊带’,有的还当面叫。”祖母说:“那你再戴,他们就不敢叫了。你这样懦弱,你怎么比你表妹还不如呢?”
祖母说的“表妹”就是我。我只比姗姗小一岁。姗姗读初二,我读初一。初一的我,也到了发育的年龄。只是我比较瘦,用不着戴那东西。但我毫不犹豫地穿上祖母为我们姐妹俩买的皮鞋,姗姗却一直不敢穿。因为那时候班里没有人穿皮鞋,大家都穿布鞋和球鞋。
姗姗被祖母责备后,便不再作声。她回到我们合住的房间,趴在书桌上写字。姗姗喜欢写字,但她的字绝对没我写得好。祖母要给远在异乡的儿女们写信,总是找我代写而不找姗姗。为此,姗姗有一种失落和妒嫉。我知道姗姗总是千方百计,想讨祖母欢心。有一天她从书店买回来一本《红色娘子军》组曲音乐和完整剧本。音乐是五线谱的音符,包括序曲与正剧。她在收录机里播放的时候,祖母很高兴。第二天她又买回来《红灯记》、《杜鹃山》。《红灯记》里面全是剧照,封面是李玉和高举红灯闪闪亮。
那时候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革命样板戏。其中《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是芭蕾舞剧。它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化成了优美的旋律与舞姿。我曾经听着乐曲,掂着脚尖,扮着穷人的女儿吴清华和喜儿。然后把客厅当舞台,奋力飞跃,感觉像弧光一样滑过舞台。这时候祖母就会说:“你发神经啊!”
姗姗不会像我这样发神经,但她比我更喜欢《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她说吴清华那一双美丽的眼睛,那一种舞姿与造型,是记录着一种年代的声音。还有她的装束也很特别:灰色军帽压在浓密乌黑的短发上。那双绑腿的布带,打得多么结实。灰色的上衣,手里的长刀,威武的英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战士,在万泉河边把大红枣儿献给解放军。
我第一次听姗姗发表这样的高见。“一种年代的声音”这句话,让我觉得很特别。我就是从她这句话开始,对她越来越有好感。于是她喜欢吴清华,我也喜欢上了吴清华。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寻访,终于在一家商店买到了印有吴清华挥舞长刀,耸立在淡绿色石膏塑像上的浮雕。我把它作为一盏台灯的底座,灯安在上面,在夜晚发出黄色光焰。我就在这盏灯的黄色光焰下,做数学题、写作文、背英语单词,还给住在我们弄堂七号墙门里的一个同班男同学,写了第一封情书。
那时候我有事没事,就往七号墙门跑。姗姗就在她的书桌上写字。她写《杜鹃山》里柯湘的唱词:“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洒热血,求解放,生命不息斗志旺,胸臆间浩气昂扬。虽陷魔掌,使命不忘。冲开这刺刀丛,极目远望,似看见密林中银光闪闪红缨枪……”姗姗一边写,一边把黑黑的墨水滴在了淡湖蓝的裙子上。祖母看见了就骂姗姗笨,写不好字还把裙子弄脏了。祖母想到弄堂东口的小酒馆里买黄酒,她在煎鱼就让姗姗去买。姗姗刚被祖母骂,心里又想着别的事,便神不守舍地还没有走到小酒馆,就把钱丢了。自然,姗姗又遭到了祖母的一顿骂。这天姗姗觉得倒霉透了。夜晚她又在笔记本上写字,写了很多无法对人言说的愤怒。那愤怒在夜晚变成了燃烧的火焰,撕裂着她。她看见烧毁的花瓣落在地上,发出黑色亮光。她默默地流泪,星星破碎了,火焰积聚着就要冲破堤坝的阻拦。
这天我从七号墙门回家时,祖母冲我骂:“你死到哪里去了?买黄酒去。”祖母的话就是命令,我乖乖地去弄堂东口买酒,顺便还买回来三个肉包子。本来是一人一只的,可祖母要惩罚姗姗丢了钱,不给她吃。我偷偷地拿去给姗姗时,看见姗姗在白纸上写下这么一段话:“血的教训一层一层牢记心上。痛定思痛,你要把前因后果细思量。为什么砸开的铁镣又戴上?为什么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聚人亡?为什么听不进肺腑言,识不破弥天谎?追根寻源,征途万里长。涓涓细水入长江,乘风破浪向前方,永不迷航。”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傻傻地看着,只觉得说得有道理,便问:“谁写的话?”姗姗说:“这是柯湘的唱词,你怎么啥也不懂?”我的脸倏地一下红了。都说姗姗长得比我难看又比我笨,可她实在是比我好学又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