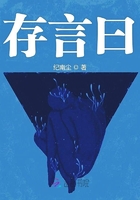法国朋友帕斯卡像一只候鸟每年秋天便飞来昆明过冬。他说汉语还不是很流利,但交流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他的太太是中国四川人,年轻时候四处闯荡做生意,到了三十多岁学习法语,认识了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帕斯卡,凑巧两人相互学习对方身上的语言,结了婚。太太很漂亮精明,在昆明有房,离清华书屋不远,帕斯卡就是从那里走过来买书我们认识的,他很喜欢叫我找书,我工作还算诚恳。
后来有一次帕斯卡告诉我正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希望有人帮他标记名著里关于吃人情节的描写。我对他说:“很乐意效劳。”他没有听懂。我只好说:“我可以帮助他。”他点点头看样子懂了,又强调希望能在二十天左右把这些情节全部标出来。我表示为难。领他到中国文学库位看那几本名著,对他说,“它们很厚。”我们挑了几个版本翻开,差不多每本七八百页,算下来每晚任务量很重。因为每天十八点或二十一点下班后回到出租屋才有时间干这事。帕斯卡耸耸肩,突然说:“《红楼梦》这本不用看,他知道里面没有吃人情节的描写,是吗?”说完把《红楼梦》单独放在一边,把其余三本堆在一起。那三本分别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我听了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啊,《红楼梦》可以排除,它写了四大家族从盛转衰的历史悲剧,应该不会有‘吃人情节’的描写。”当时我还没有看过《红楼梦》,但关于这本书的传闻倒知道一些,比如文学造诣极高,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红学研究等等。有时候想翻来读读,又怕破坏了美好印象或者害怕难于理解,就推辞等到人生过半的时候再读,到了那个时候应该气定神闲了,不像现在这么浮躁,现在读完全是不自知。这种想法很可笑,很像江珊说过等她做月子的时候读《飘》。我们总把一些事情寄托在未来,今天总是等待,等到了什么时候?等有了什么?确不知如此等待是在找借口虚度今天,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
记得寒暑假的时候电视剧播过《红楼梦》,我们总是嚷嚷,“调开,调开,看不懂。”后来就播的少了。反而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播的经久不衰,里面许多剧情早已耳熟能详,还是百看不厌。一部是孩童爱看的妖魔神仙,一部是中年人爱看的好汉路见不平,一部是老年人爱看的战争谋略布局。尽管这三本名著很多人除了课本节选都没有读过,亦不能影响他们的喜爱。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此时帕斯卡邀请我帮他读这些书,我感觉很荣幸也有一种忐忑的心情,尽管已经读过一些外国经典名著,反过来读老祖宗的东西还是很紧张,好比一个漂泊的游子回到祖国那般感触,帕斯卡把我的归期提前了。
我问帕斯卡怎么想到研究这样的课题?帕斯卡说:“因为他读了鲁迅,鲁迅写了人吃人的社会。他就想中国古代文学应该有这样的写法,那么先研究四大名著。还举例说鲁迅写过蘸血的馒头,《水浒传》里有人肉包子,好像有些关联,是不是这样?”我不认为是关联,觉得是中文语境问题。不过还是很愧疚,说到鲁迅,除了能立刻背诵的:鲁迅原名周树人。别的只在课本上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少年闰土》、《故乡》、《孔乙己》,除此都没有读过。后来买了一本《鲁迅小说集》,封面便是鲁迅头像照片,这张黑白经典照片很熟悉,经常出现在学校或者图书馆显眼而又重要的墙壁上。
帕斯卡说:“我可以找两个同事一起合作,到时候请我们吃饭。”他说这话已经有一种入乡随俗的感觉,我嘴里说,“不用。”倒是想起了江珊和林芬芳,果然她俩很乐意帮忙,和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江珊是因为合适,至于林芬芳完全是因为我感情用事想把她拉拢过来。我喊她俩来到文学库位这里,介绍给帕斯卡,帕斯卡喊她俩为小林、小珊。她们点点头,愿意帮忙。帕斯卡就把三本书摊开给我们挑,挑自己要读并标记吃人情节的一本名著。标记的不一定非要现场吃人,有此想法,有此对白,有隐蔽吃人结果等等蛛丝马迹都要标记出来。“拜托了。”帕斯卡双手抱在一起向我们前后作揖。我们都笑了。我问江珊要看那本?江珊说:“要看《水浒传》。”我说好,那么这本归你。又问林芬芳剩下的挑那本?之所以不先问林芬芳是我知道她不喜欢看书,怕问话在她那里就卡壳。她说:“随便。后面又说《三国演义》吧。”让我很意外。
帕斯卡从书店买了这三本书发给我们,还发了三支做标记的铅笔,我们抱着书笔仿佛三个刚领到作业的学生。
过了几天,十八点下班后,帕斯卡请我们三位去文林街喝咖啡。我们很乐意,出了清华书屋,从天桥上跨过一二一大街向文林街走去。
我们都不是第一次去文林街,用不着惊异的张望,直奔帕斯卡所说的咖啡店。帕斯卡已经在里面等着,坐在一张靠窗靠入口的桌子边,看见我们立刻站起来招呼,这里这里。帕斯卡身材高大,脸色淡红像一个秋天的南瓜,鼻子高耸,金黄的头发往后梳,眼睛天蓝色宛如宝石。我们纷纷落坐在帕斯卡两边,坐定后他问我们吃什么?把菜单推给我们,并说这家咖啡馆的咖啡和披萨味道不错,他是这里的常客。吧台里的服务员对我们点点头。我们看着菜单不知道点什么,传递几次还是点了三杯卡布奇诺咖啡,一个披萨,几个面包几个小玩意零食。等食品上桌的空闲,帕斯卡问了我们老家那里的,问话大致这样:“小珊你老家那里的?”我们扑哧笑出来。我纠正说:“这才是小珊,你刚才问得是小林。”帕斯卡也笑了说“对不起,现在记住了。”又问小林你家那里的?我们都介绍了自己来自那里。帕斯卡不知道这三个地名,可能理解为很远的地方猛林里的村庄。这时候谈话被打断,前后进来两个人,都认识帕斯卡,前面那位是法国人,进来和他说了几句法语后走了。后来这位不知道那国人,白色人种,他和帕斯卡聊了几句英语,带一个披萨也走了。我们不知道说了什么,但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们端坐着,似乎能够听明白话中意思一样。他们可能谈论今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比较暖和,问帕斯卡怎么和三个学生坐在一起?帕斯卡回答才认识不久。前面那个人进来时和他拥抱祝他好运,后面这个人只是和他握手,我们坐在桌子边一会看见两个结实的拥抱一会看见两只汗毛浓密的手握在一起,显得很渺小。或者他们聊的是很久不见去了那里,回国去了一趟才飞来昆明两天,似乎也有这意思。
这家咖啡馆里除了我们里面还有两桌学生似乎在谈爱情。我们这桌重又平静下来,我问帕斯卡他是法国那里的?帕斯卡说了一个地名,完全没有听懂,也许这个地名是帕斯卡第一次把它从法语翻译成汉语。我重复问:“那里?法国那里?”帕斯卡解释说:“离巴黎很远的地方,接着还想往下解释,可惜找不到说出来我们能够认知的标志,只好又说了一遍那个五个字的地名。”我只能点点头,一脸茫然的装作知道了。我把那个地方想象成漫山金黄的草地,仿佛莫奈的一副印象画。
咖啡端了上来,帕斯卡说尝尝,觉得苦可以加糖。每杯咖啡旁边放着一小袋白糖。我们喝咖啡都要加糖,怕苦。这年头喝咖啡正在大学生和精英阶级流行起来,咖啡馆开在靠近学校或者繁华的街上。不过广大人民还是喜欢喝茶,比如我一年喝几次咖啡数得出来,喝茶却能灌成一面小湖,茶文化已经延续了几千年。这家咖啡馆果然地道,味道比别的地方苦。
披萨端了上来。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盯住看了一会,很稀奇的名字竟然这么普通,不就是一个大饼上放点番茄酱、肉丁、奶酪、洋葱、胡萝卜、生菜等放烤炉里烤出来,味道看着也就那样。帕斯卡说:“味道不错,尝尝。”说完用刀子切成几块,叫我们拿着吃。我们每人取了一块,刚要塞嘴里。帕斯卡忙说:“慢。”说完从桌边佐料盒里取出两个银色小瓶,每瓶拿起来向披萨上抖抖,洒出几粒像芝麻像胡椒的颗粒,如此才把披萨放嘴里津津有味吃起来。我们依葫芦画瓢的也把黑暗料理往披萨上抖抖吃起来。我不知道她们感受如何,我只觉得是大饼烤酸了的味道。帕斯卡吃完问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说不错不错,帕斯卡立刻递给我一块,我连忙推脱说,“从小不爱吃面食,刚才因为是披萨才破例了。”帕斯卡不能理解,继续在递。我只好说,肚子吃饱了,更不管用,只好接了过来,分给林芬芳一片,剩下的自己艰难吃起来。我看见林芬芳的手指上光溜溜的,上次我们一起喝咖啡可不是这样,我打量她脖子上的那颗痣,发现依然还在,它像一辆名贵车辆价值不菲的商标一样显眼。
吃到差不多,帕斯卡开始谈论工作,已经像我们中国人酒饱饭足才谈论正事一样。帕斯卡问我们看了多少页。江珊从包里取出《水浒传》翻开,差不多已经标注了二百多页,进度很快。帕斯卡很满意。而我和林芬芳都没有带书,我好像标注了一百多页,林芬芳说看了一些说的没有什么底气,帕斯卡希望我们继续加油,在预订的时间内完成,我们都点点头。
这时帕斯卡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说了几句法语,对我们耸耸肩。我们猜测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夫人驾到了,帕斯卡拉一把椅子让她坐下来,并向她简单介绍了我们。夫人身材苗条,手指细长如同弹钢琴的,瓜子脸皮肤很白,但从眼里可以看出风霜,不如说见多识广。她打量着我们,为我们大好年龄浪费在书店感到惋惜,因此说了她以前如何奔波辛苦的经历给我们听,用中文说,有时候为了照顾帕斯卡,说几句法语翻译。如此优雅自得的女人让我们大开眼界,深受鼓舞,可能暗自里想过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仿佛我们以前想过的理想一样,后来不了了之,现状本该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却视而不见,也许我们有意忽略它,不敢面对我们自己,早已逃离了自己的内心,以一个别人的角色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