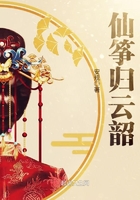《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 文\女真
选自《满族文学》(双月刊)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女真:本名张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编审、一级作家,写作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文体。现为辽宁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艺术广角》执行主编。
那个女人进来之前,先拉开车门,问他:“师傅,可以把空调关上吗?”
这个夏天格外闷热。三伏天,乘客大多嫌空调不凉,出租车上下客频繁,保温性差,加上他舍不得油,温度开得不够低。像她这样要关空调的,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乘客说关,那就关。他这个人好说话。为人民服务么。况且这个女人虽然说话温柔,很有礼貌,看着像商量,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出租车司机,尤其夜班司机,愿意琢磨乘客的身份。闲着也是闲着,天天在街上压马路,眼睛里除了红绿灯、机动车就是行人,太单调,琢磨点啥好捱时光。在厂子上班时,他就是个爱琢磨的人,小点子、小发明不断,当过创新标兵。厂子减员,开上出租车,老习惯没改。
开白班时,注意力相对集中。要听交通台的路况广播,公司的派活通告,司机群杂七杂八的消息。白天路况复杂,空车时向马路边踅摸乘客,车多,人多,警察也多,得时刻小心。白天乘客的身份相对容易辨别。去火车站、机场的是旅行者,去商场的购物,去写字楼的是白领,去学校的是老师、学生。晚上不一样。夜色降临,人与人之间一下子暧昧起来。从酒楼、大饭店、洗浴场所出来的,尤其让人琢磨不透。越来越琢磨不透。十年前刚开出租车时,他还以为自己琢磨得挺透。夫妻关系,同事关系,情人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生意关系,八九不离十。你听上几句话,看几个动作,差不多。现在不行了,越琢磨越糊涂了。拉这个女人之前,他刚从皇姑房产局那儿过来。一个女人,三个男人。女人坐前面,上车先说了一个浴池的名字。这个女人恍惚面熟,仔细一想,真还想起来了。是机床厂的。具体干什么的不清楚。重型和机床厂挨着,搬迁开发区之前,两个厂就隔了一道墙,两个厂的工人经常互相到对方的食堂吃饭或者打水、洗澡,像一家人。工厂里男人多女人少,他对女人有印象,看来女人对他没印象。他这个人长得平凡,掉人堆儿里找不着,对他没印象很正常。后面三个男人,其中一个也是机床厂的,跟女人是两口子!他想起来了,有一年搞技能大赛,那小子上台表演过,是个钳工。好像手艺还不错。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厂子里上班。现在的机床听说都数控了,用电脑操作,老钳工还能派上用场吗?他想张嘴搭讪两句,忍了忍,把嘴巴闭严了。人家并没有认出他来。而且还有两个陌生人,万一人家不想让他认出来呢?挣点辛苦钱得了,别节外生枝。到了浴池门口,女人自己下车,让他稍等,进浴池待了半分钟,上车,扭头告诉后面:“这儿没有了。以前有来着。再换个地方吧。师傅,你知道这一带哪儿有小姐吗?”
一句话让他差点背过气去。见过男人找小姐,没见过老婆带着老公还有别的男人一起出来公然找小姐的,即使就是给那两个男人找吧,也他妈的太邪性了。现在的老婆,已经不在乎到这种程度了吗?
到了一个更大一点的洗浴中心门口,他说了一句“这儿有”,三男一女齐刷刷下去了。他踩上油门开始跑。这儿真有吗?他不知道。也许有。主要是他心里别扭,不想再看见这几个货。
往北陵这个方向溜达。开到成龙花园门口,就看见这个女人招手。看她的气势,许是有钱人家的大奶,也许是二奶。成龙这儿曾经住着沈阳先富起来的一拨人。这儿的地理位置好,紧挨着北陵公园,离省政府也近。现在住这儿的也不是一般人家。多少都得有点钱吧。女人的年纪介于三十到四十之间。上车时带进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挺高级的。他把空调关掉,问:“去哪儿?”
“中街。”
还行。开夜班车,他愿意在城里晃荡。夜晚的出租车,麻秆打狼两头怕。司机提防乘客,乘客也提防司机。几起恶性绑架出租车案件,都发生在晚上。刚才他急于把那几个货放下去也是加了小心。一个女人三个男人,大晚上的,真要是动手,麻烦。不是他愿意往晦气上想。两口子都能一起出来找小姐了,谁知道还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其实乘客晚上出来多少也防着出租车司机。经常有送客的记下出租车号,明显的留一手。碰到这样的乘客,他反而放心了。
中街在城里,很早以前叫四平街,老沈阳城的繁华地带。商场林立。这个时间商场已经关门了,黑灯瞎火的,女人上中街干吗?去玫瑰大酒店?也许她只是到成龙花园这儿来串门,看熟人,真正住的地方是玫瑰大酒店吧。听口音可能不是当地人。女乘客让人放心。只要她半途不停车,不再往车上招人。顶多也就不给钱。司机哥儿们里流传着一个段子,说某夜班司机拉了一个女孩子,跑了挺老远的路,女孩子还挺健谈,跟司机聊得挺高兴。到地方,女孩子大大方方告诉司机:“大哥,我没钱给你,要不,我让你看一眼?”
他从来没碰上过这种事情。他甚至不认为这种事情是真的。没准儿是某个夜班司机给自己解闷儿的性幻想。开夜班车的司机,跟当年车间里上夜班的工人一样,黑白颠倒,生活都不正常。你下班时老婆正熟睡或者该起床上班了,你在家睡觉时大多数人正在外面忙忙碌碌。想入非非也正常。
这个女人不像那种女人。穿长裤、短袖T恤上衣。很正经地坐到后面,不像有的乘客偏爱副驾驶。其实他愿意乘客坐后面。彼此都方便安全。
“中街什么地方?”中街范围一大片,有单行道,问清楚了少走冤枉路,免得起纠纷。也是借机会想听女人说话。女人的声音挺好听,不是地道的沈阳话,有点像吉林、黑龙江那边的声音。沈阳话土,没有那边的话好听。
“玫瑰大酒店。”
猜对了。猜对了的感觉很爽。女人把后面的车窗摇下来,他也把前面的摇下来。夜风吹走了车里原来窒闷的凉气,外面的空气是热的,他身上一下子出了汗,但车速带进来的夜风,很快将热吹走了,变成了一种通透的爽。出汗的感觉其实挺好。夏天出不来汗,不舒服。他出过汗,又被风吹散了,身体比原来闷在空调里舒服多了。夜晚的崇山路车比白天少,可以开到六十迈。他从后视镜往后看一眼,女人在向外面看,面无表情。
从柳条湖桥向南拐,过小北关街,过天后宫,从小南门拐向大南门,再一个弯儿,已经能看见玫瑰大酒店了。玫瑰大酒店刚建起来时是沈阳挺高级的地方,在中街一带鹤立鸡群。现在一般了,落伍了,更高级的地方多的是。五里河那一带,万豪、喜来登,太原街的商贸,铁西的好多大酒店,都比这儿豪华。他把车停在酒店的路口。酒店在路东侧,栅栏与车道隔着,那边是步行街,不通车。女人坐着不动,他提醒了一下:“到了,车进不去了。”
女人有一会儿没说话。也没有掏钱的动作。然后,她说:“师傅,麻烦您往音乐学院那边儿开吧。我不在这儿下了。”
这个意外让他不快。这条路是单行道,从南向北行驶。为了把女人送到离酒店最近的地方,他已经从南往北拐了弯儿。音乐学院在南边,现在往南行,他还需要绕着走,是一种挺别扭的走法。司机顶讨厌这种拐弯抹角。况且你就是改变了主意,也应该早点儿说话,别等着到了地方再言语啊。
他从后视镜往后看,观察着女人:“音乐学院的南校区,还是北校区?”
南校区出城了,在浑南,得过浑河大桥,远着呢。晚上他不爱走。北校区在三好街,三好街是电脑街,白天车堵得厉害,这个时间还行。
“三好街的那个。”
“噢。”女人对沈阳挺熟悉。至少她知道音乐学院在三好街。没准儿她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沈阳音乐学院出了不少唱歌的名人。这种联想让他又认真看了一眼女人。听说有的女名人不化妆跟平常人一样,你根本就认不出来。女人的眉眼儿,细琢磨挺耐看。那也认不出来她是谁。他很少有时间看电视,偶尔看也是看电视剧,对唱歌的一点不熟悉。唱歌的就能认出个那英,还是因为她跟踢球的高峰闹过绯闻。他是个球迷。在厂子上班那会儿经常去五里河看球。这么晚出来闲逛,不让开空调,没准儿就是出来透气的闲人。在空调里憋了一天,受不了了,又不敢自己散步,干脆坐出租车吧。如果是这样,那他今天的活儿挺合算。一个有钱的女闲人,在街上没有目的地走走逛逛,不会少了他的车钱,比他在小区门口蹲着等活儿强,比他在大马路上空跑强。已经十点半了,从现在往后,打车的人越来越少了。
车拐了几个弯,重新开始从北往南开。到文萃路,开始往西走。离音乐学院很近了。女人一直不吱声,必须提醒她一下:“您到音乐学院正门吗?”音乐学院的正门在三好街,后门与电视台一路之隔。不在一条街上。
“正门。”
又不吱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在夜晚的出租车上一声不吭挺难受的。晚上开车,他愿意遇见饶舌的乘客。那样时间过得快。没办法,遇见这么个主儿,人家不爱说话,咱也别讨人嫌吧。
车停到音乐学院门口。三好街卖电脑之前,音乐学院的大门看上去很宽敞,现在被两边的大楼欺得小门小户的了。门口没有人出入,灯光昏暗。女人仍旧不动弹。他有点急:“您是到音乐学院吗?到了。”
不用回头,他也知道女人根本就没动弹。别告诉我你又改主意了!还好,女人从后面递过来一张百元大钞。票儿大了点。要找她六十多呢。出租车司机都愿意要零钱。万一碰上假钞,不但没挣着钱,还得往里搭。现在假钱做得比真的还真,谁能一下子辨认那么准。他犹豫了一下,想问女人有没有零钱,没等张嘴,女人说话了:“师傅,对不起,我不在这儿下了,您放心,我会给您钱的,我先把钱放您手里。我就是出来散散心,麻烦您随便开吧,别出城就行。”
他知道自己遇上麻烦了。这个女人有问题。不差钱。或者说不差这点出租车钱。不知道她是差点啥。被老公甩了?跟铁子吵翻了?不可能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一个年轻女人,什么问题没有,半夜三更的,花钱让出租车拉着满城跑,精神病啊?最简单的办法是收了她的钱,把该找的钱给她,告诉她自己还有事,或者干脆就是该收车了,请她就地下车,另请高明。街上空车有的是。一个较真儿的女人,也许会告他拒载,那也比他遇见更大的麻烦强。可是万一她今天晚上遇见什么不测呢?比如被害了,失踪了,他的麻烦就更大了,跳进浑河也洗不清了。他小的时候还真在浑河里洗过野澡,被老爸发现了一顿胖揍。也许没有人看见他载过这个女人,也许她安全回家里跟老公安心过日子去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但他的心会不安。也许会一辈子不安。就像当年他开天车时出过的那个事故。铁笼子钩没挂到位,掉下去了,差一点砸上人。下面有作业的工人,砸上就是死,没商量。他到现在有时候还做噩梦,醒来时浑身冰凉,嗓子里咸咸的。所以,厂子精简到他时,他虽然很难过,还是认了。他不下别人下。总得有人下。至少不会再出现那种事故了。他会开车,不开天车了,到马路上开出租。老天爷饿不死手艺人。
踩了一脚油门,车子往前蹿去。到三好街和文化路路口,车往西拐。只要不出城,那就上铁西吧。铁西的马路他闭着眼睛都能开。上了二十年班的地方啊。虽然现在铁西变化很大,工厂大部分都迁走了,原来的厂区变成了商品房,那他也知道哪个小区原来是什么厂。鼓风机厂、机床、重型、啤酒厂,都搬走了。头几天他陪外甥去看房,外甥看上新开发的一个小区,他一到那儿就乐了:不就水泵厂吗?连厂子进门的那几棵大树都没砍。他认识不少水泵厂原来的老人儿呢。他青年点儿的一个女同学,回城以后就在水泵厂上班。
女人不爱说话,让她听广播吧。他调台。女人说:“师傅,麻烦您把广播关了吧。我想清静清静。”
女人的声音不对头。哭了!他想把车靠马路停下,犹豫一下,接着往前开。他不是慈善机构,没有必要替女人省钱。但是忍不住咕哝句:“这么伤心啊?”不知道她听见没。想清静清静,看来是吵架了啊。
女人又说一句:“不好意思,您接着开吧。”
那就接着开。他想告诉女人,什么事别想不开。车到山前必有路。人不可能一辈子总好,也不可能一辈子总走屎运。他从青年点回城时,以为自己运气好。当上工人了么,还是国营大厂,多少人羡慕啊。谁知道留在青年点的一些同学,上中学时还没他成绩好呢,因为没回城,恢复高考时拼命复习考大学,结果后来当大学教授了,当官了,而他一直就是个工人,最后还精简回家了。怨谁呢?能直接挣钱了,家里不让他考,他自己也觉得当个工人不错了。只能怨自己目光短浅。头些年,沈阳机床的职工股上市,多少人悔青了肠子。想当年机床卖职工股,一块钱一股,机床的工人有不愿意买的,拿着手里的指标到重型这边卖,一个指标五十块钱,可以买一千股。职工股后来上市了,最高三十多啊,还不算送股,翻了几十倍,能买辆夏利。当年有人问过他买不买,他手里有一千块闲钱,但是没买。就不明白股票是怎么回事。也后悔过,但并不是十分后悔。机床那边有个人,原始股买了不少,发财了,进了大户室,辞职专门去炒股票,熊市时,家当全套里了,人竟然疯了,进精神病院了。你说,当年那财发的,好还是不好?他没发财,也没疯。他下岗了,他的儿子念的是公费研究生,将来的生活会比他强吧。生活不就是这样?
他想用自己的经历劝说女人,话到嘴边,还是没说。你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一个老百姓,说出来这点儿小道理让人笑话。
手机响。是木琴的声音。很好听。小时候他在少年宫听过木琴演奏。他把车窗往上摇了摇,风太响,女人也许听不清楚。他听见女人说:“对,我出来倒垃圾,没带钥匙,风一吹把门带上了。我现在外面,你什么时候回来?”
撒谎!谁家倒垃圾穿这么整齐,身上揣手机,还带百元大钞,还到处乱跑,还哭?给她打电话的也许是她男人吧,在外面有情况了,不回家,女人找不到更好的理由,编了这么个谎言,哄男人回家?
管她呢,只要她主动要求下车,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这趟活儿有点让他不省心,可钱上没亏。是个大活儿。再挣上一百,他今晚就可以收工了。给车加满油,回家睡觉!
他听见女人吩咐他:“师傅,回皇姑,到陵东街,海德公园。”
不对呀?她不是从成龙出来的吗?怎么又去海德公园了?两个地方倒是不远,理儿上不对!成龙是她家?海德是她家?话里的意思,应该是海德!这个女人,不那么简单!老公没在家,自己出来约会,然后闹别扭了,不想回家?老公回家没人,给她打电话催她回家?
一直挺同情女人,难道是另外一个男人更应该让人同情?
想不明白!现在的人真是复杂啊!昨天晚上,也是十点多,他在重庆小天鹅火锅店门口揽了个活儿。一男两女。一个女的坐副驾驶,一男一女坐后面。后面俩人唠得挺投机,亲亲热热,说着下周三男人的老妈过生日,女人想去捧场,又怕男人的老婆看出来什么。两个人商量着去了怎么说。前边的女人还给后面的俩人出主意。先送前面的女人下车。他有点看明白了,后面俩是情人,铁子,前面的女人是后面女人的女朋友。前面的女人住三经街,后面的女人住浑南。住三经街的女人下了车,车往浑南开,后面的俩人动作越来越大,他假装没看见。女人下车时男人还亲了她一口。到浑南河畔新城,把后面女人放下去,男人告诉他回城里。车往城里开,男人打电话,嗓门儿挺大,你想不听都不行:“燕儿,你在哪儿?”燕儿是前面女人的名字。“还在楼下凉快啊?我马上过去,住你这儿,今晚不走了!”车到三经街,他刚才放女人下去的地方,那个叫燕儿的女人已经等在小区门口,两人挽着手进了小区。他在院门口愣怔了好一会儿。什么事儿啊!真的想不明白!男人到底跟他妈的哪个好啊?见过跟女人好的,没见过这么好法的。他已经琢磨了二十四小时,还是没琢磨明白。那两个女人之间知不知道啊?他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糊涂了。
就像眼下,他不知道这个坐了他车的女人是不是应该让他同情。她闹心,想清静,半夜三更在陌生人的出租车上哭,可是她跟男人撒谎。
海德公园建在原来的体育学院,出过不少世界冠军。这个女人住的地方风水不错。车停海德公园门口。女人说:“钱够吗?不用找了。师傅能把你手机电话告诉我吗?以后晚上我想用车可不可以给你打电话?我顶讨厌饶舌的司机,你这个师傅好。谢谢你。”声音依旧温柔,一点儿没有哭过的痕迹。她记下电话,下车,向海德公园门口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过去。没有拥抱,没有握手。倒是像两口子。男人交给她什么东西。真是钥匙?她没撒谎?他想把车开走,却又想再待一会儿。他想看着女人安全地走进小区里。女人转身进了小区,可是那个男人并没有陪她一起进去。男人竟然朝出租车走来,打开车门,第一句话是:“师傅,把空调开开成吗?”
成!乘客的要求就是命令。他把窗户摇上,打开空调。空调的凉气让他露在外面的皮肤马上绷紧了。男人穿休闲西裤、皮鞋、面料很厚的T恤,一看就是出入高级场所的成功人士。他是那个女人的丈夫吗?回来以后为什么不上楼?他问男人:“您去哪儿?”
“中街。玫瑰大酒店。”
很好。很有意思。像一个故事。原来那个女人去玫瑰大酒店并不是心血来潮。也许男人是她的丈夫,在外面有了情况,女人知道他在那个酒店,已经想上去闹了,临时改了主意。所以她才哭,才想清静清静。这么解释合理吗?
有那么一点道理。
这两口子,都是沉默寡言的人。他打开广播。男人没反对。
夏天的这个夜晚,他走了一条差不多相同的路线。第二次比第一更快。感觉上是。但他对男人和女人坐他车上感觉不一样,尤其男人和女人好像还有什么关系。一种说不清楚的什么感觉。仍旧走崇山路,走柳条湖立交桥,走小北、天后宫,从小南往大南拐。车到玫瑰大酒店楼下,刚才女人下车的地方,他把车停下了。男人递给他一张二十元的钞票,看他仔细找零钱,还他让把票据打出来。他看着男人下车进了酒店,犹豫着是在这儿等会儿,还是去马路上溜达。这个时间,街上的人已经很少了。他决定在原地等一会儿,但没决定是关了空调还是继续开着等。他不喜欢空调,这个时间外面已经不那么热了。但万一再上来个乘客是喜欢空调的呢?这么打开、关上的最费油。
等了二十分钟,没有人叫车。手机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吓他一跳!谁会在这么晚的时间给他打电话?但愿不是家里老爸犯病了。还好,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他把广播关掉,接听:“你好。”
“您好。”是一个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女声。“我是刚才坐您车的乘客。”他已经听出来了,是那个女人。她落了什么东西在车上吗?他回头看一眼,看不出来。“我麻烦问您一下,刚才你送的那位客人是在玫瑰大酒店下的车吗?”呵呵,今晚的故事还没完啊。她知道是他载走了她的男人?她在院子里没回家往外监视男人哪!“你能过来接我一下吗?”
能。为什么不能?他不想掺和进一个复杂的故事,可他没干别的,只是给一个女人当司机,女人出手很大方,会合理地给他报酬,何乐而不为?手艺人,挣一点辛苦钱。况且这样的客人让他想入非非,让一个酷热的夜晚过得飞快。
一脚油门,车轰地起动了。开出去一百米,猛然想起女人不喜欢空调。他把空调关上,把窗户打开,让午夜的夏风呼呼地吹着自己。在空调这件事上,他跟女人爱好相同。刚才在海德公园门口,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想过女人可能是个瘾君子,男人只是给她送货的人。现在看来,那会儿的判断是错的。
住在高档住宅区的有钱人不一定幸福。坐出租车花钱不眨眼的女人也不一定幸福。趁着一个红灯的机会,他活动了一下很难受的腰。拉完这趟活儿,他决定收工回家,睡觉。他实在是有些坐不住了。奔六张啦,年龄不饶人啊。
原刊责编 于晓威 本刊责编 付秀莹
责编稿签:作家是对生活满怀困惑的人,或许,作家的困惑恰恰来自于他的清醒。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看到的却是夜幕掩映下城市暧昧不明的表情。小说通过一位夜班出租车司机的眼睛,窥到了生活深处的漩涡和激流,看到了时代风潮中人的内心波澜和精神起伏,呈现出人物心灵隐藏的悲剧,掀开了斑驳复杂的人生世相的一角。
小说叙事沉着,优游裕如,在有限的篇幅之内,闪转腾挪,虚实相生,挑战了短篇小说的叙事难度,很好地拓展了文本内部意蕴空间,使得小说兼空灵与迷离、轻盈与丰厚之美。悬念迭起,惹人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