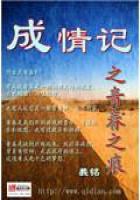太难受了,几个小时待在车厢里,空调开着窗也不能开,一股难闻的气味到处都有。
长途汽车好歹还可以开启个窗户缝。
到站下车,我差点吐了。怎么大家都乘的那么自在如意,我们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吗?下车的其他乘客一点都不嫌弃车里的味道。
是我的鼻子功能太好了,还是别人见惯不怪,我忍着除尘术都没用一个。
到了地方,原想叫辆出租车,好像有个不好的传言,于是我还是决定乘地铁。
进到酒店的房间,突然间就想去海滩。心血来潮,是在提醒我可以去海边找人吗?
我自然知道我自己住哪儿,孩子哪儿念书,父母亲住在哪儿。但是不能直接去啊,到时候人家问我怎么知道的?难道我起个八卦,说“算出来的。”
先去了婶婆从前住的地方,那儿拆迁了,房子都是新造的,我直接去了派出所找户籍警。
我拿出族谱的照片,还有我和姑姑的合影,同那个户籍警说,“我家失散多年亲戚,他们家以前住这儿,这两个。”我指着婶婆和堂姑姑的名字。
户籍警开始以为我从香港来寻亲的,态度有点谨慎,我告诉他族谱上的女儿现在50多,她应该改了姓跟着母亲的。4、5岁就和母亲同家人失去联络。
族谱上那个媳妇应该是80多岁了。可能年纪大的都给户籍警一些印象,这儿毕竟拆迁吗。
他立刻说,这个老人家拆迁的时候不在的,和母亲一个姓的母女也很少见,尤其年纪那么大的母亲。
后来他还找了同事一起回忆。
没想到真有印象,有这么个老人家的,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因为拆迁分房子没轮到,户口本上少了一个,很罕见的。而隔壁两户都不搬是钉子户。
别人家三个变四个,四个变五个,这家人四个变三个。一起的是儿子,媳妇还有孙女。
是舅舅,总算凑上关系了。
“能联络一下,问下知道裴美玲吗?”我有些难过,虽然早知道婶婆已是不在。
户口迁出去有备案的,一查就查到了。这回他们更是谨慎,唯恐我是坏人,也许家族里有遗产纷争。
我只能好好和他们解释,裴美玲是我叔公的女儿,她改姓了就是裴家的人了,我们家啥财产都和她不想关的。找她就是家里老人想三叔公了,想再见见他女儿。
户籍警也理解女子在大族里没啥地位,也不纠结。就和我说,你可别作奸犯科,找亲戚好事情,千万不要骚扰别人啊!
这也够负责的。我是否要写个表扬信?
结果倒是联系了,可是没想到,裴美玲说,“当年父亲死了,章家把她母亲和她赶回娘家,说女儿早晚出门的,不愿意养活寡妇孤女。现在母亲不在了更不要来往了。”
好了,找到等于没找到,我也不能随便见他们。但是找的其实最终目标是裴瑾,于是我对警察说,“不愿相见就不见,只是可以打听一下裴美玲的家人都健康平安吗?回去我也好和长辈交代。”
户籍警真心是个好人,马上就问了过去,倒是简单,裴美玲两个女儿,大女儿户口在家,小女儿结婚也没迁户口,户口本上还有外孙,也姓裴,在外区读小学了。
那个户籍警看到就望望我,大约是觉得他们家都跟着娘姓,那个裴家不简单啊,女婿都是上门的吗。
大跌我眼镜,真的好吗?怎么回事?难道男人都不在?我有些意外。记得当初没这回事儿啊。自己的孩子名字难道会搞错。
户籍警说裴美玲的丈夫活着的,大女儿跟他姓的。小女儿丈夫也活着,就一个儿子。
都在,我惊呆了,我是谁?
我在哪儿,在做什么,我要去哪儿?
户籍警看到我的状况也有点懵,大约是以为,我见不到亲戚,又发现裴家有点强势没想通。
其实我是无法接受,有两个我。一定要去看看,另一个裴瑾。
已经不考虑有可能存在的三个我了。
人都有来处,不管是父母生的,石头里蹦出来的,还是魂穿的,我从哪里来的。
50岁的我,正是知天命之年。美好的生活一下子更美好了。年轻了难道不是嘛?
至少前25年我是裴瑾,这个父母全在,家庭完整的我是真的。
另一个呢,在同一所医院,两个姓名相同的人不一样的时期在同一间手术室,面临同样的抢救?
我是哪个,这个活着,不管芯子是谁,她是完整的,美好的,正常的。
我既然不是她,那么另一个真的就是我吗?
一定要去看一眼孩子。
我与户籍警还有另一位警察致谢告别,匆匆跑去学校等下课,快到了才发现星期六是休息的,一种想笑又想哭的感觉袭来。
我去了从前一直喜欢,早早来到坐在里面吃烧烤的店铺。因为怕孩子吃了不好,我总在接他以前在这儿吃几串过过瘾。
照旧叫了几串常吃的。都多少年过去了,居然还历历在目从前的爱好。
一边撸串一边又想起来,可以去生产的医院了解一下另一个裴瑾。
很近的,医院是7天24小时开业的,都有人,周六不休。
说走就走,我找到医院,看着产科大楼的楼层介绍。下面几层是外科的,8楼是妇科,9楼,10楼是产科。
我跑到产科,没人理会,他们当我是爸爸吧!找到一个眼熟的护工,我悄悄把她叫到一边,拿出姑姑和我的照片。
“这是我姑姑,亲姑姑,她女儿嫁给上海人,听说去年在这儿生了孩子,但是死了。她们长得很像。”说到这儿,她一激灵,打个颤。
她看我一眼,说,“马上就吃饭了,我们出去说。”
我偷偷塞给她一个红包,点点头说,我在电梯门口等你。
心里面直打鼓,是了,死了,我是她变的,她变成了我。脚步越来越重,有种大哭一场,不要在乎一切的欲望。
一会儿护工来了,她看上去很干练,非常干净,找她照顾小婴儿,父母亲一定很放心的。
我们去了医院隔壁的小饭馆,我叫了几个菜招待她,她要了三两饭。吃了几口,我看着她,耐心快要变定时钟,马上要响起来前,她开口了。
“她叫裴瑾,生产时候休克了,据说抢救过来的,孩子是健康的。”
“没想到在监护室里,心跳加速,警报直响。
抢救的医生不知道情况,给她用了药过敏,20分钟就没气了。怎么也救不活。”
“医院赔了30万。”然后她又盯着我,“这是你妹妹?姑姑的女儿,你姑姑没来和亲家接触?”
“我们家不知道妹妹死因。姑姑和女儿不开心,叫她别嫁给外地人,我们家在广东。”反正吹牛也不伤害别人,我使劲博取同情,眼泪是真的。
我死了,我难道不该哭,着回是真的,那么骨灰怎么回事呢?
“妹夫他是不是结婚了。”这下是关键,是怎么也逃不过的问题。
那位护工使劲你点点头,这是个新闻,你妹夫娶了我们医院产科病房的护士。喜糖我也拿到。大家在后面议论,赔了这点钱也是因为又讨了老婆,不好意思在新老婆的单位闹。
“孩子呢?”我想着是不是找个借口把孩子要去给姑姑带。一想不对啊,孩子还有亲外婆呢!这家和我家不是亲戚,我凭什么呢?
没听说我们医院的护士带着孩子,说不定就给了奶奶或者姥姥带。
已经清楚了,只不过听下来这个裴瑾就是名字熟,家里都不是我知道的啊?
那个裴瑾所有的都是什么对的上号的,连儿子生日也对。这个除了生产的日期和姓名其他的我都没接触过。
记忆是件好东西,她家的男人我也不认识,我明明不是这个,为什么我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兔子的灵魂。而真正的裴瑾好好的活着,偏偏我的记忆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