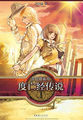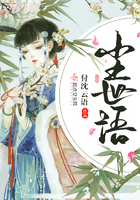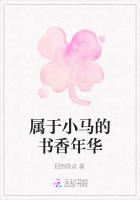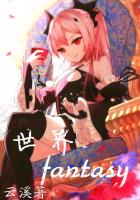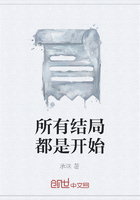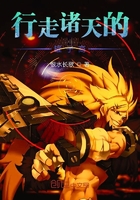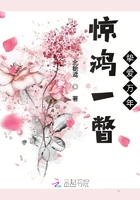何谓小说伦理 文\李建军
小说的伦理问题和小说艺术的本质密切相关。小说家的伦理态度和处理伦理问题的能力,决定了他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会对读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成熟的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从不讳言自己对政治、信仰、苦难、拯救、罪恶、惩罚以及爱和希望等伦理问题的焦虑和关注。如何表现作者自己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如何建构作者与人物的伦理关系,如何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何获得积极的道德效果和伦理效果,乃是成熟的小说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阅读那些优秀的作品,读者固然会为其中的美感所吸引,但更会被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诗意和伦理精神持久地感动。斯坦纳在评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说:他们的作品“是文学领域中涉及信念问题的重要典范,它们给读者的心灵带来巨大影响,涉及的价值观以非常明显的方式,与我们所在时代的政治形成密切关系,我们根本无法在纯粹的文学层面上对其做出回应。”
展现包含着道德内容的冲突性情境,表现充满道德意味和伦理性质的主题,乃是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重要特点。美国批评家特里林就特别强调文学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意义。他把“道德职责”当成作家最重要的“知性”,甚至提出了“道德现实主义”的主张。在《风俗、道德与小说》一文中,他把小说视为“道德想象力最有效的媒介”。在他看来,小说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在道德影响力和伦理感召力方面,它具有别的文学样式无法取代的作用和地位:“无论在美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小说从来就不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的缺点和失败也比比皆是。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和实际效用在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将读者本人引入道德生活中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育引导他所理解的一切。小说教会我们认识人类多样化的程度,以及这种多样化的价值,这是其他体裁所不能取得的效果。”他把道德效果当作评价一部小说价值的至关重要的尺度,他高度评价简·奥斯汀的小说,认为“《傲慢与偏见》最大的魅力和最具魅力的伟大之处便在于它能让我们将道德视为一种风格。”特里林高度评价巴别尔的小说,因为,他发现,巴别尔像简·奥斯汀一样关注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在巴别尔那里,美学效果是为了更高的道德效果和伦理目的而存在的,是为了“非凡的责任感”而存在的:“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巴别尔特别关注形式,关注美学的表层意义,而这种关注态度完全是为他的道德关怀所服务的。”比较起来,伊迪丝·沃顿之所以让人失望和不满,是因为她缺乏这样的道德自觉和伦理精神,是因为她的小说《伊登·弗洛姆》不仅“根本没有表现任何道德问题”,而且,还表现出严重的“道德的惰性”。
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中,他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小说的伦理性和作者的伦理责任。他把交流和沟通当作文学的本质,把文学当作引导人类心灵生活的良师和益友,所以,他不仅强调作家和作品对读者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读者伦理”(ethics of readers)的概念,认为读者对“故事”同样负有责任。他关注包含在小说中的那些“极为严格的道德标准”,例如“诚实”、“正派”、“宽容”,但“‘道德判断’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更关心与“性格”、“人格”和“自我”相关的一系列效果。这样,他便对“伦理批评”做了这样的阐释:“伦理批评试图描述故事讲述者与故事阅读者或倾听者之间的情志的遇合。伦理批评不必一开始就抱着评价的意图,但是,它们的描述总是要对作品所叙写的价值进行评价。”他说自己的伦理批评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到讨论叙述经验的伦理品质的方式。当我们阅读和倾听的时候,我们在与什么样的伙伴交往?我们曾经拥有过什么样的朋友?”虽然布斯的“小说伦理学”尚未形成充分、完备的理论形态,也不像他的小说修辞学理论那样影响深远,但却是富有理论勇气和现实感的,为“小说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和深刻的启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和界定小说伦理呢?虽然小说伦理是小说写作和小说文本中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关于它的“词典定义”(lexicographical definition)却是不存在的。不过,我们可以尝试着对它进行设定性(stipulative) 的界定。所谓小说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时,在塑造作者自己的自我形象时,在建构自己与生活及权力的关系时,所选择的文化立场和价值标准,所表现出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态度,所运用的修辞策略和叙事方法;它既关乎理念,也关乎实践,既是指一套观念体系,也指一种实践方式。它涉及至少五个方面的因素:作者、人物、读者、生活和权力;其中,作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核心位置,发挥着选择、组织、判断和评价的主导作用。一部小说的成败、优劣,最终决定于作者能否以最佳的方式处理小说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关系。就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而言,作者与自我、作者与人物、作者(经由作品而建构的)与读者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内部伦理;就作者与外部客体世界的关系而言,作者与生活、权力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外部伦理。按照作者伦理意识的自觉程度,又可将小说伦理分为积极伦理和消极伦理;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诗意,具有对人物公正和同情的态度,具有通过反思和批判来介入生活和建构生活的热情,具有净化和升华的力量,后者则缺乏道德诗意和伦理情调,缺乏对人物的理解,缺乏批判的精神和介入的勇气,缺乏净化和升华的力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前者的典型文本是《红楼梦》,后者的典型文本是《金瓶梅》。
在小说领域,不存在纯形式的小说技巧。表面上看,技巧和手段似乎纯然是一个工具性的问题,技巧的选择和运用完全是美学领域的实践问题。事实上,隐含在技巧背后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美学意图,还有作者包含着政治、宗教、性别等立场的伦理态度和写作意向——按照布斯的说法,技巧的问题。譬如,给人物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怎样来形容和比喻,选择从谁的视点和角度展开叙事,选择由谁来做叙事者,都包含着小说家的伦理态度,显示着他对人物关系的理解,最终显示出作者在小说伦理上所获得的效果、达到的境界。斯坦纳在他的经典之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精彩地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技巧里所包含的道德意味和伦理品质:“给予小角色专有名称,对他们在小说中露面之前的生活有所介绍,这种技巧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取得的效果不可小觑。托尔斯泰的艺术富于人文主义特征,他没有把人变为动物,变为寓言、讽刺、喜剧或自然主义小说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提及的呆滞对象。托尔斯泰尊重人的完整性,不愿让他沦为纯粹的工具,甚至在虚构中也是如此。普鲁斯特采用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具有启迪性的对比:在普鲁斯特的世界中,小人物常常无名无姓,他们在字面和隐喻两个层面上都被用作工具。”有时,技巧的选择甚至会受到具有主宰性的“文化无意识”的影响,例如,汤普逊在《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一书中研究俄罗斯小说的“帝国意识”和“殖民主义伦理”的时候,就发现俄国作家很少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场、很少通过“本地人”的视角来叙事,结果便造成完全不同的历史意识和伦理效果。显然,很大程度上,力量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含而不露的民族情感潜在地影响了他们对小说叙事角度的选择。
总之,伦理性是小说重要的精神品质和价值构成。一个成熟的小说家,不仅不会否定伦理性,而且还会自觉地建构小说伦理的内部和外部关系,自觉地处理复杂的、有价值的伦理主题,从而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伟大的伦理精神和深邃的伦理意义。相反,如果小说家将作品当作一个封闭的世界,将客观性和幻象当作最高价值,如果人物的“声音”被不适当地抬高,以至于作者被淹没在“众声喧哗”里,如果将“可写性”置于“可读性”之上,并赋予读者的阅读以无限制的自由,那么,小说的伦理关系就将陷入紧张的状态,小说最终就会因“去作者化”而成为一个缺乏亲切感、可读性和伦理价值的文本世界。
[ 作者系文学批评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