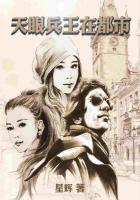他们可不知道,这时还在玉书房侍侯的宫女太监,正忍笑的看着两个关心则乱的人,做着这种难得一见的没营养到白痴的对话。
两人在离开皇宫后的几天里,辛追都忙着东奔西跑交朋识友,好容易有点两人独处的时间,也迟钝的几乎令人发指的没留心,自己几天前点燃的火山还处在喷火状态无法平复。
气愤之于圣很大力的拉住辛追想要再次外逃的身体,要不是她要去的是那些官宦富甲家小姐的香闺,圣怎么也不会允许自己被她遗忘在府里自生自灭而不去当连体人的。
先不说自己的****了,就是辛追的寻人状况他都不知道,每次他想问的时候,辛追总是能找出千百种希奇古怪的借口插磕打岔混过去,害得他被这种有力无处使的无奈憋的够戗,简直快要生出有无语问苍天的感慨了。
圣没好气的拉住再次想逃逸的辛追,二话不说直接回屋,不管怎样他都不打算和这小怪物继续玩捉迷藏。“先和我说说你这几天的寻找有没有进展。”声音里满是叹息和无可奈何。
“没有了,哪有那么简单的。”对着圣翻起不知道是这些天来的第几次白眼:“你们这个时代的女孩子都好象有病一样,只要一提起匈奴首先的联想就是环境风沙满天,苦寒无比。
人们暴戾野蛮,身形高大,红发碧眼,妖魔鬼怪。别说让她们嫁了,看他们的样子,就好象有谁亲眼见过什么人被生吞活拨一样。”
“那!”圣的眉头皱成小山,不意外的发现对话的结果有让自己提前衰老的迹象。
“不急,了不起最后偶嫁过去,然后把两国弄它个天翻地覆。”辛追摆出一副听之任之的无所谓表情,把刘圣气得牙痒痒。
圣控制不住,用手抓住她的双肩摇动颤声怒吼:“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虽是在生气,但那压不住的颤抖,丝毫不留余地的出卖了他的关心。
“你生气做什么,我又不是你的花魁知己。”辛追的表情天真到无辜,不过酸的程度使人严重怀疑泡着她的液体不是醋,而是没有经过任何溶解稀释的醋精。
“唉!小姑奶奶,我错了好不好。不过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人家还是清官这大家都知道,不用我给你特意解释它的意思吧!”刘圣扬着唇角,似笑非笑。
“你的意思是暗示我,如果人家不是清官,你就可能不会什么也没做了吗?”辛追故意曲解,但更多的还是幽怨与萧索。
刘圣笑:“小醋坛子,没有。从认识你之前到以后的岁月,能让我头痛个牵挂的只有一个人,一个叫辛追的小怪物,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你呀。”辛追顺势依偎进他的怀抱,打算不在继续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人家只是和你生气,可是你也不用太担心。你想你那精明的皇帝老爸,怎么可能用自己的江山社稷来赌呢。”
刘圣默然,这个他不是没有想到,可他的心叹息的:“你还知道我担心!”说罢扶着她肩膀的手向下滑动,轻轻一使劲将她紧紧的扣入怀中。
以后的时间,下人们没看见辛追姑娘出门,那个夜晚没有月没有光的照拂,没人打扰的两个身影,相依的与夜融成一体,在暗淡的夜色中感受彼此的温暖。
同一个夜晚,另一个绝美的少女白衣飘飘,似真似幻的坐在窗前。房间里的灯光很弱,这让原本就娇弱、美丽、不染纤尘的少女愈发有随时会乘风非去的感觉。
天色越来越深,一个丫鬟打扮的女孩悄无声息的走进房间,对着依然在窗边吹风的少女无奈的摇头。
随手在衣架上取下一件披风,莲步轻移走到窗前,看着依然呆呆出神的少女轻蹙柳眉,双眼如水波般漾着深邃的忧郁,即便是笑的时候也掩不住淡淡忧愁,似有难解千结,令人不由得心生怜惜。
小丫鬟帮少女披上披风喟叹一声:“小姐,您总是有这么深的忧郁,这么重的心事,身体怎么会好。”
少女淡淡一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完全不放在心上,转头望着丫鬟担心情急的面孔,,她才轻嘘口气喃道:“不是我不爱惜身子,是上天不给如霞爱惜的命。”
小丫鬟叹口气:“小姐别怪我唠唠叨叨地念您。说出身您虽然比不上管宦人家的小姐,可是您的容貌气质又是哪一个富家千斤敢一比高下的。可是如果您一定要在这上面钻牛角尖,那真的谁也帮不上您。”
如霞摇摇头,裙摆轻扬,站起身往屋里走去。“你哪里知道,我是宁愿有个丑陋的容貌做个清白人家的女子,也不要当什么劳神子的花魁的。”
小丫鬟愣愣地看着小姐的背影,突然眼眶一阵灼热,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如霞幽幽叹口气撅撅然转身,只觉得浑身无力,不胜虚弱,又是一声叹息坐在琴前,正好面对琴桌上摆放的一纸书绢和一枚精致的龙形玉制腰饰。
“小姐……”小丫鬟忧心仲仲的眼不安地凝视着如霞:“小姐过去好几天了,那人不会来的,您不要再等了吧。”
如霞摇摇头:“他一定是有事情在忙,我能看出来他不会是个不重承诺的人。”
丫鬟摇摇头,试图想让自己的小姐从不可能的幻想中情形过来。“您根本不认识那个人,他也没和您说什么,一张写了两个字的书简,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承诺。”
“可是,他写的是……”如霞忽然感觉象是有人拿着火热的利刃,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插人她的心头。
“是他写的是自由,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小丫鬟深吸一口,声音不由因不平激动起来:“先不说他自己是不是有那个心,就是真的想要帮小姐,妈妈又怎么可能会放象姐姐这样的摇钱树赎身自由!”
如霞蹙起眉,深邃的眸子直直望夜幕,仿佛看向一个未知的世界。“有机会就有希望,如果没有了希望如霞早已成为飞灰飘散在茫茫大千世界中了。”
身为一个青楼歌妓,不论美艳群芳还是平凡无奇,充其量也都只是男人们的玩物。
既然是玩物,当然就会有一个价格。而花魁不过就是给精致的玩物打,上了一个更高的价格标签而已。至于鸨母不会要求她和其他人一样穿梭在众恩客之间倚门卖笑,不是因为她有什么了不起,更相反的是要用这一切的手段来标志货物的质量,以确保她可以长时间的利用女人最原始的吸引力去掏空男人的荷包!
不过玩物终究是玩物,总有一天,当然鸨母认为她的身价已经赚足了回票,或出现了让她满意的金主时,自己那卑微可怜的自尊,就会在一票男人垂涎争夺后成为竞价的猪肉,只等谁的价高,谁就得手。
以后的生命,以后的时间,龌龊可耻的鄙视代替清高洁净颂扬,直到青春不在年华老去时,被毫不怜惜的转卖丢弃。
就像这个房间曾经的主人,大家面对着她没有了生命气息的身体,就相面对一具被利用完的物品般,没有眼泪更没有心痛的“处理”。